
2005年,黑格爾研究的著名學者意大利哲學家洛蘇爾多,出版了一本新書《自由主義批判史》(Liberalism:A Counter-History,中譯本2014年商務印書館)。作者在前言中聲明,正因為自由主義承載了太多的心智光芒,他試圖在這聖徒傳一般光輝曆史中,逆向找尋自由主義的陰暗面,誇張地說就是自由主義的罪行或者劣跡。那麼這本書的基調大概可以理解為:主義如果替代了從前的垂直信仰,那麼作為准信仰的世俗化的主義,那佔據現代曆史中心位置的自由主義,其信徒所思、所言以及所為,是如何回應和理解17、18世紀的種族奴隸制、殖民擴張以及19世紀的勞工問題的?作為當代著名哲學家的洛蘇爾多,這次他認為自己是在書寫曆史。
多米尼克·洛蘇爾多(Domenico Losurdo,1941— )
意大利著名曆史哲學家、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專家。意大利烏爾比諾大學哲學史教授、教育學院院長,國際黑格爾—馬克思辯證思想學會主席。研究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與共產主義的關系及其解放戰爭等主題的重要學者,致力于通過解構史料來挑戰我們時代操控曆史的意識形態。著有《黑格爾與現代人的自由》《黑格爾與自由主義者》等。《自由主義批判史》于2005年在意大利出版,反響極大,一年內再版三次,並被譯為多種語言。
自由主義從誕生之初,並沒有承諾要消除人間的一切的罪惡與不公,自由主義總是伴隨著這些刺目的傷痛和悲憤,並試圖將矛盾與沖突移交到司法體系中,予以緩解和疏導。
視角單一
自由主義在政治現場該擔何責?
《自由主義批判史》就在這樣的路徑中展開了,任何一種觀念、意見和立場的表述都會被一樁具體的曆史事實推翻。我們知道這樣詰問適用于任何主義,比如,一個自由主義者怎麼可能是一位奴隸主?作為一個有正常心智的理性的現代人,主義該如何與行為絲絲入扣,這樣的提問方式構成了這本書的基本線索。
如果我們攜带著如此尖利的問題意識,進入任何以主義之名所展開的曆史開端,甚至包括宗教史,我們就會與洛蘇爾多一起感到絕望與悲憤,這種視角的單一性本身就決定了作為過程性曆史不可抹除的悲劇屬性。首先必須接受曆史邏輯就是強力意志,所謂的曆史潮流带來的毀滅感籠罩在人的周圍,新/舊對立最慘烈的沖突總是在第一時間发生,任何起源故事的現場總是會出現血汙與暴力。但有一點必須澄清的是,作為政治自由主義的誕生故事里,除了確定自主自決自治的原則之外,政治自由主義作為新型的權力,他的敵人僅僅是暴政與專制,這種權力之外不產出任何東西。不可能存在負責一切並承擔一切的自由主義,就其政治涵義而言,因此作為信念的自由自身恰恰是種族奴隸制、殖民主義的終結者。
在這個意義上,自由主義是否應該為貫穿在《自由主義批判史》中的黑奴境況、美洲原住民的滅絕以及19世紀的勞工待遇承擔責任,這是一個驚悚而又令人疑惑的問題。因為自由主義從誕生之初,並沒有承諾要消除人間的一切的罪惡與不公,自由主義總是伴隨著這些刺目的傷痛和悲憤,並試圖將矛盾與沖突移交到司法體系中,予以緩解和疏導。而作為抽象自由的實體概念權利一旦深入人心,人們會以更加慎重的態度來處理、調試與權衡特殊利益之間的矛盾,因為權利的概念是普遍性的。這就是為什麼美國國父們在賓夕法尼亞的制憲會議必須隱秘地進行,並將廢奴議題寫進了憲法章程,政治創制與政治實踐就這樣在心智的門內與門外展開了。在曆史的現場,政治智慧需要小心權衡風險問題,如果奴隸起義不是新生國家的最大威脅,那麼奴隸制,在德·托克維爾和漢娜·阿倫特這樣的政治思想家看來就不屬于政治問題,而是社會問題。當《獨立宣言》向全世界宣告:人生而平等,那麼當時在場的奴隸主的耳朵是否就有風暴穿過,這是政治劇目最詭秘的時刻。如霍布斯在其《利維坦》中題詞所言:我內心最強烈的激情就是恐懼,而免于恐懼的政治出路只能是建立起保障自然權利的世俗國家,其由恐懼所激发的悲劇詩學的革命性因子如何保持在道德審慎之中,這恰恰是政治學最難處理的議題。
契約論看起來只活在書本與人們的心智生活里,而事實卻是:1588年荷蘭人創立了曆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百年之後的1688年英國光榮革命,1776年美國革命,自由人的共同體在政治體制上宣告君主專制的終結,洛蘇爾多稱之為自由主義的三次革命,其光芒自不待言。但是這三個偉大的現代國家即自由人的共同體,恰恰是以反自由的侵犯、剝奪和排斥行為,支撐起他們的勝利,即共同攜带著殖民擴張、蓄奴的汙點和劣跡,《自由主義批判史》對此要反攻倒算的是,與自由主義起源故事相伴隨的,是良心的沉默、道德的軟弱以及心智的褊狹。和這樣的責問相關的就是自由主義理論導师們的思想和言論,在信念與事實之間,自我理解以及自我辯護如何成為可能?他們包括格勞修斯、洛克、托克維爾、孟德斯鳩乃至阿倫特。再者,洛蘇爾多一直將啟蒙思想家最喜歡使用的詞匯即人類或者每一個人,這樣全稱判斷的代詞理解為,在說出的那一刻就應該與事實完全相符。
混淆觀點
指責托克維爾關于殖民事實和蓄奴制的言論
該書中引用最多的就是托克維爾面對殖民事實和蓄奴制的言論,重要集中在那本著名的《論美國民主》緒論第十八章:居住在美國疆土上的三個種族的現狀及其可能出現的未來。洛蘇爾多全然不顧作者的上下文,斷章取義地摘取托克維爾的言論,指責這位自由主義最堅定的擁護者,將殖民者與土族劃定在文明與野蠻的對立之中。那麼托克維爾說的“野蠻”是什麼呢?他是在一個更寬泛的曆史意義上使用這對概念的,比如羅馬帝國時期的北方蠻族,以及與中華文明相對的蒙古人。沖突的結果總是“野蠻人把文明人請進他們的宮殿,而文明人則對野蠻人開放他們的學校”,武力征服之後必須依賴文明進行統治。那麼印第安人是一個怎樣的狀況呢?畢竟托克維爾的足跡曾印在這片新生的國土上,他遇見過印第安人,與他們接觸過,並在這個章節中,記錄下了對這些相遇的所感所思:文明人在追逐印第安人,前者因內心的貪婪使用各種詭計攫取後者天然擁有的大片土地,而印第安人呢,他們對所有權不感興趣,他們只對野獸的聲音和蹤跡保持敏感,他們在追逐動物以維持溫飽。“當擁有物質力量的一方同時也具有智力優勢時,則被征服的一方很少能夠走向文明,他們不是後退便是滅亡。”當然以今天人類學家的眼光來看,這是理性主義的自大與狂妄。理性主義者往往顯現為現實利益的擁護者,一切在一種功利主義的算計中保持利益最大化,就具備了一種天然的正當性,獲利就是最高的善,這也是我們所熟悉的源自19世紀經濟自由主義的核心。
而蓄奴制則涉及更复雜的曆史與制度問題,托克維爾從來沒有為這個罪惡的制度辯護,他只不過以一種带有勤儉的清教色彩的筆觸,來描述他觀察的黑人,他們懶散,遲鈍,而與之相輔相成的南方莊園主即奴隸主,他們輕視勞動,享受基于特殊經濟作物所带來的特殊的經濟利益,他們情願終生負擔奴隸的吃穿住,也不願意向北方人那樣以貨币來購買勞動力,他們身上殘存著老貴族的習氣。托克維爾基于一種平實觀察者視角,描述了蓄奴制以及廢奴制的各種錯綜复雜的原因和困境,他的結論是廢除奴隸制之後,黑人迎來的會是更悲慘的處境,自由之身會淪陷于白人世界更可怕的隔離與歧視之中。托克維爾的預言沒錯,但曆史的進程,或者自由主義艱險幽微的實踐恰恰在此,曆史知識告訴人們:廢奴制以及更晚的民權運動的驅動力來自宗教,是亨利·克拉克·賴特以及馬丁·路德金這樣的偉大牧师,在自由平等的嚴酷戰場,顯示出了一種驚人的力量。當然檢閱這樣的曆史,人們還須記取的是:19世紀前後逐漸壯大的中產階級力量,對平權運動的積極回應也有重要關聯,而這個階層正是從工商業文明,也就是哈耶克所說的財富智慧所積澱的自由信仰中誕生的人群,無一例外都是普遍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
但是曆史的缺憾總是這樣,並沒有讓人類學的知識在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來挽救文明樣態的多元性,當然多元性恰恰是我們今天握在手里的一種自由主義立場——就寬泛意義的自由而言。與托克維爾的同時代人,或者說被自由主義碰巧遇上的是另外一種人類學,這就是達爾文主義和斯賓塞的進化論。因此,在19世紀,自由主義與曆史主義交織,工業革命带來的巨大財富,讓當時的人們沉浸在進步與发展的高亢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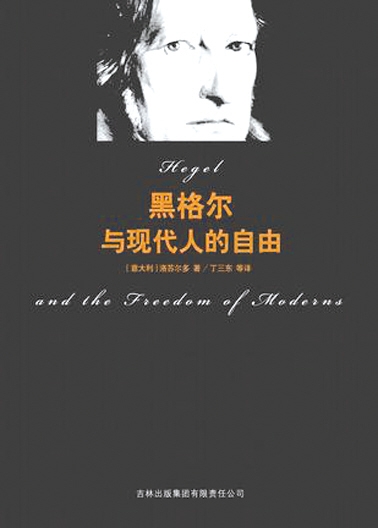
首先是自由存在,不管是精神的還是制度的,激進的保守的也好,才有可能真誠面對政治的古老的箴言:與他人一道,在合理的制度中追求共同的善。
《自由主義批判史》
作者:(意)多米尼克·洛蘇爾多
版本:商務印書館2014年3月
在政治術語和學者的論著里,自由主義是世界曆史中一種積極的力量;自由的社會可能曾容忍了一些罪惡,但那只是實現普遍自由過程中的偶然產物。洛蘇爾多反對此種說法,他揭示了自由主義的內在矛盾:它是一種無力踐履自身理想的意識形態。本書中,他以批判柏克、洛克、孟德斯鳩、富蘭克林、傑斐遜等自由主義先驅開篇,指出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哲學立場和意識形態,自始就與奴隸制、殖民主義、種族滅絕、種族主義和勢利眼之類最反自由的政治行為密切相關。
聯系牽強
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並無直接關聯
洛蘇爾多將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有關帝國擴張與種族主義的內容,解讀為極權主義的原因,認為“優等種族民主”和“統治種族”范疇的出現,“不僅是作為整體的集中營體系,而且是個別的極權體制已開始形成。”而脫胎于上述三次革命的自由國家身上,就攜带著擴張與種族統治這兩個可恥的汙跡,于是洛蘇爾多大膽地將極權主義與自由主義建立起邏輯關聯。的確,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阿倫特列下了這樣的標題:“英國人的權利”與人權,但是她小心甄別了種族優越論與真正的政治思想之間的區別,前者其實並不關心政治,他們只不過以此作為某種便利工具,為擴張攫取實際利益服務。激勵這種勇往直前的擴張行為,那種征服者的驕傲,恰恰是達爾文優勝劣汰的進化論。受進化論推波助瀾的種族優越觀只能激化政治沖突,而並不產生任何有益的政治思想。但與種族優越論切近的民族自豪感的另一個來源就是政治性的,像英國人那樣,不放棄啟蒙以來的大寫的普遍的人的觀念,在政治實踐中往往會以人類保護者的面目出現,這樣带有政治意味的意圖必須借助自由人共同體的原始因素,比如土地和血緣,來凝聚起主權疆域之外的統治力量,統治並傳播某種文明法則。因此,自由主義與極權主義沒有任何直接關聯,在他們中間也許存在著無數的主義,在曆史的情感、意志上发揮效用。
其實,阿倫特最為警惕的正是人們很容易將《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中談到的問題,直接理解為極權主義的发生原因。在伊麗莎白·楊-布魯爾所著的《愛這個世界——阿倫特傳》里,記錄了阿倫特未曾发表過的一次講座內容,涉及《極權主義的起源》第二版的修訂內容。阿倫特強調自己的起源研究方法的現象學傳統,即起源處的各種構成性因素並不一定直接導致極權的結果,其關系不是邏輯性的,而是說極權主義如果是一個事件或現象,從其自身內部測量時間的話,曆史的曆史性就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未來則是現在完成時的,過去就成了正在進行時。
從未聲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阿倫特,也被洛蘇爾多作為反自由的反面言論,可能因為阿倫特是美國革命最精湛的理論辯護者。洛蘇爾多引用了阿倫特在《論革命》中的原話,認為她面對罪惡的奴隸制,也存在一種智識上的模糊面目。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美國革命既然向世界宣告一個自由政治秩序的誕生,那麼當時的立國者們為什麼對奴隸制持有一種曖昧不清的態度?阿倫特的回答是,這種態度上的漠然並不意味著實際上的良心沉默。《論革命》一個重要的理論貢獻就是,將政治問題與社會問題嚴格地區分開來,政治自由要處理的核心問題是,一種怎樣的制度規劃,能夠讓人顯現于公共空間,讓個體生命從相互隔絕與無動于衷的狀態走出來,彼此相遇聚集,這聚集的力量被阿倫特稱為權力,權力在這一刻給所有人带來光明。因此,基于情感層面的同情與憐憫,往往很容易被外顯的困苦所激发,這里沒有任何政治內涵,但這種強烈的情感會煽動其政治激情。政治的发生一定依賴激情,但僅有激情,沒有理智的冷靜與更寬廣的深思熟慮所形成的政治判斷,這種激情本身就會带來災難。盡管阿倫特對法國大革命的理解有所偏頗,但她對美國革命的理論辨析,已經讓自由的信念成了無可辯駁的神聖理性。
誇大不足
關閉了自由主義曆史批判的路徑
至此,洛蘇爾多所羅列的自由主義第三宗罪,即“階級壓迫”已經躍入一個新時代的新問題了,正如馬克思所言,奴隸並非天生是奴隸,而是在買賣行為中產生的,一種普世化的生產關系如何變成了最可恥的壓迫,馬克思的術語稱之為“資產階級的政權”。在這樣的曆史時期,奴隸制不复存在,現在,的確如洛蘇爾多所言的,自由人共同體內部的劇烈沖突展開了,在法國,工人起義頻繁爆发。洛蘇爾多寫道:“對于當時的自由主義來說,毫無疑問的是財產權面臨的風險使得政變合法化了。”
接著洛蘇爾多羅列的一系列自由主義者——主要代表依然是德·托克維爾,面對財產累進稅是否保留、議會席位是否擴大以及挑戰法律程序的暴動等相關事件的態度,都持有激烈的反對立場;讓他最不能忍受的是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在得知工會罷工抗議時,竟使用了“射殺”這個字眼;自由主義者更令人不齒的是,當他們得知意大利法西斯這樣的政治勢力是確保財產所有權、痛斥累進所得稅制式乃合法偷盜行為,如米塞斯這樣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大师竟給予法西斯主義明里暗里的言論支持。
在此,對自由主義的批判,令人不安的首先還不是邏輯性的錯誤,因為支持一種經濟制度與支持法西斯肯定是兩個概念,更為令人迷惑的是,作為黑格爾研究專家,洛蘇爾多曾根據黑格爾的《權利哲學原理》(漢譯通行本《法哲學原理》),寫過一本《黑格爾與現代人的自由》一書,把黑格爾對市民社會的批判從其絕對精神的演繹環節中抽取出來,變成了純粹的政治問題,但黑格爾強調:正是市民社會強化了自由人的自我意識,沖突是自由的一種表現。如果不在馬克思主義的譜系里來思考19世紀出現的勞資沖突,那麼我們就應該回到黑格爾關于市民社會的邏輯辨析,即經驗如何顯示為一種權利制度的邏輯運行模式。黑格爾將市民社會,即現代意義上的自由人共同體內部的沖突,理解為一種特殊利益與另一種特殊利益的沖突。而這個沖突发生的根源,恰恰援引的是由自由主義政治的國家承諾,即在人間事務中所確立的普遍的自由意志,就現實而言就是被啟蒙了的自身利益。
但是洛蘇爾多把自由主義者關于抵抗行為的暴力性、與財產權密切相關的社會主義思潮及實踐、議會政治的參與權等問題的反應,籠統地解釋為自由主義針對自由的背叛,顯然有些誇大其詞。另外一種智識困局正如芝加哥大學曆史學教授Jennifer Pitts指出:如果洛蘇爾多將自由主義與種族主義、極權主義擺放在一起,這樣就已經關閉了對自由主義曆史進行批判的豐富路徑。因為當自由主義的政治革命完成之後,統治依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矛盾與沖突,這時候的自由主義就以秩序與法制為由,顯現出了其保守的面目,因為秩序和法制更多的時候是官僚體制的遮羞布。被送入正當程序的權力統治,不會改變其馬基雅維利意義上的強硬屬性。思想家只能在事實、事實造成的結果中來小心甄別抵抗的正當性,一個最棘手的問題就是,革命或多或少都具有暴力性,但暴力絕不等于革命。而繼續革命,如果從抵抗的激進的民主邏輯來看,生活世界中的政治抵抗,已經超出了洛蘇爾多所檢視的自由主義曆史,因為他沒有涉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西方世界的文化革命。在20世紀60年代的這股新左翼浪潮之中,自由依然是佔據人們心靈之中最耀眼的字眼。
就自由主義觀念史自身的演化曆程來看,自由主義理論宗师康德所關心的道德哲學有一個不言自明的權利基礎,與現代人的形式自由相對應,在今天依然是我們思考自由最值得信賴的精神資源。而在這個哲學前提之下,革命可能會吞噬她的兒女,但自由主義盡管面目混雜,無論怎樣依然是普遍權利的堅定守護者。就政治而言,今天的各種意識形態立場必須面對自由主義說話,才能自由地去抗辯質詢:誰的權利?何種正當性?因為人不可能在一種無自由的狀態中來反對自由主義,簡單地說,也只有在政治自由的條件之下,反對自由主義的思想依然受到自由權利的捍衛。
首先是自由存在,不管是精神的還是制度的,激進的保守的也好,才有可能真誠面對政治的古老的箴言:與他人一道,在合理的制度中追求共同的善。
【延伸】
《黑格爾與現代人的自由》
作者:(意)多米尼克·洛蘇爾多
版本:吉林出版集團
2008年12月
現代社會是一個大規模異質人群聚居的社會,是一個复雜社會。黑格爾所反思的正是這個复雜的社會:如何讓所有的社會階層,如何讓每一個人的自由都能夠得到現實的實現?自由概念與平等概念之間有著怎樣微妙的張力?作為國際著名的黑格爾哲學研究專家,多米尼克·洛蘇爾多在本書中試圖證明,黑格爾的理論恰恰是現代人的自由的真正堅定的捍衛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