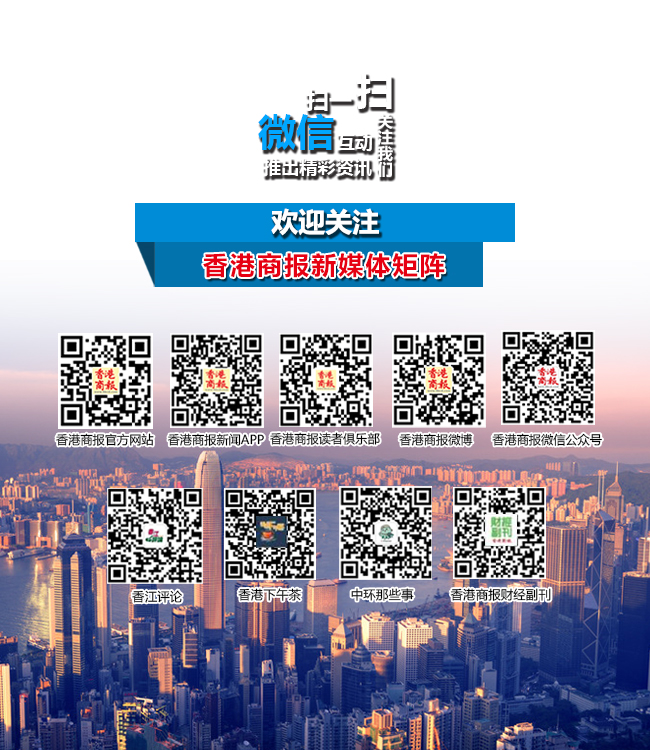學一門“外語”(母語外的語言),很多人從罵人的話開始。其實,我也一樣。我學是從“黐線”(qixin,神經病)開始的。
我的職業起步于廈門的一家叫做XOCECO的公司,第一個O是Overseas。我去的時候廈門特區剛剛成立一兩年,香港投資方康力在這家公司派駐了許多不太會講普通話的經理。好玩的是他們的英文名,總經理馮光銳叫JOHN,采購經理叫Jonny,海外市場部經理叫Joseph,后來來的叫Johnsen……連模具廠的李大叔也叫J什麼來着。大概是馮信教,所以請的人也都是這類貨色的。
當時我在海外市場部,備受“欺辱”。這些叫J的經理,常常拿廣東話嘲笑我。一個人聽不懂羞辱的話,本來是一種福氣。但血氣方剛的我,感覺那是一種難耐,這種難耐化作了羞辱感。于是,我發誓要盡快聽懂廣東話。
那時候,廣交會每年兩屆,每屆會期有兩個禮拜之久,連布展撤展要一個月長。1987年春交會,我發誓在廣州把廣東話學出“臭尿破”味。我住在廣元西路的宇航賓館。剛進住時,就開始跟服務員開玩笑。被罵——“黐線”。我聽成“氣死你”。我答,我這個人樂觀,“你是氣不死我的!”
其實,“黐線”的意思是,神經線搭在一起,發生了錯亂。
當然,我在廣州街頭很快學會第二句話:丟累勞模。這句話后來有了英文版,叫Delay no more,如狗不理被譯成Go believe,雅正得奇妙無窮。

當然,在從廈門出發來廣州前,我是下功夫溫習的。香港的朋友到廈門,過了關,總要給我带手信——一支酒、兩條煙。我說,這次免了,你給我带一本粵語速成教材。于是,我一個字一個字啃,大致掌握了一些普通會話。當然書上是沒有“黐線”和“delay no more”這些的。
那時候來廣交會的,有講英文的鬼佬,但更多的是來自香港的間商。那時候大陸人還傻傻的,要把差價給港澳同胞賺。我認識了一位叫張健生的香港人,他是從廣州偷渡去的。他服務的公司做非洲生意,對我們的電視機很感興趣。這兄弟笑容,我覺得很有親和力,于是大膽地與他用粵語聊天。他剛初總是用普通話回應我的廣東話。我開始,把電視機(gei)說成電視雞(gai)。“gei唔系gai,gai是‘叫雞’的gai。”我這才明白,機不是雞,雞不叫機。
我畢業踏入廈門島起,就喜歡喝廣東早茶。無論在泉州,在廣州,在香港或者去成都、新加坡,一早都會約人去有粵式早茶的餐廳喝早茶。因為這個氛圍,我能夠接觸講純正廣東話。
從“飲”的讀音yam,我掌握了很多以m為尾音的字,比如南(nam),kam用。又比如dim sam(點心)。其實,閩南話里,m這個音也用得不少,比如“kam蘭”(很厲害的意思)、甘(gam)願。而普通話的拼音,只用n,不用m。所以你叫北方人發“南方”這個詞,他會說“nan fung”,而福建人則發“nam hung”。
學一門地方話,測試你是不是學了點譜兒,就看當地人是不是願意跟你講這種話。一個禮拜后,再見我的上述張健生先生,發生了轉變,開始或多或少跟我講廣東話了。
這是,我知道,我成功一半了。

閩南人齙牙多,講話總漏氣。該閉唇的不閉唇,比如“福建”念成“胡建”,陳忠和把“發球”發成“花球”。而廣東人愛把不閉唇的發成閉唇的,比如“流花”、“化州”的hua讀成“fa”……那時候我腦筋還不打結,能夠識破很多規律。
“去”這個字,廣東話,讀的不是hui,海這個字,讀的不是hai。我發現一個共同點,拼音間存在一個“o”。去,讀hoei;海,讀hoai。
最典型的就是“唔該”(excuse me,麻煩……,謝謝),讀m3 goi1。

當然帮助我學廣東話的還有電視。當時香港、廣州的電視有不少早晨節目,播新聞、搞專訪、介紹美食。我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知名的口水聰的。
才一個廣交會的時間,我基本能簡單跟粵港人會話了。這讓很多港籍經理很surprise,連后來當廈門副市長的公司常務副總葉天捷也很欣喜。但也因為我學了粵語,成了親港派,不受中方人員待見,當一官半職的希望破滅。在八十年代末,轉會香港的公司了。我走的時間跟老習差不多(我是八八年八月走的)。
八九事發前,物價飛漲。一家香港電子貿易公司,在廣州順德佛山一带做fujiyama的OEM產品,我被指定為港方代表,游走于三四地,住在小北路的分支法政路的小洋樓里。那個時候,廣東人還把普通話當鳥語,于是我的廣東話越來越趨近完美。雖然,一開口,很多本地人就判斷:你是潮州或汕頭人吧!
泛閩南語系的潮汕人,一開口,跟閩南人一樣,總带着濃濃的地瓜腔。
來,了解一下廣東話的歷史。
史料說,秦朝滅亡后,南海郡尉趙佗兼並桂林郡和象郡稱王,建立了短暫的南越國。在漢朝的鼎盛時期,華夏族融合當時百越族演變成漢族。中原語言和當地古越語(百越之南越)本土語言形成粵語雛形。閩越、南越、揚越等即百越。
粵語至今還保留像ng這樣的聲母,這是普通話里沒有的(ng在普通話是韻母)。而,粵語共有9個聲調,這也是熟悉了普通話四個調的人,難以掌握這門“外語”的原因。
粵語一共分為九聲:
❶陰平、❷陰上、❸陰去、❹陽平、❺陽上、❻陽去、❼陰入、❽中入、❾陽入。
九聲各自代表字有:
❶詩、❷史、❸試、❹時、❺市、❻事、❼色、❽錫、❾食。
關于香港廣東話,細讀本文后的“閱讀原文”。

我第一次去香港,不是1987年尾,就是1988年春。那時候,香港只講兩種語言,一是廣東話,二是英語。當時我在維多利亞公園撞到香港電台的一個活動,認識了兩個藝人,一個叫林憶蓮,一個叫鐘淑慧。
我感覺,我講的廣東話水平,已經超過她們講普通話的水平。
很好玩的是,林憶蓮知道我是大陸來的,刻意跟我講普通話,而我不從,偏偏與她講廣東話。約莫兩年后,林憶蓮的第一張普通話大碟《愛上一個不回家的人》面市。
當然菜市場也可聽到閩南話,那是在北角筲箕灣地區。根本沒有普通話什麼事。我一直覺得,你字正腔圓地用普通話跟香港人講道理,是無法講通的。你不掌握粵語,就無法了解當地人的思維方式。無論新華社還是中聯辦,大多的官員都不會講當地話,這是起矛盾的初因。
普通話才四個調,顯得簡單粗暴!廣東話除了有九個調,一句本來比較硬的話,也被長長的“~啊”“~啦”軟化了、稀釋了。所以,你會總體覺得廣東人比較隨和。

孫中山孫大炮有權有勢的時候,沒把廣東話當作民國的普通話。我覺得這是他大公無私的表現。但慶幸香港這個地荒,因為被租借出去,一種地方性語言得以被發揚光大。
香港開埠前,原居民有三個群體,分別為圍頭人、蜑家人(又稱水上人)、客家人,各族群皆有自己的語言(即圍頭話、疍家話、客家話),其中圍頭話和疍家話亦是粵語的分支,香港一詞的英語譯名“Hongkong”就是取自疍家話發音。
香港成為英國殖民地后,中國大陸其他地方的人如廣州人、江門人、東莞人、潮州人、閩人陸續入境,各自有不同的語言,如廣州話、四邑話及閩南話等在新界原居民的鄉村,原本以圍頭話或客家話教學的私塾,也被迫令要使用粵語廣州話教學。自此,廣州話成為了香港的常用語言,逐漸發展及形成了香港粵語,並且達致了香港語文中的第一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香港人口約50萬,當時的香港社會上流通多種方言,包括廣州話、客家話(非本地客家人)、閩南話、閩東話、四邑話、潮州話及東莞話等;在新界則有圍頭話及客家話,以及水上人的閩南話和蛋家話。至1950年,香港人口上升至220萬,語言使用情況復雜,各族群的人都以自家族群的語言交流。

如今,香港廣東話的優勢在于:
1、這是民間的“官話”,官方的“民話”。
2、這是香港教育的語言工具。
3、這是視聽傳播語言。
4、每句廣東話都能找到相對應的字。不像台灣人使用閩南話,有些寫不出來只能用注音。
5、粵語歌大量創造,巩固了這種語言的地位。
6、大量海外唐人街以廣東話為官方“街”語。
7、很多香港人,他們的名字雖然洋化了。但他們的中文名正式譯音,根據的是廣東的拼音。比如張為“Cheung”,陳為“Chan”,吳為“Ng”。
8、夾雜英語(讓鬼佬更易掌握)。
有一陣子,聽說廣州有意要把本地化從廣播電視里消滅,但我覺得不太可能。但是事實是,廣東話在這個南方的首府被削弱了。
相比之下,很多少數民族的語言,已經被逐漸消滅。你比如廣西自治區里的很多壯人,不但不會說壯語,還不會寫。

說得出來,就寫得出來。這是廣東話優于其他方言的地方。
當海南人“那哈呀那哈呀”講着東北話,當自貢人講四川話不再字字卷舌,當化州人沒了阿嬌腔,當莆仙人講話沒了sao味,當廣東人講話個個學着趙忠祥或者倪萍……這樣的大同,實際上是一場慢性的文革。語言,是一種活化石。想想毀了化石,對歷史文化的破壞有多大。
到現在為止,我會覺得,很多人來廣東白來了。他們沒有學會當地的語言,來深圳,只是把普通話講得更准了。有些人甚至回去,带了一口带兒音的國語。很多人說廣東話,還把“唔知”發成“母雞”。
慶幸的是,他們的兒女從英美回來,英語說不了幾句,卻把廣東話講得倍溜。原來常常去唐人街買電話卡、吃中餐,學了第二門中國話。笑死人了!
我的好朋友Sunny,是個印度人,本來他可以用英文與香港人溝通得很好。但要融入社會,做好生意,他把廣東話學了,再把普通話也掌握了。他先在上水開公司,后把家移到深圳。后來,他把羅湖向西村大地主的女兒給娶了。
2016年香港書展,我與蔡瀾問答。
很多內地人去了香港大半輩子,半句廣東話也不會講。我感覺,他們這一生單調了一些。我主張,從香港角度保留本地文化的角度考慮,以后誰想定居香港的人,先要通過廣東話考試,像靠TOEFL、雅思一樣。不通過,買張八達通,去蓮塘找卓越兄補補。我現在而今眼目下講的廣東話,比李嘉誠標准。
雖然自恃廣東話講得不錯,但我還沒用在電視台或者電台展示過(接受采訪不少)。亞視曾有個談話類的節目,記得主持的副總裁(新聞及公共事務)劉瀾昌老师曾带口:有空來參加我們節目。我渴得不得了,但最終那句話只是水扁gonggong,到關門都未如願。這讓我很不自信,爬到亞視樓頂的沖動都有了。
《尋找他鄉的故事》粵語旁白散發濃厚的“漂泊”味
亞視是我喜歡的電視台,他們有個系列紀錄片叫《尋找他鄉的故事》,旁白把漂泊感講得很入味。其實,我只想檢測自己的廣東話水平。后來《尋找》為了在大陸賺錢,改成普通話旁白。就像《看見台灣》沒了吳念真的地瓜腔解說,味道大失!
但我堅信,因為掌握廣東話,所以我更體恤香港,理解香港——知道他們為何因蝗而鬧,為何因壓而彈。你不掌握當地語言,講着包括普通話的外地話,那麼你永遠是外地人。
去一個地方,你想入味。一要吃當地的美味,二要學當地的言語。陳曉卿說,舌尖上的美味后,他要做舌尖上的方言。我說,要的!拍廣東話的時候,我來說兩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