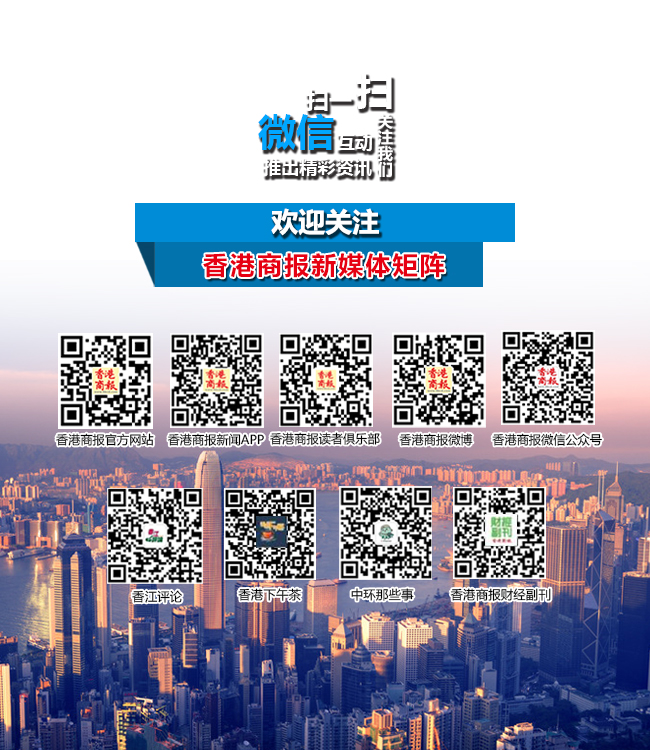这是我的香港老朋友张健生(上图),我叫他“阿张”。他已经七十岁了,我们认识时,他刚好四十岁。弹指一挥间啊!
我们1987年认识于广交会。生意没做成一单,但友谊保持了三十年。6月15日,在鰂鱼涌滨海街,我们约在他家楼下一家叫乐林的餐厅,吃小锅米线。
所谓的小锅米线,就是你叫一个米线底,然后再按兴趣叫三四样配料,肥牛、萝卜、木耳……加加埋埋,好大的一碗,甜酸苦辣,什么味都有。
我这个佬友,出生在粤东的揭西,小时候是讲客家话的,后来跟爸妈进了大省城广州,住的是中山四路的一栋三层半的小楼。1968年,阿张与弟妹先后到中山下乡。挨了三年的苦后,实在忍受不下去了。于是,响应大潮流,开始偷渡。第一次从番禺十三涌搭小船到澳门外海的琪澳岛,目标是香港。怎知道,小船被浪给打回来。
第二次,于1971年10月,从东莞常平出发,躲躲闪闪走了5晚6天,终于来到深圳的后海湾,结果被抓了回来,关到中山。2个月后,自己的大弟弟也从同样的地方偷渡,岂料海正退潮,不慎溺毙。
1972年春,阿张第三次冒险,偷渡的地方依然是深圳的后海。这次,终于成功了。
“当时生活太苦,不后悔!”阿张说,就算把广州的房子给了有关官员,有机会都要出来。
深圳有句口号叫做,来了就是深圳人。但这句话没有当年的“来了就是香港人”实在。登岸后,阿张投奔了自己的大姐和姐夫,很快成了香港人。他也成了姐夫药厂(做伤风素、止咳药)的一员,但居无定所,就在工厂的办公室席座而寝。一捱就是九年,姐夫的厂搬到哪里,他转战哪里。
1979年,阿张经常出差去马来西亚婆罗洲的古晋去催货款,认识了一些揭西河婆镇的老乡,怎知被极力推介一个南洋妹,两人一年后成了夫妻,张把她娶来香港。
刚开始,两人在姐夫工厂里开辟一个小单间作为婚房,但因为厂房不断换址,夫妻房成了流动站。老丈人看不下去了,于是阿张从姐夫那里讨来五万元汗水钱,又得到老丈人七万元的援助,1986年用两笔钱交首期,在鰂鱼涌买了一套45平方米面积的两室一厅房。“当时的房子总价是203000港币,当时100块港币大约折合人民币35元!”
现在(香港鰂鱼涌)的这套房子值400万(港币)!——阿张说。他家在广州的三层半楼房,建筑面积11平方,中山四楼拆迁的2001年,政府才给200万。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的前一晚,我应邀到阿张家里喝酒,这是我拍下了上面这张阿张与其次儿的合影。当时他小儿十岁,现在30岁。
儿子都在做什么?我关切两个侄子。
一个35岁,一个30岁。都做酒店业,都还没对象。两个人还一直住在我们两公婆的隔壁,上下床。
“他们都没买新屋?”“现在的小年轻,手头没有四五百万,怎么付得起首期?哪像我们当时!”

言谈中,阿张不像福建式的爷爷,不在乎儿子的婚况,也没有当爷爷的冲动。一种儿孙自有儿孙福的淡然。广东人在这方面上,想得比福建人轻松自在。
阿张的老婆,从小在马来西亚出生,一直不懂写中文,广东话、英文讲得非常流利。“一直在餐厅做,去年才没做。”
阿张说,自己来香港四十几年,虽然没赚到大钱,但马马虎虎总算过得去。赚了休闲。这天下午,本来他约我三点见面的,但因为打麻将耽误了时间,到了六点半才碰上头。
虽然相比回归那天的相貌,阿张头发变得稀疏且多了点白发,但总体精神面貌没有多少改变,走路一如二十年前那样矫健,没有半点古稀老人的老态。

赚多赚少是小事,命长命短是大事。阿张说,他的一个银行的朋友说,到了世界那么多地方,发现香港的医保体系最好,“想死都没有机会”。他举个例子,前不久脚痛,被怀疑是通风,救护车一来,马上被送进去住院。住了三天,才三百多块。
他说这话时,我想起我在街上拍的一张标语——发对急诊室加价。“即便是急诊室加价到180块,也没多少。”在阿张的言谈中,他对香港人病得起感到幸福。阿张有小小的心脏病,“但我每年都回去检查,一不舒服就挂急诊就看医生。说,如果在心脏安支架,按理说必须自己掏钱,但也可以向政府申请补助,社工会来跟你谈申请事宜。
回归二十年,阿张说,中国越来越强大。他不信有人有能力推动港独,也不可能得逞,首先香港没有资源,“就说水吧,一旦深圳掐断了,你就死了!”这些人就是有不满情绪,能有什么本事独?政府不要怕!
我希望阿张与其次子,再拍一张合影,这样有了直观的对照。但阿张似有危难。尽管他家是我熟悉的场地,记得2004年我在香港搭早晨的去欧洲的班机,还在他家借过宿。这晚兵临城下,我最后还是没有被要求上去坐坐,也许有什么不便。其实我也跟他交待,吃完饭,坐一会儿我回宾馆去做爱做的事了。各有各的不便。
真正的君子之交,是不苛求,不强迫,不超越,不黏人。我在想,我与阿张的佬友之情能维持30年,最主要是没有利益来往。所以,实现了淡如水的境界。
明早喝早茶!
再说,起来后八点半定。
得!
作者:卓越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