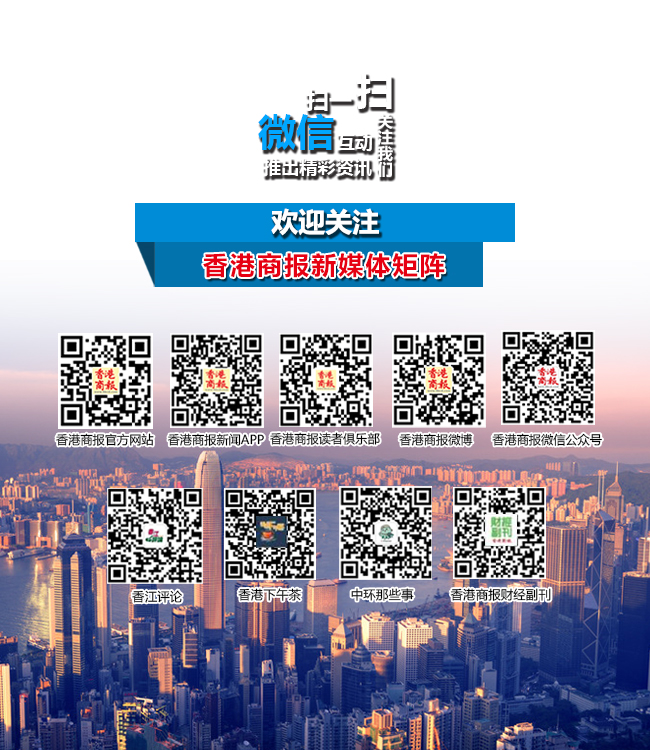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香港商報網訊】昨日,全國港澳研究會在深圳舉辦「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紀念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國際研討會。會上,英國專家艾琳·麥克哈格表示,在英國,權力的地域分佈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而地方自治和國家統一之間的平衡是當前充滿大量爭議和緊張的一個問題。的確,鑒於蘇格蘭和北愛爾蘭都存在著重大的分裂主義運動,英國目前狀態的延續性是高度不確定的。
在致辭中,艾琳·麥克哈格概述了英國當前憲法的領土規範的主要特徵,以及一些具體的緊張點;分享了英國試圖在地方自治和國家統一間取得適當平衡的經驗中汲取的教訓。
一、英國憲法的領土規範的主要特徵
英國憲法的領土規範的兩個主要特徵需要在這裡強調一下:
1、不對稱
第一個是不對稱。英國由四個地區單位組成:英格蘭在地理面積和人口規模上都是最大的一個,它約占英國總面積的54%、總人口的84%;其次是蘇格蘭,約占總面積的32%,只占總人口的8%;威爾士約占總面積的9%、總人口的5%;最後是北愛爾蘭,約占總面積的6%、占總人口不到3%。
英國四大組成部分的治理存在很大的差異。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都有權力下放的政府體制,如直選政府、對地方性政策行使立法權,然而令人困惑的是,這三個地區的法律權力和體制結構又各不相同。這些體制目前的形式始於1999年。但是,這些體制是建立於先前已存在的領土治理差異之上。例如,在1921年到1972年之間,北愛爾蘭有了較早期的立法權下放體系,然而在蘇格蘭,自1707年蘇格蘭和英格蘭合併開始,蘇格蘭就一直保留著獨特的治理特色,包括獨立的法律體系,而更廣泛的行政權力下放則發展於1885年之後。在1999年之前,威爾士的治理並沒有太與眾不同,不過從1960年代開始它也開始有了一些行政權力的下放。
但是,英格蘭沒有單獨的權力下放體制。這意味著威斯敏斯特的英國議會在擔任整個英國的某些“保留事項”(如國防或外交事物)中擔任立法角色的同時,也是英格蘭地區性事務(如健康或教育)的立法機構。鑒於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下放立法機關的權力各有不同,因此英國議會有時需要代表英格蘭和威爾士,或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或英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英國政府由英國議會產生,並對其負責,同樣,有時代表整個英國,有時僅代表英格蘭,有時代表各地區的不同組合。
雖然英格蘭沒有立法權,但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英格蘭試圖建立民選地區議會。不過,除了大倫敦議會外,該計劃由於缺乏民眾支持而被放棄。最近,具有誤導性名字的“城市放權”計劃在英格蘭展開。但是,這實際上是地方政府的增強形式,沒有單獨的民選議會,也沒有立法權。
英格蘭沒有單獨的政府或立法機構意味著當前的權力下放制度實質上是對少數族裔的一種保護。換句話說,它通過一定程度的擴大地方自治,試圖防止英國少數族裔選民在特定地方關注事項上的利益或願望被英格蘭在英國國家級別的代表機構中壓倒性的優勢所壓倒。
2、議會主權
英國憲法的領土規範的第二個主要特徵是,議會通過其通過的法規把就特定事項進行立法的權力下放給蘇格蘭、威爾士、北愛爾蘭並不影響英國(威斯敏斯特)議會的主權。議會主權仍然被視為英國憲法最重要的原則。這意味著英國議會頒佈的立法被視為最高法律形式,英國議會可以頒佈的立法沒有法律限制,並且法院不能推翻英國議會的法案(譯者注:由於議會至上原則,英國法院不能宣佈議會通過的法律是“違憲”,但由於法院根據Human Rights Act 1998可以判斷爭議的法律是否符合人權法案,因此如果法院認為某法律或其中某一條不符合Human Rights Act,會在實際中導致該法無法繼續運行,與宣佈該法律“違憲”在效果上一致)。英國的所有其他憲法原則都在議會主權的前提下運作——充其量只是解釋性原則,更籠統地說是政治限制。
議會主權的重要性對權力下放具有三大影響。首先,沒有指導和限制權力下放發展的約束性憲法原則。是否應該建立權力下放的機構,以及如果要建立,應行使什麼權力,這些問題本質上是政治問題。因此,英國權力下放的發展遵循的是政治邏輯而非憲法邏輯。與其以一致的憲法視野為指導的同時,實際上已經存在三個獨立的權力下放過程,以應對各種不同的政治壓力。在蘇格蘭,權力下放本質上是對民族主義情緒在政治上日益重要的一種回應,即是為響應當地強烈的需求而發展的。在北愛爾蘭,1999年恢復權力下放是一種折衷辦法,以結束由國際協議(貝爾法斯特協議,又稱1998耶穌受難日協議)引發的工會主義者(支持英國)和民族主義者(支持愛爾蘭統一)之間的社區間暴力。在威爾士,權力下放是一個更加謹慎和漸進的分權過程,目的是提高威爾士治理的反應能力和責任性(儘管威爾士也有民族主義運動,但比蘇格蘭或北愛爾蘭要弱得多)。鑒於歷史上英格蘭地區一直沒有強烈的需要與英國區隔,英格蘭沒有權力下放也反映了人們對此缺乏需求。(但是,權力下放的一個重要副作用是英格蘭人往往會對蘇格蘭人、威爾士人和北愛爾蘭人懷有敵意)。
議會主權繼續運作的第二個影響是,權力下放機構的存在和權力沒有在法律上得到鞏固。它們是由《議會法》創立的,同時也可以被《議會法》修正,甚至可以被廢除。此外,權力下放的立法機關和政府在立法和行政權限上有嚴格的法律限制,要遵循廣泛的執法機制,防止它們影響英國國家級別的政策事務,但英國議會的立法權卻沒有同等的法律限制以防止其影響權力下放地區的事務。
因此,權力下放機構的存在和自治取決於政治而不是法律上的保障——民眾對權力下放的支持可由頒佈前的公民投票和憲法公約(Sewel動議或legislative consent motion同意立法動議)證明。Sewel動議規定,未經有關權力下放立法機關的同意,英國議會通常不得就已經下放到地方的問題進行立法(包括關於現有權力下放政策問題的立法以及改變權力下放權限範圍的立法)。最近,Sewel動議成為蘇格蘭和威爾士法律上的立足保障,其保證蘇格蘭和威爾士的下放機構是英國憲法的永久組成部分,除非再次進行公民投票,否則不得廢除。但是,按照對議會主權的正統理解,這些規定不具有約束未來議會的能力,因此僅具有象徵意義。確實,在R(Miller)v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xiting the European Union一案中,對Sewel動議的法定承認對其法律地位沒有任何影響。它仍然是通過政治手段強制執行的憲法公約。因此,最高法院拒絕就權力下放的政府與英國政府之間關於Sewel動議是否涉及觸發英國脫歐的立法糾紛作出裁決。
議會主權為權力下放的發展和防禦留出了很大的政治空間,這一事實引起了第三個影響,即它允許對權力下放的憲法意義進行相互解釋。一種觀點認為,英國仍然是一個統一國家,在這裡,權力下放是對地方自治的有限和可撤銷的讓步,而權力下放的機構顯然是從屬�英國的。另一種觀點認為,權力下放是一個更加多元化的聯盟或准聯邦國家的證據,在該聯盟中,地方自治被理解為在被下放地區中行使人民主權的產物。按照這種觀點,權力下放產生了受約束的憲法秩序,在這種秩序中,英國政府和權力下放的各級政府之間在彼此平等的基礎上共享治理權限。不足為奇,這些觀點中更傾向哪一個取決於觀察者視角的變化,取決於是否強調法律或政治因素。它也可能取決於地理位置——在英格蘭和英國國家級的機構中,統一國家的觀點往往更為普遍,而在下放地區,聯邦或准聯邦國家的觀點更為普遍。最後,這也可能取決於政治說服力。民族主義政黨極力主張地方自治,而反對權力下放的保守黨則傾向於貶低其憲法意義(最近有證據表明,政治右翼對權力下放的敵意越來越大)。
二、緊張與問題
這種不對稱治理與議會主權的結合非常容易造成主權者與自治地區之間的緊張。在放權初期,工黨在英國國家層面、蘇格蘭和威爾士都是執政黨,緊張關係部分被緩和了。但是,由於政治分歧,緊張局勢開始出現。首先是在蘇格蘭,(獨立派)蘇格蘭民族黨(SNP)自2007年以來一直是蘇格蘭的執政黨,自2010年開始,保守黨一直是英國的執政黨。2016年6月舉行的是否留在歐盟的公民投票結果進一步加劇了緊張局面,當時全英國52%的選民投票贊成退出歐盟,但蘇格蘭和北愛爾蘭的多數選民投票留在歐盟。考慮到權力下放和歐盟決策權限的交集,退出歐盟(脫歐)對權力下放機構具有直接影響。但它在更廣泛的範圍內也具有政治上的不穩定作用,尤其是在北愛爾蘭,人們認為這會干擾1998年《貝爾法斯特/耶穌受難日協議》在英國、愛爾蘭和北愛爾蘭政府之間達到的平衡,而且蘇格蘭一直有獨立的想法,甚至在威爾士,(統一派)威爾士工黨政府因英國政府對權力下放的不敏感性感到不滿。最近,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的處理又造成了進一步的緊張局勢。
這些緊張關係已經與憲法的領土規範的四個方面產生了關係。
1、保護地方自治
在英國脫歐之前,Sewel動議一直有力地保護權力下放之下的自治,促進了英國與權力下放政府之間在相交權限領域的合作。但是,英國脫歐對Sewel動議造成了嚴峻的考驗。
首先,面對被拒絕的權力下放,首次頒佈了一系列與英國脫歐有關的影響下放權限的立法。在最高法院拒絕就米勒案適用Sewel動議作出裁定之後,由於英國政府繼續堅持不採納Sewel動議,因此,在未征得下放政府(譯者注:即蘇格蘭議會、威爾士國民議會和北愛爾蘭議會)同意的情況下頒佈了《2017歐洲聯盟(退出通知)法》。更成問題的是,儘管英國政府承認這些法規確實影響了英國的權力下放,但隨後的兩項法規(《2018歐洲聯盟(退出)法》和《2020年歐盟(退出協議)法》)也未經下放政府同意而通過。Sewel動議指出,一般情況下需要獲得權力下放政府的同意,因此可以辯稱,在英國脫歐這種異常情況下,允許不經過權力下放政府的同意。然而問題是,英國政府沒有解釋為何以上關於脫歐的法規可以未經下放政府同意即頒佈。相反,英國政府某種程度上重新解釋(並削弱了)Sewel動議,一方面它要求徵求權力下放政府的同意,但另一方面如果國議會認為它們會不合理地拒絕同意,則毋需一定要獲得權力下放政府的同意。
此外,《2018歐洲聯盟(退出)法》的一個影響是改變權力下放權限的範圍,以使蘇格蘭議會通過的一項法案追溯無效——英國從歐洲聯盟退出(法律連續性(蘇格蘭))條例草案。此外,它還創建了一個程序(迄今尚未使用),使英國部長可以通過二級立法的形式,改變權力下放權限的範圍。此程序受“同意機制”的約束,但它再次允許推翻下放政府拒絕同意的某些事項。
這些事件造成英國與權力下放政府之間的信任嚴重破裂,並直接導致各議會對保護權力下放自治的Sewel動議也失去了信心。
權力下放的局限性
英國與下放政府之間在英國脫歐事件上的緊張關係有一個關鍵點,即迄今歐盟層面行使的決策權限應分配在哪裡。權力下放政府認為,按照權力下放的保留權力模式(除非明確保留給英國,否則政策將下放),解除遵守歐盟法律的義務應意味著歐盟在一些領域的權限應在脫歐後權力下放,如就農業、漁業或環境政策進行立法的權力。但英國政府認為如果這些立法權力和政策執行權力一概下放,在歐盟法律的共同限制解除後,英國內部市場的完整性以及其未來貿易政策的執行將大受影響。
因此,英國脫歐使這些從未被系統性厘清的重要問題浮出水面,包括地方自治與國家統一之間的邊界何在。過往的經驗顯示,權力下放是在路徑依賴和本地需求的驅動下以臨時方式分配和擴展的。正如已經指出的那樣,這導致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在決策權限上有很大差異。在英國脫歐之前,各方認為應當給予地區更大的自治權,而沒有過多考慮這樣做會給維持國家統一帶來影響。例如,《2016蘇格蘭法令》(2014年蘇格蘭獨立公投失敗而獲得通過)頒佈,對福利政策和蘇格蘭憲法各方面的權力(如投票權)進行下放,這有可能會危害英國公民權。可能損害公民權的例子還包括失去統一的來自上層的標準,例如,英國脫歐可能失去歐盟對個人權利的保障,或者保守黨繼續威脅要廢除《英國1998年人權法》。
儘管人們意識到有必要在地方自治的基礎上保留促進國家統一的政策,但往往我們很難意識到需要對權力下放的邊界進行限制的重要性。但現在這已經變成很難解決的問題,因為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和英國政府之間的關係非常差,政治分歧嚴重。此外,如果要促成大家達成共同標準,可能需要收回一些下放的權力,這讓問題的解決變得更難了。
2、政府間關係
第三個問題是政府間關係。鑒於保留/權力下放的邊界錯綜複雜,在任何決策權分散的系統中,不可避免的是某些問題將涉及相重疊的權限和/或具有的溢出效應,以及權力下放資金安排的複雜性,因此,明顯需要英國政府和權力下放政府在某些問題上密切合作,並需要建立解決爭端的機制。儘管1999年已經制定了包括聯合部長理事會在內的政府間工作的既定安排,但政府間關係依然是當前權力下放安排中最薄弱、最常受到批評的一點。當前的體系主要在非成文法基礎上運行,目前的體系由英國政府主導,並由英國政府自行決定,並沒有獨立的爭議解決機制。
鑒於英國政府在有些問題上扮演英格蘭政府的角色,但在其他問題上卻又扮演著整個英國政府的角色,這種雙重角色使英國政府的統治地位有很大問題。在最近的新型冠狀肺炎的危機中這一點所引起的困難顯而易見。儘管事實上解決病毒大流行的關鍵權力,包括公共衛生政策和執行的權力,是由權力下放政府行使,但英國政府一直期望可以在整個英國範圍內採取協調一致的應對措施。地方政府堅持根據當地情況做出自己的決定,例如,關於如何以及何時解除封鎖的決定,英國的領導人對此顯然感到受挫。對地方政府領導而言,同樣感到受挫的是,英國政府未能明確表明新宣佈的措施何時僅適用於英格蘭,以及未能就具有重要跨區影響的英格蘭政策進行磋商。
3、分離權
緊張關係最後涉及到的領域是分離權。最近的領土爭端極大地推動了分離主義運動。在蘇格蘭,蘇格蘭民族黨政府認為,英國未經蘇格蘭的多數同意而退出歐盟構成了第二次獨立公投的理由,並且它已明確表示打算在不久的將來舉行公投,目前該計劃已因為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大流行暫時被擱置。英國脫歐還意味著愛爾蘭獨立的可能性大增。儘管威爾士支持獨立的比率比蘇格蘭或北愛爾蘭低25%,但這也是有史以來最高水平。
主權統一(和/或英國議會至上的權力)顯然是所有三項權力下放法規中的保留事項,因此,根據英國的法律,沒有這樣的分離權。但是,《貝爾法斯特/耶穌受難日協定》保障了在愛爾蘭可舉行所謂的“邊境民意投票”的權利,並在《1998年北愛爾蘭法》第1條中也明確承認。儘管威爾士或北愛爾蘭沒有同等的法定權利,在蘇格蘭民族黨在2011年蘇格蘭議會選舉中獲得多數票並承諾舉行公投後,2014年英國政府準備與蘇格蘭政府進行合作舉行獨立公投。
然而,未來舉行獨立公投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如果多數人投票贊成北愛爾蘭獨立,根據《北愛爾蘭法》,其可以要求英國政府進行邊境民意投票(至少間隔7年)。但是,最近北愛爾蘭上訴法院拒絕了嘗試要求英國政府制定政策以決定是否通過法定測試,如果通過,在何種條件下進行民意投票。在蘇格蘭,也有正在進行的訴訟,旨在闡明蘇格蘭議會是否具有單方面的權力授權另一次獨立公投,或者是否需要更清楚的授權性英國立法。然而與此同時,英國政府拒絕了蘇格蘭政府提出的第二次獨立公投,目前尚不清楚在什麼情況下,或是否有可能說服英國政府改變主意。
在上述對憲法的領土規範不同理解的背景下,各地方對分裂合法性的不確定和分歧有可能造成嚴重的憲法危機。必須要有有效的治國之道來遏制分裂主義的壓力,而不能僅僅通過高壓來維持國家領土完整。
三、英國的經驗教訓
總而言之,英國目前看起來更像是一個在面臨分權的情況下如何維護國家統一的例子,而不是一個成功的領土自治模式。英國的憲法的領土規範高度不穩定,面臨著瓦解的壓力。也許可以得出一些具體的教訓。
首先,不對稱的權力下放不僅僅是地方利益的問題,它影響著整個國家的憲法和治理。
其次,很容易造成緊張和不滿。要有效地管理,需要明確且可執行的基本規則以及對這些規則的相互承諾。
第三,非對稱的權力下放是保護少數派的一種形式,在這種情況下,多數派要自製。這就需要中央政府認真處理,對差異保持敏感,以避免積怨。
最後,重要的是在關注國家統一的同時也要關注地方自治的需求,換句話說,要同時培養國家和地方的認同感。如果地方是迫於高壓而不是協商同意而受制於國家,或者只出於一時的策略性考慮,那麼國家的領土完整也將一直處於危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