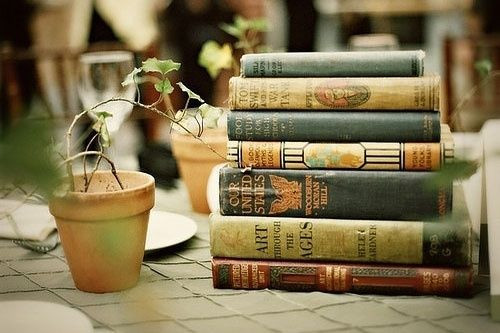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近日公布的第十一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显示,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的纸质图书阅读率为57.8%,较2012年上升2.9个百分点;2013年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50.1%,较2012年上升9.8个百分点;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7本,比2012年增长0.38本。
阅读率上扬意味着国民阅读在量上有所增长,但阅读量的增长并不等同于阅读品质的提升。提倡全民阅读,或许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注到提升阅读品质方面,让更多的人认识并了解阅读的真正意义。对此,记者采访了几位文化学者和专家,就读书、择书智慧以及高品质、有营养的阅读发表了见解。
读书不能随性 经典永不褪色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张柠当年从广州调至北京工作时,他和家人没有带任何电器、家具等,唯一打包托运的就是一箱箱书。这些书一直整齐地排列在他客厅的书架上,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谈到如何有选择地进行高品质阅读,张柠说,今天不是无书可读,而是面临信息膨胀所带来的“选择恐惧症”,有很多书只能说它无毒,不能保证它有营养,所以读经典是个稳妥的选择,这些经典穿透时空的阻隔和地域的界限,在每个时代、每个地点都产生相似的共鸣效果。他建议读者要有自己的阅读目标,围绕某些主题进行有价值的阅读。
文化学者朱大可谈到阅读品质的提升和对书目的筛选时说:“我一般不阅读畅销书,只读思想史或文学史所推介的、在人类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图书。这种选择可以使人直接阅读思想原典,而不需要在垃圾书上浪费时间。”
三联书店总编辑、资深出版人李昕一直呼唤有价值、有品质的阅读,在他看来,提高人均阅读量的绝对数,并不意味着提高全民阅读质量。“对读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读什么。我认为,读者需要阅读两类书:一类是能够提升思想修养、认识水平,富有人文精神和思想智慧的书籍;另一类是陶冶性情、愉悦身心的文艺类书籍。要多读古今中外名家大师的经典之作及当下广受好评的书籍,它们有助于读者对现实、对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李昕说。
从上世纪70年代至今,知名媒体人、文艺评论家解玺璋所有“私房钱”只用于买书这一件事,家中的藏书量比一般的图书馆还丰富。“对于有职业需求的人来说,读书不能太随性,还是要有目标、有想法地去读。”解玺璋说,“我常常定期围绕一个主题去阅读,比如我当记者跑戏剧、影视口时,就把所有中外戏剧和影视的书都买来阅读;我写《梁启超传》时,就通读有关梁启超的书。”他认为,要读好书首先要选择信得过的作者,比如专业书就选相关专业里最权威和有说服力的作者,像文史类书籍选陈寅恪等大家的著作;其次要选严肃认真的优质出版社,比如古文类书就选中华书局等。
急功近利进入不了书中世界
谈到高品质书籍对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塑造,这些专家和学者有着各自丰富的内心体验。
“阅读是思想的发动机。”在张柠看来,书本内外有着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书外的世界是大家所熟知的世俗世界;书里的世界是一个陌生的空间,它有自己的一套历史悠长的逻辑。急功近利地读书,带着这个世界朝九晚五的逻辑是进入不了书中的世界的。只有带着感情去阅读,把个人的感受和生命体验倾注进去,才能抵达文学作品的核心。
艺术家陈丹青之所以热衷于读好书,是因为每次读书他都发现自己知道得太少,通过读书他领悟到做人不要自以为是,要自以为非。“我觉得用心读书比用脑子读书更重要。我看的第一本书是英国的《流浪儿》,《牛虻》这本书当年是偷来看的,巴尔扎克、普希金、托尔斯泰、狄更斯、哈代等人的作品对我影响非常大,很多好书讲出的道理我都觉得很透气。”
北大中文系教授、评论家陈晓明说,我们这代人多是通过商务印书馆的那套汉译学术名著打下的学术底子,上世纪80年代初,商务印书馆开始陆续出版汉译学术名著,尤其是康德、黑格尔构成了我们最初的学术根基。具体到我个人,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书,之后我的阅读进入到更加专业的层面,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等。
“微时代”下仍需品质阅读
对于“微时代”下网络浅阅读对传统纸质阅读造成冲击这一现象,朱大可说:“深阅读和浅阅读的选择,取决于每个人的生活目标及其经验。我个人在浅阅读方面无法获得快感,如果需要放松,我宁可在iPad上看欧美大片。我肤浅的快感来自图像文本而非文字。但一般而言,深浅阅读应该适当搭配。”
“浅阅读是需要的,但止于浅阅读是不够的,要保证阅读的品质还有赖于深阅读。”在李昕看来,长期被动接受浅阅读的人,不仅思维得不到训练,就连阅读复杂文本的能力也会降低。而深阅读是伴随思考的阅读,能通过训练实现分析力、概括力、判断力、联想力的全面提升。
在张柠看来,“微时代”阅读所特有的“撕裂性”直接影响着阅读的品质。今天的媒介能够将我们试图通过传统“阅读”获得的信息和思想,迅速转化为五花八门的文字、声音和影像。“微时代的阅读”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阅读”,而是一种“观看”,甚至就是一种“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