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研究表明,贝多芬终生饱受政治力量的冲击。
贝多芬在艺术史上是个独特人物——光彩夺目,魄力惊人。他的风格不但影响了后世所有音乐家,而且塑造了整个音乐体系。专业管弦乐队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连续演奏贝多芬的交响曲。指挥的艺术是在他之后出现的。现代钢琴在音量与灵活性上的提升,也要归功于贝多芬的要求。录音技术的发展也与他有关:1931年第一张33 转的商业黑胶唱片里面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代CD光碟的时间被设定为七十五分钟,目的是能够完整容纳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音乐厅本来只是人们轻歌曼舞的休闲场所,在贝多芬之后却成了严肃艺术的神圣殿堂。聆听音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人们必须全神贯注,主动参与,才能领会贝多芬的深度和他那开创性的手法。音乐家的舞台上奏演着无形的戏剧,如同神庙传递着音乐的启示。
贝多芬最大的成就,在于为后世所谓的“古典音乐”立下了标准的范式。在十九世纪的进程中,已故作曲家的作品开始充斥音乐会曲目,大师作品的圭臬形成,贝多芬如日中天。学者威廉·韦伯(William Weber)证实,对过去的迷恋可以用精确的数学方式加以体现,那是一条上升的直线:1782年,莱比锡上演的已故作曲家的曲目占全部曲目的百分之十一,而到了187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百分之七十六。韦伯将1807年贝多芬庞大而狂暴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在莱比锡的演出视为转折点:这部作品在演出仅仅一周后,便“应听众的请求”重新演出,并且享受到最后出场的尊贵待遇。据一位乐评家记载,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也“不断接到重新演出的请求,甚至连最出众的管弦乐队也发出了这样的请求。”最重要的是,贝多芬音乐架构中那令人沉迷的复杂性——他那通过对简单动机的不懈发展,编织出庞大结构的独特手法——使得古典音乐有了重复演绎的可能。不是说巴赫、海顿、莫扎特等贝多芬以前的音乐巨人没能通过变奏的智力游戏达到让人反复聆听的地步,而是说贝多芬让反复聆听的过程变得更加诱人,不可抵抗。没有哪个作曲家像他那样努力去避免在音乐中出现令人厌倦的内容,从而让一个人愿意成百上千遍地聆听或演奏同一首乐曲。
于是,贝多芬就像被封神一般,他的阴影不仅笼罩着后世作曲家,甚至也笼罩着之前的作曲家。他在世时,人们对他的尊崇便不断增加。1810年,以富于神秘色彩的幻想小说闻名的作家兼作曲家E·T·A·霍夫曼对贝多芬第五交响曲进行了独到的点评:
贝多芬的器乐作品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强大的力量和无限的可能性。这里闪动着刺透暗夜的光芒,我们开始觉察到那来回摇摆的巨大阴影,它离我们如此之近,摧毁了我们内心的全部感受,只剩下无尽的渴望所产生的痛苦。在这痛苦中,每种欲望都随音乐的起伏而上升和下沉……贝多芬的音乐启动了掌握着敬畏、担忧、恐惧和痛苦的装置。
这是种新颖的评论。音乐被赋予了超凡和变幻的力量:乐声回荡于尘世的上空,同时改变了凡俗人类的进程。贝多芬的音乐,在某些方面符合了霍夫曼为音乐设计的这种重要角色。一代又一代过去了,贝多芬始终位列时代的前沿: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交响曲的演出与对自由的渴望被联系在一起;二战时期,第五交响曲开篇那著名的“三短一长”被用在摩尔斯电码里,意为代表着“胜利”(victory)的字母“V”;1989年,伦纳德·伯恩斯坦在倒塌的柏林墙边指挥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我们自己似乎开始在认同这种音乐的过程中编织神话,”学者斯科特·伯纳姆(Scott Burnham)写道。然而这种崇拜对后世作曲家来说是很大的阻碍,他们必须在贝多芬霸占着荣耀的领域拼命竞争。我年轻时曾想成为一名作曲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在波士顿交响乐厅看到“贝多芬”之名镶刻在舞台拱顶上,又羡叹又沮丧。它好像在说:“别想了。”
造成这种困境——一位艺术家由于太过伟大而妨害了他所从事的艺术——贝多芬本人是没什么责任的。没有迹象表明他故意打压后辈。虽然他希望后世能对他感兴趣——否则他不会保留那么多手稿——但他从未以霍夫曼等人赋予他的夸张地位自居。“音乐之外的一切事情,我都做得很糟,而且愚蠢,”他曾经这样写道。而音乐则是用来进行严厉的自我批判的。历代听众都把贝多芬晚期的弦乐四重奏视为西方艺术的巅峰之作,但他对出版商谈论这些作品时却说,“感谢上帝,里面的想象力匮乏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个评论在将近两百年后仍然令人吃惊,不仅因为这是对自己刻薄的低估——就如莎士比亚认为“《暴风雨》不像我早年的戏剧那样平庸”一样——还因为它对当代音乐生活是种无形的挑战。不去演奏在世作曲家的作品,而是演出贝多芬的作品,就是展示匮乏至极的想象力。
关于贝多芬的书籍不断增多,体现出这种狂热的崇拜正在持续增加。今年夏天,作曲家兼评论家扬·斯瓦福特(Jan Swafford)出版了近千页的贝多芬传记《贝多芬:苦闷与成功》(Beethoven: Anguish and Triumph),而在此前出版的贝多芬相关著述还包括:约翰·苏赫特(John Suchet)的《贝多芬:启示者》(Beethoven: The Man Revealed)、尼古拉斯·马修(Nicholas Mathew)的《政治贝多芬》(Political Beethoven)、马修·圭列里(Matthew Guerrieri)讨论第五交响曲开场动机的文化史意义的《前四个音符》(The First Four Notes)、迈克尔·布洛伊(Michael Broyles)的《贝多芬在美国》(Beethoven inAmerica),以及桑福德·弗里德曼(Sanford Friedman)的小说《与贝多芬对话》(Conversations withBeethoven)。这些书都是最近三年出版的,它们已加入浩如烟海的贝多芬研究文献的行列里。研究贝多芬的专著最早可追溯至1827年,当时贝多芬去世仅几个月,约翰·阿洛伊斯·施罗瑟(Johann Aloys Schlosser)便为他立传,对他的地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的艺术成就,是其他人望尘莫及的。”
斯瓦福特的书并非研究论著,而是对贝多芬其人其乐的综合介绍。这本传记是自十九世纪美国图书馆员亚历山大·惠洛克·塞耶(Alexander WheelockThayer)撰写的多卷本贝多芬传记以来篇幅最长的英语贝多芬传记。在简介中,斯瓦福特表示自己喜欢塞耶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叙述风格,而对现代音乐学的修正主义不感兴趣。他写道,“在为同一位艺术家作传的历史过程中,是时候抛开过去积累起来的学说和立场,还艺术家一个清晰实在的本来面目了。”梅纳德·所罗门(Maynard Solomon)在其1977年的贝多芬传记中,对贝多芬进行了弗洛伊德式的分析,斯瓦福特与这种作传的角度也保持了距离。虽然斯瓦福特没有掩饰作曲家身上不那么讨人喜欢的特质——他的无礼、粗鲁、酗酒和偏执——但其塑造的贝多芬形象大体上仍是令人钦佩的。
霍夫曼在1810年的文章里将贝多芬归于浪漫主义。斯瓦福特认可的是一种较新的倾向——所罗门和钢琴家查尔斯·罗森(Charles Rosen)所采纳的观点——将贝多芬视为启蒙精神最后的体现者,认为他最看重的是受理性约束的自由思想。他“从未真正受到浪漫时代的影响”,斯瓦福特写道。从这个角度看,贝多芬反而是信守了他的家乡波恩盛行的理想。在科隆王位候选人、哈布斯堡皇帝约瑟夫二世之弟马克西米利安·弗兰兹的治理下,波恩曾一度绽放过精神之花。斯瓦福特不是第一个注意到贝多芬的成长环境有多么幸运的作家:贝多芬的祖父,出生于佛兰德的音乐家路德维希·冯·贝多芬,曾任波恩管弦乐队的指挥;他最重要的老师克里斯蒂安·戈特洛布·尼弗(Christian GottlobNeefe)则向他灌输了先进的文学理念。贝多芬刚二十出头,就在博爱的感召下打算为席勒的“欢乐颂”谱曲。而从更现实的层面上来讲,正是由于波恩与首都维也纳关系密切,贝多芬才有机会于1792年前往维也纳。
斯瓦福特生动地描绘了贝多芬在维也纳第一年的生活:他如何以作曲家及钢琴家的身份初获认可,如何以谨慎的态度面对资助人和评论家;耳聋症兆出现时他的恐惧,还有他明显的自杀倾向;以及他如何凭借“英雄”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热情”奏鸣曲、“华伦斯坦”奏鸣曲和“拉苏莫夫斯基”四重奏在十九世纪初宣布自己的横空出世。拿破仑颠覆欧洲传统秩序,与贝多芬引发音乐界革命处于同一时期。贝多芬对法国革命抱有一种模糊的好感,他甚至盘算着要搬到巴黎。斯瓦福特因而相信,“英雄”交响曲是对“英雄领导者和仁慈君主所拥有的改变自己和改变世界的力量”的致敬——一场经过革命检验的启蒙。有传闻称贝多芬听说拿破仑称帝后,一怒之下撕掉了手稿上写着拿破仑名字的题献页,然而斯瓦福特认为,这个传闻里有太多捏造的地方。他确实去掉了“以波拿巴为名”(titled Bonaparte),但保留了“因波拿巴而创作”(written on Bonaparte)这句话,而且即便拿破仑加冕后,他仍然称这部交响曲为他的“波拿巴”。1806年,这部作品最终以“英雄交响曲”为名出版,可能更多地是出于现实上的考虑:当时奥地利正与法国交战,若取名为“拿破仑交响曲”,未免太过不合时宜。
斯瓦福特对“英雄”交响曲有一章非常精彩的评述,让这首早已被人熟悉的曲目重现了新鲜气息。他展示了贝多芬独辟蹊径的作曲手法:并非层层展开,而是根据他早年的舞剧“普罗米修斯的生民”里的轻快主题进行一系列繁复的变奏,并以拼合的形式衔接在一起。第一乐章降E大调的宏阔主题与变奏主题存在联系(都围绕降B音进行展开),并突然落在不和谐的升C音上——比“普罗米修斯”主题的转调更纯熟的转位处理——营造出一种不稳定的效果,渲染了管弦乐强烈的表现力,让冲突直到乐章的末尾才得到解决。此外,通常给人留下狂暴印象的贝多芬,素来抱定一种基本的创作理念,在这部作品里却特意展现了他对舞蹈韵律的得心应手与热爱。斯瓦福特别出心裁地把“英雄”交响曲的末乐章——主题来自流行舞蹈Englische——与席勒在一封信里将Englische视为理想社会的象征联系在一起。席勒期待,在这种理想社会里,“每人都能发展自己的天赋,而且不会妨碍到别人……每人都享有自己的自由,同时也尊重别人的自由。”
《贝多芬:苦闷与成功》富于感情,旁征博引,比英国电视节目兼电台主持人苏赫特那本油腔滑调的传记优秀得多。苏赫特的传记在史料不足之处会添入虚构的成分,比如贝多芬与海顿的对话。但斯瓦福特的传记既不像所罗门的那样简洁,以区区四百页就横贯贝多芬的一生,也不像威廉·金德曼(William Kinderman)和刘易斯·洛克伍德(Lewis Lockwood)分别于1995年和2003年出版的著述一样充满独到的洞见。一个冷酷的编辑可能已经删掉斯瓦福特很多重复夸张的表述了(“当然音乐里还不曾出现过如此曼妙而深刻的平静与田园式和睦”)。
然而,斯瓦福特充满激情的表述富于感染力,这会促使读者重新关注那些著名和冷门的作品。我发觉自己迷恋上了“竖琴”四重奏,这部作品创作于1809年,属于过渡时期之作,几乎从未得到过关注【但有一份专门研究它的论述:马康德·萨卡尔(Markand Thakar)的《寻找“竖琴”四重奏》(Looking for the ‘Harp’ Quartet)】。斯瓦福特在“竖琴”上花了两页的篇幅,来探讨第一乐章里容易让人记住的小模式——各乐器在第一主题的末尾处相继采用拨弦的形式——是怎样变得越来越重要的。确实,拨弦多得几乎有些反常,让乐曲的结构显得不够稳定,听上去也有些吵闹。你会觉得,贝多芬最初好像是以为自己在写那种大众喜欢的短命作品,但之后你会发现,乐曲正稳步朝深刻与复杂的方向发展。也许他一开始就打算偏离正道。聆听贝多芬的享受,可与阅读乔伊斯的乐趣相提并论:最疯狂、最不可理喻的解释,或许恰恰是正确的解释。
贝多芬是怎样成为被后世尊奉的那个贝多芬的?是什么促成了威廉·韦伯所说的“音乐趣味的伟大转变”,让音乐厅不再那么重视在世作曲家,而是反复演出已故作曲家的作品?最简单的答案,也许是贝多芬实在太伟大了,后世不得不向他低头。但历史不会给人超级英雄漫画里的待遇。这位作曲家也是时势造英雄,他碰巧在最成熟的时候赶上了霍夫曼这样的理性听众迎接不世出的天才,迎接开拓音乐领域的帝王。学者马克·埃文·邦兹(Mark Evan Bonds)在新书《绝对音乐》(Absolute Music)中写道,“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人们越来越相信,音乐有能力以文字所不及的方式揭示宇宙的‘奥秘’,音乐家其实是处于神与人之间的神使。”正如邦兹所观察到的,人们会谈论莫扎特的天赋,但并没有把他称为“一个天才”;而贝多芬呢,天才成了他明确的本体身份,是自身塑造而非上帝的赐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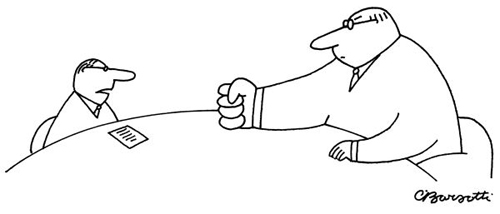
“如果你要用这种方式解决,那好吧。”
政治对贝多芬获得崇高地位也有推动作用。拿破仑战争打破了欧洲传统格局,终结了神圣罗马帝国,这种无序的状态让很多人转投音乐,将音乐视为避难所。在混乱的局面下,贝多芬显露出了最高的威望。而且,霍夫曼1810年对第五交响曲的评论显示出贝多芬名望的快速增加,这种名声飞速增长的状况符合了二十世纪初思想家卡尔·施密特定义的“政治浪漫主义”倾向——对消失的中世纪基督王国和神话国家怀抱的泛德式思愁。贝多芬虽然有着相信四海一家的启蒙思想的背景,但对这种愁绪也并非无动于衷。最近的一些研究,尤其是马修的《政治贝多芬》和斯蒂芬·拉姆夫(Stephen Rumph)2004年的著作《拿破仑后的贝多芬》(Beethoven AfterNapoleon),着重关注了贝多芬晚年的关系变动,探讨了甚至包括超凡脱俗的晚期四重奏在内的作品里的政治内涵。这类讨论也许会被斯瓦福特当作装腔作势,但它对贝多芬现象诞生的原因提供了新的解读。
拉姆夫和马修分别任教于华盛顿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他们在作品中都研究了常见曲目——第三交响曲、第五交响曲、第九交响曲、“菲岱里奥”和“庄严弥撒”——同时也关注了很多贝多芬爱好者所忽视的宣传性作品。拿破仑于1809年占领维也纳时,爱国情感正在奥地利人民当中滋生。贝多芬早年虽然热衷法国,但当时也有了反对法国的倾向。1813年,他写下战争交响曲“惠灵顿的胜利”,来纪念惠灵顿在维多利亚击败拿破仑;一年之后,他又创作了华而不实的清唱剧“光荣时刻”,来歌颂维也纳会议和奥地利的复兴。早期学者认为这些作品浪费了贝多芬的天赋,或把它们当作讽刺及模仿的习作。而拉姆夫和马修则认真对待了这些音乐,认为它们是贝多芬向晚期过渡的作品。拉姆夫指出,“惠灵顿的胜利”结尾处极快的二重赋格,预示了第九交响曲临近结尾处的对位的欢庆。贝多芬自己也对这些作品比较满意,他在批注一份否定这些作品的评论时写道:“我拉出来的东西,比你的任何思想都要强。”
长期以来,传记作家一直坚称,拿破仑时代的动乱和随后的王朝复辟让贝多芬遁入了一个隐秘的空想世界。他们还认为,听力的丧失让他远离了日常事务。相比之下,拉姆夫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形象,展示了一个信念趋于保守、越来越信奉“政治浪漫主义”里的民族审美性的作曲家心神不宁的状态。贝多芬晚期的印记——对已故大师的兴趣与日俱增,尤其喜爱巴赫与亨德尔;热衷于复调和对位;对自由奔放的、有时显得不够成熟的抒情民歌产生浓厚的爱好——体现出来的不是进步,而是紧缩倾向。在这些作品里,甚至在第九交响曲中,晚期的理想主义突然出现,表达方式变得有些保守,末乐章开头部分骄傲的男低音独唱——“哦朋友,不要用这样的声音!”——仿佛在宣称这是对权威的救赎之声。
马修在《政治贝多芬》里提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的观点,然而他的阐释所蕴含的意义具有惊人的广度。在他笔下,贝多芬从作曲生涯之初便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进行永恒的抗争:书里有些地方描绘了拿破仑时期维也纳的战时图景,号角声、进行曲和战争歌曲响遍大街小巷。贝多芬接纳了这些战争元素,把它们转化成了更纯粹的器乐语言。这种置换,在马修认为“以全部的号鼓、赞美诗与壮烈爆发营造出政治气氛”的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里体现得甚至更为明显,只是没有明确的政治指涉罢了。第九交响曲的末乐章里含有被某些重要使命所激发和唤醒的强烈能量。但这是什么重要使命?埃斯特班·布赫(Esteban Buch)1999年的著作《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一段政治史》(Beethoven’s Ninth:A Political History)记载了这部交响曲在不断循环的语境中的地位,从德国的沙文主义到马克思信徒的国际主义,再到以“欢乐颂”作为“盟歌”的欧盟的自由主义。
“晚期的音乐把听众变成了诠释家,”马修写道。历史和伟人的光环在我们耳边展开,冲向未来,让我们陷入疲于奔命的阐释中。这,或许就是贝多芬现象的核心。他拥有空前的自主性,哪怕面对资助自己的贵族,他也决不低头。他的大多数重要作品都冠以奏鸣曲、四重奏、协奏曲和交响曲之名,以抽象的、非描述性的形式传达思想。然而这种从奴性和功利中解脱出来的自由也有矛盾之处:这种音乐虽然摆脱了当下的束缚,却成了未来的俘虏。“第九交响曲和‘庄严弥撒’,”马修写道,属于“永远在寻找合适出场时机的天成之作。”由于它们压制了我们自己的梦想和热情,我们正面临将它们以空洞的方式消耗殆尽的危险。这种危险有可能让我们永远空虚。甚至已不只是一种危险了:圭列里的《前四个音符》的最后一章谈到,在E·T·A·霍夫曼笔下承载着敬畏与恐怖的工具,如今已成为毫无意义的迪斯科舞曲、嘻哈音乐、歌谣和手机铃声的片段了。
贝多芬能躲避这种似乎是命中注定的无意义的不朽吗?马修一针见血地总结道,我们需要“重新认识他身上的偶然性和不合常理之处”:他的野心,他的机遇,他的背离,他审美的偏差,甚至他的失败。“惠灵顿的胜利”和“光荣时刻”等次要作品——“差的”贝多芬——显示出作曲家容易受到低潮期的影响。如果你认可贝多芬时代的流行作品——马修举的例子是伊格纳兹·莫谢莱斯(Ignaz Moscheles)的钢琴奏鸣曲“1814年奥地利首任皇帝弗朗茨陛下返都维也纳之反响”——你或许就能对当代音乐有更多的忍耐了。经典是个巨大的幻影,随着让人失望的过去的消逝而产生。
最近的出版物里,在还原贝多芬真实命运方面最下功夫的是一部虚构作品。桑福德·弗里德曼是一位纽约作家,2010年以八十一岁高龄辞世。他凭借一系列小说赢得读者的青睐,其中最著名的是1965年的成长小说《图腾柱》(Totempole)。《与贝多芬对话》并未在他生前出版;由于关于作曲家或其他类型音乐家的知识分子小说十分稀有,《纽约书评·经典》(N.Y.R.B. Classics)便付出一系列努力助其问世。这本关于贝多芬的小说描述的并非他如日中天的时期,而是他状似老怪物一般的风烛残年的生活。
贝多芬耳聋后,曾通过笔记本与友人保持正常沟通,弗里德曼的灵感即来自于此。让人沮丧的是,这些所谓“对话录”大多只保留了别人向贝多芬说的话,而非贝多芬本人的言论:因为他只聋不哑,没必要靠书写来表达。大部分谈话都是家长里短(比如“蜡烛花了多少钱?”),有时也会冒出一些我们非常希望贝多芬回应的问题:
你在创作歌剧或者清唱剧吗?
你认识莫扎特,你是在哪见到他的?
莫扎特是一个优秀的钢琴家吗?
弗里德曼利用了这种挫折来进行创造。他以单向对话的方式叙述了贝多芬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其中很少引用笔记本里的内容,但加入了大量传记所记载的事实与合理的虚构。作曲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了沉默,弗里德曼因而得以避免落入捕捉其“真实”声音与想法的陷阱中。贝多芬的话语会转而出现在读者的想象里。尽管这种方式有些隐晦,但其效果却足够生动逼真。
小说开始于1826年7月,贝多芬十九岁的侄子卡尔自杀未遂。卡尔的不幸对贝多芬的晚年有着令人不安的决定性影响。男孩的父亲,贝多芬的兄弟卡斯帕·安东·卡尔,在1815年便去世了,贝多芬为了获得卡尔的监护权,与被他认为是“卑劣至极”和“心狠手辣”的卡尔的母亲约翰娜进行了一番争斗。在一封信里,贝多芬称她为“黑夜王后”,暗指卖淫。约翰娜的性格确实有些缺陷——她曾因偷盗珍珠项链而入狱——但还不至于被剥夺抚养子女的权利,不过贝多芬最后还是如愿以偿了。他教导小卡尔的方式往往很奇怪,常用威吓的手段,有时甚至是虐待。在《与贝多芬对话》的一章里,安东·辛德勒,一个热心但有些阴险的人,散布流言称贝多芬在某种程度上对卡尔的自杀负有责任:
我认识的大部分人都非常同情你;只有一两个人怪罪你。
这没什么区别;他们是少数。
请别自责了,这不值得。
对话就此结束,辛德勒悄悄溜出房间,下一个谈话者出现。
读遍全书,我们通过心灵的耳朵见证了贝多芬的咆哮、牢骚、烦忧、自负、蔑视、嘲笑,还有那最常见的抱怨。贝多芬经常感到痛苦,尤其是在晚年,有些痛苦是出于命运,有些痛苦是出于自身原因。斯瓦福特认为,酗酒和其他健康问题结合在一起,给贝多芬带来了致命打击。(2001年出版的《贝多芬的头发》一书推测贝多芬死于铅中毒,后来对贝多芬遗骸的检测推翻了这一假定。)在弗里德曼的小说中,医生对贝多芬便血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同时检查了他的尿液。关于金钱,又有很多争吵,几无片刻安宁。
弗里德曼对贝多芬盛怒面孔之下的温柔宽宏的一面也有展现。在令人感慨的一刻,年轻的弗朗兹·舒伯特拜访了贝多芬。舒伯特不善言谈(“上帝啊,我愿把自己多余的体重分给你!”),不安地询问大师如何看待他的艺术歌曲。“你没发觉修道院的钟声有点太响了吗?谢谢,我呼吸能顺畅点了。”这段插曲本来极有可能变成威严长者对年轻晚辈谆谆教导的感人故事;然而在后面的对话里,当贝多芬把舒伯特与自己多年的好友胡梅尔做一番比较时,我们却发现他实际上更喜爱胡梅尔那虽然优美却缺乏深度的音乐。但凡你听过大艺术家如何评论自己的继承者,你就会清楚这个情节有多么真实。
小说里,贝多芬正在创作最后一首四重奏,明亮的嬉戏般的F大调四重奏。贝多芬警告过仆人几次,让他离手稿远点。除了此处,小说里没有其他地方提到贝多芬作曲的行为。书里也提及了贝多芬在卡尔试图自杀前刚好完成的升C小调四重奏,Op.131,但谈论的主要是这部作品的题献。此曲最初准备献给贝多芬的一位友人兼资助人,但他临终前改变主意,将其改赠给斯通泰汉姆(Stutterheim),因为此人在卡尔自杀未遂后录用这个年轻人作为部下。在弗里德曼的故事里,贝多芬担心斯通泰汉姆会因为传言而反悔,便盼望通过改赠题献来让他坚定心意。贝多芬的朋友斯蒂芬·冯·布罗伊宁(Stephan vonBreuning)不相信Op.131适合这样的用途:“他无疑会受宠若惊,准确地讲是呆若木鸡!你确定要献上这样一份厚礼吗?”
131号作品最后还是献给了斯通泰汉姆。人们通常把它视为贝多芬最优秀的创作,堪比史上最伟大的作品。斯特拉文斯基称其为“不可作一处更改的出神入化之作”。这部作品有七个对比明显的乐章,意识在其间不断流动,自由组合的结构在最出色的演绎下会给人一种集体即兴创作的印象。同时,它那令人着迷的发展性逻辑也是前所未有的。乐曲开头那超凡的赋格的前四个音符经过反复的重排组合,有些很明显,有些则隐蔽到难以觉察的地步。第五交响曲开头四个音符的动机,连小孩子都能轻易识别出来,而Op.131却需要用一生去体味。(舒伯特去世前几天就曾希望听到此曲。)把这样的音乐与改赠题献所折射出来的家庭丑闻联系在一起,让人难以接受,但《与贝多芬对话》硬是把这个难题塞给了我们。这部小说拒绝刺探天才的隐秘,而是通过摄影般的手法,描绘了一颗极度不满的心灵在逆境中的挣扎。
弗里德曼写到贝多芬弥留之际时,忧郁消散了一些。一个众所周知的传闻称贝多芬临终前曾向雷暴中的天空挥拳。考虑到贝多芬的朋友添油加醋的倾向,没什么理由相信这一传闻,虽然气象记录证实当时确实有雷雨。我比较满意弗里德曼的版本,借约翰娜·冯·贝多芬之口道出结局。贝多芬认为这个弟媳缺乏头脑,对她充满憎恨。(前面提到过,贝多芬曾称她为“黑夜王后”,包括斯瓦福特在内的很多传记作家都把这指称的对象搞错了,实在令人惊讶。)弗里德曼设计了一个场景,让他们达成了和解,贝多芬在那个场景中产生了幻觉,仿佛看到他的母亲和“欢乐颂”里极乐世界的仙女来拜访他。小说以约翰娜致卡尔的一封长信作为结尾,驳斥了“挥拳向天”的传闻:“你伯父的面容……没有丝毫敌意,而是非常严肃,带着祈求的神情。你伯父祈求的到底是什么,我自然不晓得;但我猜想,那一定是某种语言难以传达的事情,某种需要牢牢把握的事情。他的手仿佛握着一只小鸟。在我看来,他祈求的,而且最后如愿得到的,是死亡的许可。”
作者:ALEX RO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