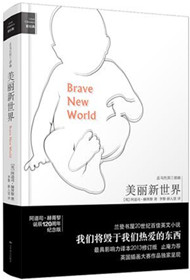
《美丽新世界》
[英]阿道司·赫胥黎 著;李黎 薛人望 译
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11月
凤凰网读书频道独家授权连载内容,如无授权,请勿转载。
长久的追悔,是最可厌的一种情绪,这是所有的道德家都同意的。如果你犯了错,就忏悔、努力改正,争取下回做好就是了。绝对不要沉溺在自己的错失里。在污泥中打滚可不是最好的净身办法。
艺术也有其道德,而这种道德的许多规则,与一般伦理道德的规则是同样的,或者至少是相类似的。譬如说,为恶劣的行为而长久懊悔,跟为拙劣的艺术品而长期追悔是一样的不值。恶劣之处应该挑出来,加以承认,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将来尽量避免。对二十年前的文学缺失吹毛求疵,意图把当初完稿时未能达到完美的作品加以修补,而想在中年来改正那个年轻的自我所犯下的艺术罪愆——这全然注定是徒劳无功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本新版的《美丽新世界》与旧版完全一样。作为一件艺术作品,此书的缺点是不少的,但是若要改正它们,我势必把全书重写——而在重写的过程中,我这个年纪老大、比起年轻时等于是另外一个人的人,可能会在改正故事中一些错误的同时,也删掉了原先具有的优点价值。因此,我抗拒着沉溺在艺术追悔中的诱惑,宁可让好坏两者都保留原状,自己想别的事去吧。
不过,把这故事中最严重的一些缺点提出来,还是应该的。书中的“野人”只得到两种选择:一是乌托邦中的非人生活,一是印第安村落中的原始生活,后者在某些方面虽然比较近乎人性,但在另外一些方面却同样怪异而反常。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人之所以被赋予自由意志,就是为了让他在两种疯狂状态中任选其一:当时我颇为这个想法扬扬自得,且相当自以为是。为了戏剧性效果,我让“野人”说着理性的话语,其实他是在一种半为生殖崇拜、半为忏悔自虐的宗教环境中长大的,那种环境不可能教养他那样理性地说话——即使是他熟读了莎士比亚,也还是难以令人信服。当然,到了最后,他被安排了走向疯狂:他原有的赎罪意识重又抓牢了他,他以疯狂的自我凌虐和绝望的自杀告终。“从此以后,他们悲惨地死掉了”——完全符合了那位自得的、怀疑论唯美主义作者的态度。
今天,我已不想证明心智正常是不可能的。相反地,虽然我像过去一样,认为心智健全是一种相当稀有的现象,但我已相信那是可以达到的,并且想要多看到一些这种现象。由于在一些近作中说过这样的话,又编辑了一本心智健全者所说的有关心智健全和如何达到的方法的选集,就有一位杰出的学院派评论家告诉我说:我是一个危机时代知识阶层失败的可悲的病例。这话的含义,我猜想,就是这位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是成功的可乐的病例吧。这些人类慈善家理应得到他们应得的荣耀与纪念,让我们建造一座教授圣殿吧。这座圣殿该建在欧洲或日本的一座损毁的城市的废墟之中,而在灵堂入口上方,我要用六七英尺见方的大字铭刻这样的话:
献给世界上的教育者的纪念。
SI MONUMENTUM REQUIRIS CIRCUM SPICE.
回头谈未来吧……如果我现在要重写这本书,我会给野人第三种选择。在乌托邦和原始生活的两难之间,会有一个心智清明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书中已经实现到某个程度了,那就是被美丽新世界放逐出来或逃出来的人,在保留区的边缘组成的小区。在这个小区里,经济将会是分布式的、亨利-乔治式的,政治是克鲁泡特金式的、合作式的。科学与技术的运用会是像安息日一样,即是为人而造的,而不是像现在,或更像美丽新世界那样,要人去适应它们,被它们奴役。宗教将会是人对“终极”的有意识的、有理智的追求,是对内在的“道”、对超俗的神与佛之认识。主要的人生哲学将会是一种高级的实利主义,“终极”原则第一,“极乐”原则屈居第二——生命中每一个事件的第一个问题都会是:“我和绝大多数其他人,如果这样做或这样想,是否会对人类的‘终极’有所贡献,或有所干扰?”
在这本假设要改写的书中,野人虽然还是在原始部落中长大,但他会先有机会认识另一个社会,那个社会是由一群献身于追求心智清明的人们自由合作组成的,然后他才被送到乌托邦去。这样修改之后,《美丽新世界》就会具有一种艺术上和哲学上的完整性(如果允许我在一本虚构的小说上用上这么堂皇的用词的话)。这份完整性在现在书中显然是没有的。
但是,《美丽新世界》是一本讨论未来的书,不论它的艺术性或哲学性如何,一本有关未来的书所做的预言,必须是看起来有可能会成真的,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从十五年后的现在我们所处的今日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本书中所做的预言,有多少是似有可能的?在过去这惨痛的十五年里,发生了多少事情是印证了或者推翻了那些一九三一年的预测?
有一个很大、很明显的预测上的失误,是一读就会立刻看出来的:《美丽新世界》一书没有提及核裂变这件事。这是很奇怪的:因为早在这本书写成以前的好几年,原子能的可能性已经是一个常见的话题了。我的老朋友罗伯特·尼可斯甚至以这个题材写过一部很成功的剧本;而我自己,也曾在二十年代晚期出版的一本小说中,偶然地提起过这个话题。因此,在“我们的福特”纪元七世纪时,火箭与直升机不是用核子分裂做动力,是相当奇怪的。这个疏忽固然不可原谅,但至少很容易解释。《美丽新世界》的主题并非科学进步的本身,而是科学进步对人类个人的影响。物理学、化学和工程学的成就,在书中已经不言自明了。唯一特别描述的科学进步,是生物学、生理学与心理学在未来的研究成果应用到人类身上。唯有用生命科学才能基本地改变生活的质量。物质的科学可以被用来摧毁生命,或者使生活变得无法容忍的复杂与不适;然而除非这些物质科学是被生物学家与心理学家用来作为工具,否则它们根本无法改变生命本身的自然形式和表现方式。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历史上一大革命,但并非最终的、最彻底的革命,除非原子弹把我们炸成粉碎、历史告终。
这种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不是经由外在世界,而是在人类的灵魂与肉躯之内达成的。生在一个革命时代的沙德侯爵,自然会应用这种革命理论去把他所特有的疯狂合理化。罗伯斯庇尔达成的是最肤浅的一种革命——政治革命。巴贝夫略深了一层,试图经济革命。沙德自认为是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使徒,超越了政治和经济,而成为每一个男人、女人与小孩的革命,这些人的身体从此以后成为全体的共有性财产,他们的心智也丧失了一切自然的廉耻、一切传统文明好不容易才建起的种种禁戒。当然,在虐待狂和真正革命性的革命之间,是没有必须和必然的关系的。沙德是个疯子,他的革命的意识性的目标,多多少少是全球性的混乱与毁灭。统治美丽新世界的人可能也不是心智清明的(以最严谨的字义而言);但他们也不是疯子,他们的目的不是乱无秩序,而是社会的稳定。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稳定,他们用科学的方法实施了最终的、人身的、真正的革命性的革命。
而同时,我们正处在可能是倒数第二个革命的第一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可能就是原子战争,果真如此,我们就用不着为预言未来而操心了。但我们也可以想象,人类可能还保有足够的理性,即使不能全面停止战争,至少也会像我们十八世纪的祖宗们一样适可而止。“三十年战争”难以想象的恐怖给了人类一个教训,使得有一百余年之久,欧洲的政客和将军们有意识地抗拒了诱惑,未曾穷兵黩武到国破家亡的程度,或者拼命打到完全歼灭敌人为止。当然,他们还是侵略者,贪图财富与荣耀;但他们同时又是保守主义者,决心不管怎样也要维持他们的世界的完整,是为利害关系之所系。过去三十年来,已经没有保守主义者了;只有右派国家主义激进分子和左派国家主义激进分子。最后一个保守派的政治家是兰斯当侯爵五世,他写信给《泰晤士报》,建议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仿照十八世纪大多数战争一样,以和解的方式结束,那份曾经是保守派的报纸的编辑竟然拒绝刊登。国家主义激进分子遂能随心所欲,结果是尽人皆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法西斯主义、通货膨胀、经济不景气、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毁灭,以及几乎全球性的饥荒。
那么,假定我们可以从广岛习得教训,就像我们的先人从马德堡学得教训一样,我们可以期待一个时期,虽不是全然的和平,但也只是有限的、仅具部分毁灭性的战争。在那样一段时期里,核子能可能会被利用在工业用途上。结果是会很明显的,就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快速与全面的经济和社会的变化。所有现有的人类生活形态都会瓦解,新的形态必然会产生,以配合原子威力的非人事实。穿着现代服装的普罗克拉斯提斯——核子科学家们,将为人类准备好非躺上去不可的床;如果人类的身长与床不符——好,那人类就倒霉了。有的人要拉长,有些要削短——自从应用科学大展宏图以来就是这类的拉长与削短,不过这一回比起从前是来势凶猛得多。这些绝非无痛的手术,将由高度中央集权的政府来指挥。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不久的将来很可能像不久的过去一样,而不久的过去,在大量生产的经济制度与大多数人是无产者的情况下发生的急遽的科技变化,业已造成经济和社会混乱的趋向。要处理这种混乱,权力便集中了,政治的控制加强了。甚至在原子能被控制利用之前,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就有可能或多或少地走向完全极权了;而在原子能被控制利用之时和之后,这些政府的极权化则是几乎必然的了。唯有一种大规模的、广泛的反集权和自救运动,才能够阻止目前这种走向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的趋势。然而目前毫无这种运动会发生的迹象。
当然,新的极权主义没有理由会跟老的极权主义面目相同。以棍棒、行刑队、人为饥荒、大量监禁和集体驱逐出境为手段的统治,不仅不人道(其实今天已经没有人在乎人道了),而且已经证实了效率不高——在科技进步的时代,效率不高简直是罪大恶极。一个真正有效率的极权国家应该是这样的:大权在握的政治老板们和他们的管理部队,控制着一群奴隶人口,这些奴隶不需强制,因为他们心甘情愿。在当今的极权国家里,使奴隶们心甘情愿,是宣传部门、报纸编辑和学校教师们的任务。可是他们使用的方法仍嫌粗糙、不够科学。从前耶稣会教士曾吹嘘说:如果把一个孩子交给他们教养,他们可以担保负责这个人的宗教思想,这真是一厢情愿的想法。现代的教书匠,在制约他的学生的反应方面,可能还比不上那些教育伏尔泰的大人先生们那么有效率呢。现代的宣传术,最伟大的成就,并非做了什么,而是靠不让人去做什么。真理固然伟大,但从实际的眼光来看,对真理绝口不谈则更伟大。只要闭口不谈某些话题,落下丘吉尔先生所谓的“铁幕”,把群众跟他们的政治老板们不想要的事实或议论隔离开来,则极权政府的宣传人员们左右意见的效率会大得多,远超过雄辩滔滔的谴责和强压的逻辑辩驳。不过光是沉默还不够。如果想要避免迫害、清算以及其他社会摩擦的症候,宣传的积极面必须与它的消极面同样有效。未来的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将会是由政府发起的大规模的调查研究,探讨政客们和有关的科学家们所谓的“快乐问题”——换句话说,使人们如何能心甘情愿于他们的被奴役。没有经济的安全保障,心甘情愿于被奴役便不可能实现;简而言之,我假定那大权在握的行政部门及其管理者们会圆满解决长期安全保障的问题的。可是安全保障等等会很快被视为理所当然。所以这种成就仅仅是一种肤浅的、外表的革命。除非是一种深入每个人身心的革命的结果,否则心甘情愿被奴役是办不到的。要达成这种革命,除了其他条件之外,还需要以下数种发现与发明:首先,大幅度改进了的暗示技术——经由婴儿时期的条件制约(Conditioning),到后来辅之以药物,如莨菪胺。其次,一种十分发达的人类分等科学,可让政府管理人员们,将任何个人分配到他或她在社会和经济等级制度中合适的位置上去(插在方洞里的圆钉子,会倾向于对社会制度的危险思想,并且会将他们的不满情绪传染给其他人)。第三(既然不论现实是多么乌托邦式的,人们也会感到时常要度假的需要),一种酒精及其他麻醉品的代替品,一种比杜松子酒或海洛因危害较少而给人乐趣较大的东西。第四(这可是一个长程计划,得要好几代的极权控制才能有所成效),一套绝无差错的优生学系统,用来标准化造人,以减轻管理人员们的工作量。在《美丽新世界》一书中,这种标准化造人的过程推展到了想入非非的极致,然而也并非不可能的。从科技和意识形态上来说,我们距离瓶养婴儿和波卡诺夫斯基的半白痴群体还远得很。但是到了福特纪元六百年时,谁又知道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同时,那个更为快乐、更为稳定的世界——也就是索麻、催眠教学和科学的等级制度——的其他特点,可能用不了三四代就会发生了。《美丽新世界》中所说的性杂交现象似乎也离我们不远了。已经有一些美国城市,离婚和结婚的数字相等。无疑的,过不了多少年,结婚证书会像畜犬证书一样地发售,有效期十二个月,没有法律条文禁止犬只互换或者同时豢养多于一只的。随着政治和经济自由的减少,性自由势必补偿性地增加。而独裁者将会乐于鼓励这种自由(除非他需要炮灰和家庭人口,到无人地带或被征服的领土去殖民)。性自由加上由麻醉品、电影和收音机所支配的做白日梦的自由,统治者会更容易使他的臣民顺从于自己的奴隶命运。
从各方面的考虑来看,乌托邦比起十五年前任何人可以想象的都更接近了。十五年前,我还把它设定在六百年以后。今天看起来,这种恐怖状态可能要不了一个世纪就会降临到我们身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没有把自己炸得粉身碎骨的话。真的,除非我们决心去反极权,并且以实用科学为手段,来产生自由个体组成的人类,而不是把人类当成手段而以科学为目的;否则,我们就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条是一群国家主义的、军事化的极权主义者们,以他们的原子弹恐怖行为起家、以文明的毁灭告终(或者,如果战争受到限制,则是长期的军国主义);另一条路则是一个超国家的极权主义,由急遽的科技进步和原子革命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中应运而生,并在效率和稳定的需求中发展成为“福利专制”的乌托邦。你付钱,任选一种。
一九四六年再版时作
(摘自《美丽新世界》,北京燕山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