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板油画《愉悦相伴》(Merry Company),1562年,作者:让马特西斯(Jan Matsys),现存于法国瑟堡市托马斯亨利艺术博物馆。图自《布里奇曼艺术》/盖蒂社
压迫的性质和形式不一而足,但几乎所有的起因都是不公正:人们所接受的待遇与他们应得的待遇有所不同。当然,我们很难说出一个人应得的待遇到底是什么,但是在当今世界,我们常常认为,功过赏罚在某种程度上与人们所能控制的事物有关。例如,你的肤色并不由你做主,所以你因此而受到恶劣待遇,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压迫。我们说的这种待遇往往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一个排斥同性恋的社会可能比一个关押同性恋者的社会的压迫性要低,尽管如此,它还是让人有压迫感的。性取向和种族是相当明显的压迫重灾区,阶级和性别亦如此。但是,如果压迫就是没有给人以应得的,那么将会有另一种压迫进入我们的视线,这就是丑陋之人所受到的压迫。
我们不能选择我们的长相特征,就像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肤色,但是人们一直都以貌取人。正如心理学家克米拉沙哈尼丹宁(Comila Shahani-Denning)于2003年在《霍夫斯特拉视野》(Hofstra Horizons)期刊上关于该问题总结并发表的研究报告所说:“(人们关于)长相的偏见出现在各个领域,比如老师看脸给分、选民看脸投票、陪审团在模棱两可的案件中看脸来做出裁决……长相也会影响面试者对于应聘者的评判。”蹒跚学步的幼童爱盯着漂亮的成年人看,成年人也喜欢凝视可爱的孩子,我们无情地给予长得养眼的人以优待。长得丑的就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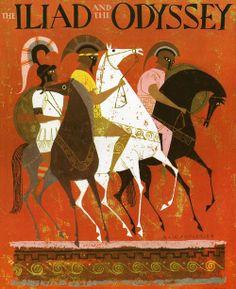
古希腊人也爱以貌取人。19世纪的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评论道:希腊人不仅深受美的影响,而且还普遍并且坦率地表达他们对于美的价值观。”荷马所著的《伊利亚特》(Iliad)中就有一幕,颇能蛊惑人心的平民忒尔西忒斯(Thersites)要挑战阿伽门农(Agamemnon)的权威,但很快就被奥德修斯(Odysseus)狠狠揍了一顿,奥德修斯对于这位自命不凡者的蔑视十分强硬:“所有那些来到伊利昂城(Ilion)脚下的人中,没有比你更坏的人了。”荷马对于忒尔西忒斯的描写,基本上都用“最丑的”(ugliest)来代替“最坏的”(worst):
这个男人是来到伊利昂城的人中最丑的一个。他罗圈腿、跛足、驼背、含胸,尖尖的脑袋上顶着羊毛般稀疏的头发。
将“最丑”与“最坏”两个概念等同,并非是荷马个人独有的习惯。希腊语中,表示“美丽”的词汇是“kalos”,它也有“贵族”的意思;而表示“丑陋”的词汇是“aischros”,它也有“可耻”之意。我们再次引用布克哈特的说法就是,在古希腊,“美丽与精神上的高贵相连,是一种最为牢固的信念。”
希腊人毫无保留地崇拜美丽,他们请求将长得好看的运动健儿看做半神(quasi-deities)[1]并为之立下雕塑;把青春帅气的男孩培养成名流雅士;甚至到了偶尔会仅仅因为一个敌方士兵长得俊美,就要放他一条生路的地步。一种文化若崇拜美丽,那么在这种文化中,丑陋也会受到压迫。布克哈特讲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一个斯巴达姑娘后来成为了狄马拉图斯(Demaratus)的妻子,因自己样貌丑陋,她每天都去特拉波涅(Therapne)的海伦神庙祷告;她站在美丽的海伦塑像前,恳求海伦让她变美点。”
虽然现在时兴的是外科手术而非求神拜佛了,我们的文化似乎仍然与希腊文化一样恐惧丑陋的事物。父母仍然希望他们的孩子不拥有丑陋的外貌,许多父母也愿意助孩子一臂之力:虽然让孩子去做隆鼻、丰胸、抽脂手术的不多,但对诸如牙套等一些形式的牙齿美容的投资,现在已经屡见不鲜。东倒西歪的牙齿意味着丑陋的笑容,丑陋的笑容会让你在人生的舞台上多次付出代价。当然,人们会说带牙套是为了健康,而不是为了好看,但是对于那些忍受这一过程的孩子来说,真正的原因十分明确——在我们的文化中,牙套是缠足的翻版。
希腊人应该不会对承认带牙套的真相而感到尴尬。亚里士多德就明确公开地说,除非你的孩子开心,否则你无法开心;而且人只有长得好看,才能真正感到快乐。他的意思并不是丑陋之人就永远“感受”不到开心;他说的并不是(或者至少起初不是)主观或者内在的感受,而是更加客观的感觉。我们不妨这样想:有一才会有二,循序才能渐进。我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快乐地成长。假如你能替他们做选择的话,那么哪种环境,哪些品质对于他们来说有选择价值呢?比如说,你是希望他们美如西施呢,还是希望他们貌若无盐呢?显然你希望他们能好看些。因此,如要挑选最值得过的生活,美丽必为其中一个组成部分,而丑陋则是“玷污了幸福的一个污点”。这种逻辑在当下仍然成立,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很难去承认它。
为什么我们如此关注“流行的肥胖病”呢?显然,超重会损害个人健康,也会影响公众福利,这个原因易于被大众口耳相传。但就我个人而言——希望我的观点不会过多暴露我的卑鄙——我发现,要相信减肥活动并不仅仅是由“嫌恶”所驱动这种观点是很难的。当你遇到肥胖体型的人时,我认为你会觉得——或者我认为我会觉得——有一点“惊骇”,甚至对他们有一点“恼火”。肥胖似乎是“错的”。实话实说并不容易,因为这种想法非常不道德,让我想起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著作《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1889),尼采显然没有受到这种难题的困扰:
从生理学角度来看,一切丑陋的事物都会让人们变得软弱而悲伤。丑陋让人们想起腐朽、危险以及无力:它确实会让人们失去力量。丑陋带来的影响是实实在在的。当人们消沉沮丧时,他们会感到一些“丑陋”近在眼前。他的力量感、权力意志、勇气以及自豪——统统会因为丑陋之物(的影响)而减少,因为美丽之物(的影响)而增加……丑被看作衰退的表征……枯竭、沉重的迹象……瓦解的气味、颜色和形式……所有这一切都产生了同样的反应,产生了“丑”这个价值判断。一种“憎恶”之情油然而生:人们憎恶的是谁?而这是毋庸置疑的:是“人类的倒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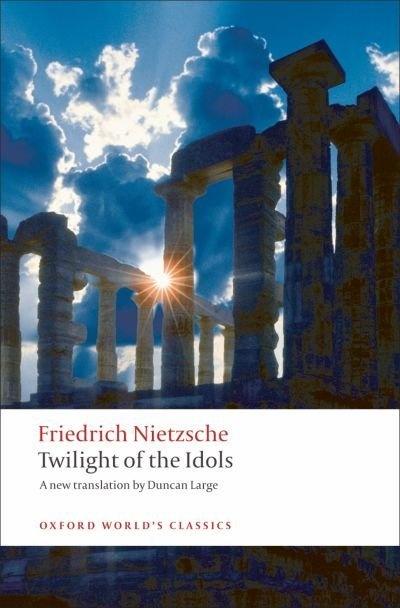
尼采接下来可能要说的是,我们现在如此关注肥胖是因为我们无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我们无法忍受“看到”肥胖者是因为他们是丑陋的,并因此散发出“腐烂以及变质的气味、颜色和形式”——换句话说,他们是我们这个种群的倒退。
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
对尼采来说,我们所说的这个种群与其说是国家,倒不如说是人类zi ji。然而长得好看的人会让我们想要神化人类,以(给长得好看的人)树立雕塑和纪念碑的形式帮助人类“肯定自己”。丑人让我们的精神和能量大伤元气,让我们对于人类的未来感到沮丧。这么说有点过分吗?可能吧。但是想一想《机器人总动员》(WALL·E)(2008)这部电影中的反乌托邦的情景,未来的人类被描绘成肥头大耳的懒汉,坐着轮椅,没有机械的辅助就没法站起来,他们的下颚骨退化消失。这样一个噩梦难道真的无法改变人们对肥胖的态度吗?

当然我们宁可噩梦不起作用。一方面,它似乎有一点纳粹主义的意思。但是它也很是肤浅与刻薄,我们是羞于变得肤浅刻薄的。仅仅根据一本书的封面就对它做出评价,这会显示出我们的肤浅。从“内心”上来讲,变得肤浅就是变得丑陋。
尼采认为,将外在美转化为内在美的革命性概念,是由以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历史上长得不咋地的人、神职人员和哲学家所发起的。希腊人假设外在美是快乐所必须的因素,苏格拉底反对这种假设,而声称理性能够带来美德,而美德又能带来快乐。众所周知苏格拉底的长相十分丑陋,但是他设法让自己的内在变得美丽,以至于英俊的年轻男士会无可救药地陷入对他的爱恋之中,让他们对自己精神上的丑陋感到悔恨,像狂吠不已的小狗一样乞求他的注意。尼采对这一切给出了一个挖苦的解释:“用辩证法的目光看去,乌合之众将反败为胜。”这种将美丽与高尚挂钩的文化,除了简单把美丽重新定义成知识分子才有的内在品质,我们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来对抗它吗?
苏格拉底式的举动将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牧师)置于一个优待地位上。在这层意义上,我们对于当代人的品位仍然有些妄下评判的意思。我们想让这一革命更进一步。我们拒绝承认“任何一个人”都是丑陋的。要么,每个人的内心都是美丽的——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雪绒花——要么,无论如何外在美都是相对的,因此谁也不好评判。总之,我们很难让某人承认一个特定的人是丑陋的,这一点显而易见。人们的相貌的确反映着他们此后的选择——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说“到50岁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了他应拥有的一副脸孔”——这的确让我们很难把外在美从其他一切中抽离出来。但是我们还是这么做了。
这意味着相较于希腊文化,我们的文化对丑陋的压迫要少些吗?我们担心自己展现出肤浅与刻薄的形象,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肤浅不刻薄。为了掩盖这一点而假装丑陋并不存在,这反而创造了一个新的压迫制度。在某种意义上,丑陋之人的处境颇似所谓“后种族”(post-racial)社会中黑人的处境:我们以为这种区别对待的压迫已经不复存在了。
然而,事态可能会对丑陋之人愈加不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从未将丑陋当做过一种不公正并予以认真对待。事实上,不管丑人受到怎样不公正的对待,也完全不会有人将其与种族主义引起的不公正相提并论。我们可以想想一个人所能实现他在这个世界上愿望的机会。假设你想变成一名宇航员、演员或者杂技演员,而这并不由你做主:它既取决于你的渴望,也要依靠你的天赋。
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轨,而这仅仅是因为出轨的机会通常就摆在他们眼前
如果一个人天赋不够,那么他的机会也会变少,而好看的相貌被当做一种天赋。研究显示,从人们求学伊始——它对于人的职业前景十分重要——不用多聪明的人都能看出来它也对人们的关系交际网十分重要。漂亮的人自然拥有更多的选择。当然,可能出现难以抉择的情况,拥有美貌也可能意味着一种诅咒:例如,漂亮的人更有可能出轨,而这仅仅是因为(出轨的)机会通常就摆在他们眼前。但是总而言之,绝大多数人会发现,在人生变幻叵测的机遇中,不贪恋更多的机会是很难的——总的来说,丑陋的人拥有的机会更少。
但是,这种压迫仅仅是坏运气吗?毕竟,似乎没有什么规章制度规定丑陋的人要“坐在汽车后排”[2]。速度更快的跑步者常常能赢得百米赛跑,而杂技演员多是拥有良好平衡能力的人,你可能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惋惜和怨愤,但这几乎不具有压迫性;在某些场景中,奖励这些具有天赋的人的“做法”就是给他们以应得的待遇。的确,生来美貌与是否能设计出好看的网页不太相干,在类似的案例中,当招聘时,把外貌作为衡量因素应当是违法的。当然,这类法律很难得以实施——并不仅仅因为用人决定通常是不透明的。现实情况是,在许多工作中,漂亮的长相都的确能够加分。这类工作不仅仅包括诸如演戏、走秀或者餐厅服务等抛头露面的工作,也包括销售、管理甚至教育等——只要客户、管理人员以及学生仍然以貌取人,丑人就很难引起他们的好感。
这说明,对于丑陋之人的压迫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法律,在清醒理智的意识的决定中也不常有所体现,它是在世俗交往中,而非法律和意识决定层面起作用。但是丑陋之人应该得到和其他任何一个人一样多的尊重:让他们的话语得以被倾听,动作得以被注意,眼神得以有交流。他们却没有得到这些尊重,但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自己犯了什么错。
而且,正如你可能已经听过的那样,生活并不公平。几乎没有人会故意地压迫丑陋之人。然而从道德层面来说很不幸的是,希腊人的态度已经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我们。有时,我们的确会发现一个人的外在之美——例如他笑容所洋溢的魅力——但在这笑容之下,他的内心是空虚堕落的。但是我们最初的想法几乎都是这个人看上去像是一个讨人喜欢的朋友。我们想要与他为伴,听他说话,多看他一会儿。当然,对于一些漂亮的人,尤其是美女来说,这种吸引力是把双刃剑,吸引一些人注意力的同时,也会失去另外一些机会。这也是一种坏运气。
问题是,我们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性情也得到了演化。幻想我们能够完全克服这种自然的遗传,认为我们能过上各自应得的生活,或者甚至,认为我们能成为我们配得上的那种人,这就是一个幻想——而希腊人能无忧无虑不受其扰,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命运使然。然而我们的白日梦,如同我们的脸孔一样,并不完全由我们自己做主。我们只能尽力去用好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