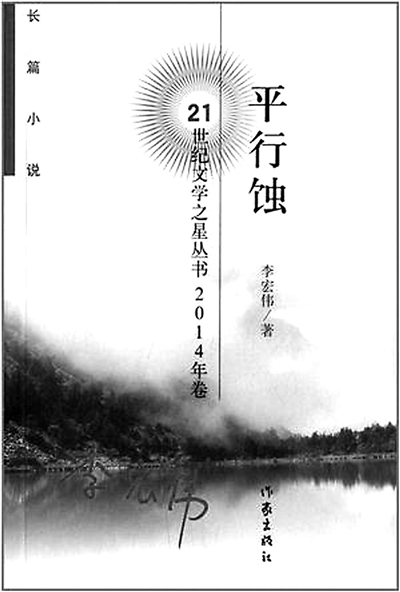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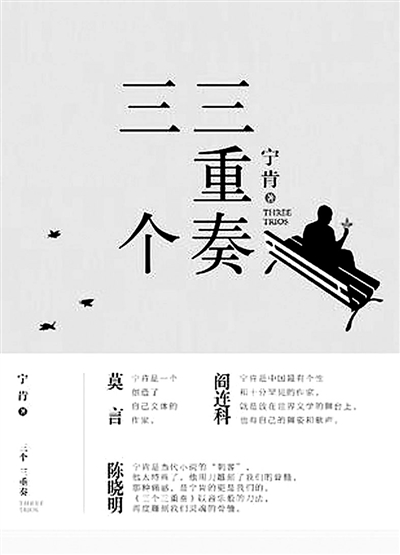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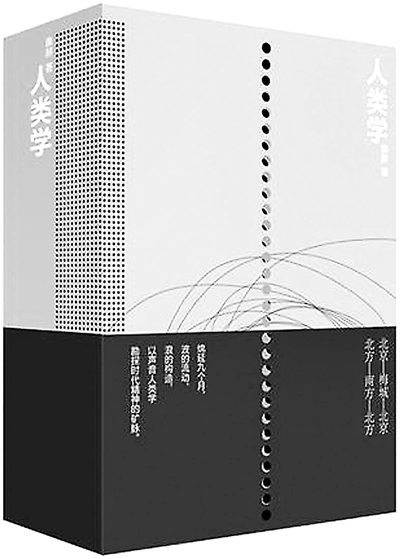
最近我读了刘庆邦的《黄泥巴》,这个作品像他之前的《神木》、《红煤》,采取了一贯的现实主义式的写法。小说的开头就是个很典型的十九世纪小说式的开头,他以细腻绵密的笔触对中原乡村儿童玩泥巴的游戏进行了精雕细凿,这种带有民俗画色彩的描写来自于写作者的本人记忆,因而有些时候因为私心中的热爱与温情而让语言变得不加节制。如果不从小说技巧和精炼的角度来看,这个开头就是一篇绝妙的乡土散文,它的温馨和熨帖可以激活有着共同经验的读者共鸣。小说中这样的段落时常出现,但这种经验“代入感”一方面是虚幻的体验,它往往会带来一种虚假的满足,从而遮蔽现实本身——这是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传统“现实主义”对于现实的无力就体现在这里;另一方面它还会面临一个更为尴尬的问题,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不再具有作者所书写的独特经验的时候,它也就失效了,沦为一种具有怀旧功能的想象型能指。
作为一个有关怀的作家,刘庆邦试图勾勒基层权力斗争和乡里社会的礼崩乐坏,姑且不论这种主题如何在1990年代以来“后革命”式思想解构与观念颠覆中被一再重写,就文本自身而言,其牵涉的社会关系与结构也依然被必然而又悲剧性地简化了——《黄泥巴》不可能像茅盾《子夜》那样具有宏大气魄和高度概括的典型性,这让它最终悲剧性地成为中国当下万千故事里的一个而不再具有“典型性”,宏大关怀最终落脚于退缩性的碎片之中。小说集中描写的房户营村作为一种象征式的存在,在村中人物的权力争夺中,丢弃了自身的历史,同时未来的重大变革可能性也隐匿不见,情节靠尔虞我诈的逻辑推进,这让它的“现实主义”面目更像一个缺少历史深度和未来关怀的后现代叙述。
在概括现实的意义上,盛可以的《野蛮生长》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她试图以时间为线索,以一个家庭中兄弟姐妹的故事来结撰晚近三十年的历史转型。这种雄心显然来自于现实主义小说的传统和写作模式,但单薄的文本却撑不起这种厚重的雄心而在两个方面都凸显出匮乏。历史与现实经验性的匮乏让细节几近于无,每个人物的性格与命运都呈现出抽象的发展,充盈在其中的倒是大量作者主观性的意念;宏观抽象能力的匮乏又让历史与现实呈现出简单粗暴的逻辑,原本应该充满各种模糊与暧昧的社会空间、权力和运作都被粗线条地白描化约为一条明确的颓败的轨迹。因为双方面的匮乏,使得作者不得不寻求想象力的补充,但她的想象力却是被充斥在大众传媒上的“习见”所规约,从而放弃了作者自身的独立性思考和文学意义上的发现。小说因此令人遗憾地流入到一个类似于山寨版的余华《第七天》,社会新闻式的故事点缀在人物的命运之中。社会新闻追求轰动效应,它们本身不具有典型性,当偶然性的命运故事集中起来,它们拥挤不堪,就像一个遍布各式没有化开的“浓汤宝”的汁液,情节与人物并没有融合为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认知物。抽象与概括于是成了化简的故事会。
这样的故事有着时间形式的外貌,却不具有现代主义的时间感,即没有展示出新的历史经验的复杂性,它所叙述的“现实”并不是实践领域的现实,而是对媒体中被语言表述过了的“现实”的模拟。这是一个充满残酷内容的小说,但令人惊奇的是,作者似乎以一种零度写作的态度呈示现实,因为缺乏有历史悲悯的感觉和激情,让这种现实的符码最终只是成为一种幻觉。
这两部“直面现实”的作品显然不是唯一的,当下大量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叙事很大程度上都不过是在现实的表面平滑地打了个旋,显示出浅表的特征。这种现象,显然不仅仅是现实主义技法的问题,而是世界观的问题。
随着《平凡的世界》电视剧热播,“现实主义”再次成为热门话题。许多人觉得,“现实主义”在经历了先锋文学的洗礼之后可能依然没有过时,毕竟刻画社会、回应现实提出的问题、召唤与显形某种“时代精神”是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尤其是现代小说的伟大传统。读者在18世纪对于小说的种种阅读期待,比如增广见闻、娱乐消遣、在故事中认识社会的企图、获得道德教益和批判性观点等等,在今天同样存在。
然而,作为被文学理论界定了的“现实主义”,如今在小说创作中可能真的难以为继了。那种“现实主义”要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主人公是个英雄,通过性格与情节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到小说想要表达的历史规律和必然性,而作者则是它创造的世界的全知全能的上帝。然而,如今的文学已经日益多元化,物质主义在市场的支撑下成为理直气壮的存在,而作家经历太多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理论与技巧的洗礼,再像他们的18、19世纪前辈一样摹写现实,已经显得有些迟钝和懒惰。
就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来看更是如此。世事变易,当代政治经济和信息传媒的发展已经让作家很难对一个社会和时代进行总体性把握。宏观把握让位于更加精细的哲学社会科学,细部描摹则有着迅速扩张的新旧媒体:它们在两方面都做得比闭门造车的作家要好,即便是那些“接地气”、“走基层”、“在路上”的作家也难以胜任其中任何的一项。
现实主义其实是个具有极大涵括性的表述,它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化身”:在中世纪后期可能是以浪漫主义的面目出现;到了资本主义时代,幻想祛魅之后产生了我们如今文学概论上所说的那种经典的“现实主义”;而垄断资本主义和帝国时代,它又变成了现代主义;在如今的全球化和跨过资本主义时代,则成了形形色色并存的后现代主义。我这种简单的描述并不是说这些现实主义化身之间有着某种线性时间链条,事实上各种现实主义化身在产生之后并没有因为后来者的产生而消亡,它们共生在整个文学生态体系之中。
关于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辨析在各种文学理论中已经足够多。奥尔巴赫在其巨著《摹仿论》中就试图把现实主义的产生看作是通过新的句法结构的创造对现实不断进行变革的结果。詹姆逊继承了这种认识,“把现实主义看成一个主动的过程,看成一种形式的创新,看成一种对现实具有某种创造能力的结果”,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讨论现实主义化身时应该采取的态度。
我们完全可以将之归结:所有的文学写作模式其实都是应对现实、时代与社会的产物。贯穿于其间的根本精神在于“新形势采取新形式”,即面对纷繁变动的现实内容,现实主义写作再也不能采取僵化了的“现实主义”教条式模式,它的外形可能变化,化身为我们可以为之命名的各种“主义”,但所有变化都离不开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关怀、现实洞察和未来瞻望。近期小说创作中,出现了不少此方面的探索,比如“前沿小说文库”系列作品、宁肯的《三个三重奏》、李宏伟的《平行蚀》、康赫的《人类学》。他们的探索成败尚未可定论,却证明了文学在现实与技巧双重变革的背景不断自我解放、自我创新的尝试,也证明了现实主义依然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