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鞍华(澎湃新闻蒋立冬绘)
许鞍华,1947年出生,香港电影导演、监制、编剧。1975年担任胡金铨助手,开始电视、电影工作,1979年银幕处女作《疯劫》领香港新浪潮风气之先,至今从影四十余年。六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1983年、1996年、2009年、2012年、2015年、2018年)、三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1999年、2011年、2014年)得主。
2018年10月13日晚,“许鞍华电影周”将于上海师范大学开幕,“许鞍华:半部香港电影史”研讨会亦将于翌日举办。在动身前往上海前,许鞍华导演电话接受了《上海书评》的专访。
我对上海有一个想象
您拍过三个时代的上海: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以及二十一世纪初;您拍过更多时代的香港。我以为,这两座城市在您的镜头里都是“新旧交替的”(甚至某种意义上“后现代的”),而您看上海的视角是外部的,看香港的则是内部的。《天水围的日与夜》《明月几时有》尤其显示了您呈现香港的历史深度,以及市民日常生活力量的企图。您怎么看待沪港二城的异同?

《上海假期》(1991)剧照:俯瞰上海的弄堂。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6)剧照:斯琴高娃和周润发在陕西南路延安中路的天桥上,面对马勒别墅。
许鞍华:我没有特别想从外来人的角度拍上海,但确实在无数细节里表现出了这样的感觉。我觉得这个很可以研究的。比如那些临时演员的脸,可能不是那么的上海人,在香港,随便找个人,我就知道他的脸不对,阶层感觉不对,但在上海我分不清。另外,我很多香港的戏都是讲粤语的,而上海的戏全部都是标准国语,尽管带一点上海口音,但也不是市民通常讲的上海话。首先是这些细节,你们上海人肯定觉得不对了,有点局外的感觉。
我年轻时,其实是从读张爱玲开始,对于上海有一个想象。七八十年代,我看了好多讲旧上海的书,尤其关于杜月笙、帮会、租界。我想所有的香港人都觉得上海特别有魅力,这个感觉是真确的。上海不止是它的风月,还有它的文化,各方面都有比香港大、优越、深厚的地方。六十年代,上海的明星,连理发的、裁缝,在香港都非常吃香,人们以他们为楷模,作为品位的保证,好像穿戴时尚上,上海的东西比较高尚。那个时候反而上海菜是不受欢迎的,不像现在。比如我们家里请客,办酒席,不会吃上海菜的,其实我们连上海菜和北方菜都分不清,觉得北方菜是外乡菜,比粤菜要便宜。不过当时吃的上海菜已经很地道了,我现在都记得吃过什么。我后来再看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即便不算风起云涌的革命和各种思潮,它也不光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

《半生缘》(1997)剧照:上海的工厂。
九十年代拍《上海假期》,我多少是带着一种粉丝的心态来上海的。后来拍《半生缘》,就希望带出一个城市开始发展的感觉,所以有工厂区、半郊区的上海。不过,不论是《上海假期》还是《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我的重点都不是上海的日常生活,虽然我拍了好多香港现在的日常生活。像《天水围的日与夜》,全都是用食物来讲述。这个故事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应该有的矛盾都没有。我感觉,我们所有人的想法,包括我自己,都是很套路的,尤其是我们看电影多的人,看了两分钟就知道后面会继续发生什么事,如果它不是按照我们猜测的发生,但也能被理解的话,我们就会特别高兴。内地有人批评《明月几时有》,翻来覆去地说,为什么没有打仗戏,为什么不那么慷慨激昂。我想套路束缚了我们的感受,让我们无法回到现实层面思考,当时的状况是怎样的。其实导演拍戏和影评人写东西,重要的都是看你有什么新的想法,而且这个新想法是能想得通的,然后不断地展开这个局面,而不是老是在套路里面打滚。


《天水围的日与夜》(2008)结尾,香港此时与彼时的中秋节。
您曾两次把张爱玲搬上银幕:《倾城之恋》紧跟原著,《半生缘》略重改编,对于前者,您多次表达了遗憾。您即将第三次拍张爱玲,为什么选择《第一炉香》?就《第一炉香》,您偏向采取哪种改编策略,人物还是情节优先,会借题发挥吗?与王安忆合作是怎样的体验?在《倾城之恋》《半生缘》《黄金时代》等电影里,画外音(旁白、独白)或字幕都直接“引用”了文学作品的句子,如此彷佛突出了文学与电影的裂痕,您为什么不尝试电影对文学更彻底的翻译呢?

《倾城之恋》(1984,周润发、缪骞人主演)与《半生缘》(黎明、吴倩莲、梅艳芳主演)
许鞍华:夏梦有个粉丝,后来跟她成了好朋友,夏梦过世的时候,把她的青鸟公司传了给他,他以后准备拍一些好电影。因为他是张爱玲迷,所以第一个戏就去买了《第一炉香》的版权,这大概是四年前的事了,然后他一直找资金,想找我拍。我本来不要再拍张爱玲的,因为他那么诚恳,又找到了资金,我想,这可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吧,希望能把张爱玲拍得好一点,所以就答应了。
我找王安忆基于两个考虑。十年前我做过一个舞台剧——《金锁记》。早一年,我在上海看了黄蜀芹导演的《金锁记》,是王安忆编剧,后来香港有人找我,说要不要试试舞台剧,我觉得还是做一个我比较熟悉的好,就用王安忆的剧本,在香港排了这出戏。我看王安忆的剧本,知道她改编的风格:她把张爱玲的移来移去,最后还补了一大场——五场戏里,讲曹七巧的女儿跟她男朋友的一场是她的创作。你如果找人来补一场张爱玲,除非王安忆是补不了的,水平很难像张爱玲一样。我当时看了特别震撼。到这次准备剧本的时候,我知道青鸟的老板来来去去就是要张爱玲的原著,但《第一炉香》还是有点短,需要加长,我想如果王安忆肯写,一定能补得很好,这样就满足了所有人的希望。如果我来改,我的能力恐怕做不到,要是改成一个我怎么看张爱玲的东西,肯定被那么多张爱玲迷骂死。我觉得王安忆是很委屈的,因为她也是个大作家,不过《金锁记》她已经做过一次了,应该不会太介意。所以这次会是对张爱玲的延伸。

《金锁记》(2009,许鞍华导演,王安忆编剧,焦媛主演)剧照
原著的句子是因为没有信心才加的,觉得没表达好,就加一点,其实不是个好办法。更好的方式是像在《悲情城市》,梁朝伟是哑的,很多时候他要写字,文字出现就是戏的一部分。如果硬把导演或者张爱玲的叙述加进去,就不是戏的一部分了。另外也有人把原著完全改成自己的东西,像《东邪西毒》《笑傲江湖》,都是只保留了人物和基本情节,供导演自由发挥,效果很好,还有德国导演法斯宾德的《寂寞芳心》《柏林亚历山大广场》,也是对名著作较大的改编。你要把文学改成自己的东西,你的水平必须比原著高,最少跟原著一样,要不改不好,两个不同水平的摆在那里,人人都看得到,这个我做不了。另外,张爱玲作为作家,是个独特的存在,她最好的,也是她难改编的地方在于,你往往离不开她的文字和文字营造的氛围,不光是情节,她不是情节为主的作家。所以很难改,尤其她的对白,不是普通人讲的话。她好多很精彩的对白可能舞台化比较好,在舞台上讲一些风格化的台词是可以的,电影就比较难。所以《倾城之恋》的舞台剧都很成功,电影就被骂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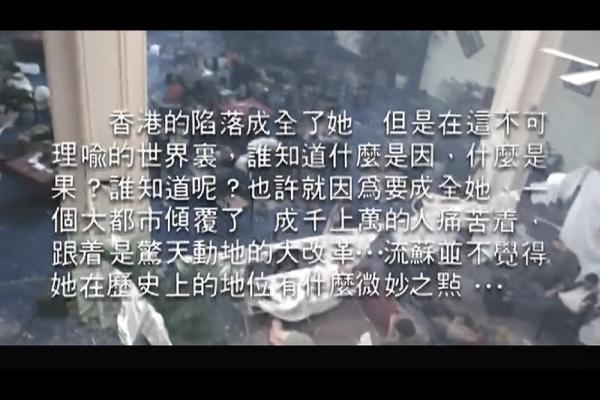
《倾城之恋》结尾的字幕
比爱情可信一点
您说您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您的全部作品涵盖了各个阶级、不同职业的女性主角:从女佣人、女学生、女陪酒、女理货员,到女武师、女警察、女文员、女编导,再到女业务科主任、女作家、女律师——当然,还有“过去年年都是先进工作者”的姨妈。您有数部电影涉及“无证妈妈”“单身妈妈”“家庭暴力”“女同/双性恋”这样的主题或元素。女性,以及通过电影再现女性对您意味着什么?

《天水围的日与夜》里的女工老照片

女佣人桃姐(2011)、女武师阿金(1996)、女作家萧红(2014)
许鞍华:我不是刻意去拍女性的。有时候在我想拍的几个剧本里,老板选中的那个刚好是女性的主人公,我就拍了。我也没想要探讨女性主义。可如果说我的哪部电影是讲女性的,再用女性主义来解释它,我觉得也很好。
对于女性在社会上的位置,我的态度比较矛盾。我从书本上读到,或者从别人那里听到的观点都是,社会对女性很不公平,可我的个人感受不是这样的。可能在男性主导的社会,我们都是男性主义的。比如我去拍戏,人家给我找一个女副导演,我立刻就会有所怀疑——她会不会要别人送回家?会不会生理周期的时候不舒服?我不知道这是男性的观念还是女性的观念。很多时候,我也不自觉地把这种目光投向自己,我总是有点自卑,因为我不漂亮,而且很胖。但我并不觉得这样就一定问题很大。我还是会和这个女副导演见面,彼此适应,像对待男副导演一样,起初小小的偏见不会妨碍未来的工作和友谊。除非你的偏见到了这样的地步,像过去包办儿子婚姻的母亲,可这反而未必是性别的问题了,也许母亲觉得儿子原来喜欢的那个女孩家里太穷。可见各种问题都是混在一起的。人人对人人都没有偏见固然好,但却几乎不可能。
最近几年,我越发觉得,对于一些根深蒂固的看法,即便是好的,也有必要重新思考。比如香港的年轻人经常触及一些很大的议题,他们的不少方式——非理性地反复喊口号、一股脑地为反对而反对,我自己并不赞同。但我后来想了很久,觉得类似的实践,只要不倾向暴力,都会使人反思社会,以及自己在社会里的位置,而所谓进步,大多是由这种动力促成的。

《天水围的夜与雾》(2009,任达华、张静初主演)以2004年发生在香港的金淑英一家灭门案为题材。
记得我在准备拍《天水围的夜与雾》的时候,读到的报道纷纷把矛头指向警察和社工。因为现实里的女性受害人一直在找社工帮忙,而她生前最后一天,曾经走到警察局求救,当值警察叫她回家,她到家后即遭丈夫杀害。我最开始确实多少想通过电影让社会感到,如果这些机构做得更好些,类似的家庭暴力事件就不会发生。但随着调查深入,我发现导致杀妻的首要根源,是他们的个人历史、社会背景,是这段不合适的婚姻,而不止是当天发生了什么,不止是工、警察能不能救她:他们的历史已经酝酿了这段悲剧。其实,到最后我也不明白男方杀女方的真正原因——这是一个谜。这里就回到一个带有哲学色彩的问题,关于人性里那些邪恶的、沉在里头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关于人终有一死。于是,早先直接的批判就太简单化了。我挺疑惑的。当时我想找刘若英演,我很喜欢她,她也很想跟我合作,她的样子又有点像女主人公的原型,可刘若英看了剧本后断然拒绝,她说这个故事实在令人沮丧,而且毫无救赎。我也同意。但我没办法在故事最后安上一个光明的尾巴,你不可能在这个大悲剧里找到任何安慰。然而,这种事情在人生里是存在的,我们从村上春树的小说,从E. M. 福斯特的《印度之行》里都能体会到。你不能说,你不停去健身,去冥想,就把这个邪恶的、虚无的东西解决掉了。所以尽管电影剧本还是有批判性的,但这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不想那么表面地去控诉社会。

《天水围的日与夜》(鲍起静、陈丽云主演)
《夜与雾》拍得不那么好,主要是因为和《日与夜》隔得太近。2008年拍完《日与夜》,王晶让我趁热打铁,于是,2009年夏天《夜与雾》就开拍了。《日与夜》没有戏剧化的叙述,这部电影让我懂得了拍戏怎么不通过故事而情绪先走,但我还没从它祥和的气氛里走出来,而《夜与雾》是一个很戏剧化的东西,通过铺排情绪,你可以把它处理得很紧张、很惊心动魄。我当时的情绪不是这样的,自己的心意和剧本剧情不是配合得很好。所以《夜与雾》局部行,整体我觉得有点勉强。它应该有让人感到恐怖的一面,但目前的呈现仅仅是片段式的。也没办法了,不能那么理想了,不过还是拍了好。拍完以后,我估计大众比较失望,那些警察和社工倒松了一口气,因为没有过于尖锐地针对他们。这个戏当然可以拍到让社会都震撼,但我没有,我觉得那样是一种剥削,也拍不好,何况我真的没有那种愤怒的感受。
回到前面的议题,我想,如果我们对性别、性取向没有那么多偏见,从传统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中解放出来,对大家都平视一点,这个社会会比较好,不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总存在根本的人性和大自然里面的恶,而不会有天堂一样理想的生活,永远不会有。所以我觉得后来的《得闲炒饭》不是一部拍得很到位的电影,后面部分太理想化了,是比较勉强的。

《得闲炒饭》(2010,周慧敏、吴君如主演)的美满结局
您不少为人熟悉的作品——《投奔怒海》《客途秋恨》《女人,四十。》《千言万语》《男人四十》《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之所以复杂,似乎一个原因是它们都关乎代际:家庭的代际、政治的代际、教育的代际。代际的问题往往又纠缠着故乡和本源的问题。能说说您自己的家庭吗?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与和解、断裂与连续、差异与重复何以持续吸引着您?

《上海假期》(午马、黄坤玄、刘嘉玲主演)剧照:中国爷爷和美国孙子在九十年代上海的宾馆,电视里的英语节目讨论的是美国在中东的存在。
许鞍华:我们拍戏,总是根据题材,在里头放进一些自己的感受,不可能从一而终追求自己想说的。比如拍《胡越的故事》,事先从来没有想过要拍边缘人、流浪人,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我是想拍这种流浪的感觉,后来通过做资料搜集才慢慢了解到,越南华侨和土生土长的越南人是不一样的,我自己的立场跟他们差不多,访问越南难民的时候,好像就很熟悉,非常感同身受,一点隔膜都没有。

《胡越的故事》(1981,周润发、缪骞人、钟楚红主演)
我其实一直没有想故乡和异乡的问题,直到《客途秋恨》,因为这真的是我的故事,我妈的故事。我三岁学的第一句诗就是“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以故乡的观念根深蒂固。人人都思乡,但我却不知道故乡在哪里。我出生在鞍山,爸爸妈妈都不是鞍山人,我们也很快离开了鞍山,如果说出生地是故乡,可我不是那里的人。故乡这个概念是很值得探讨的:是不是籍贯是哪里,你就是哪里人?香港大部分的人,有从广东来的,有从上海来的,他们那个时候都没有回过故乡,是不是他们爸爸妈妈的故乡就是他们的故乡?这些问题我拍《客途秋恨》的时候想了很久。
我妈大概二十岁左右从日本去了东北,待了两三年,就碰到我爸,两个人结了婚,生了我,接着去澳门,过了五年,就到香港。从我妈离开日本那一天,一直到十几年后,大概1960年代初,她才第一次跟我爸回了趟故乡。某种意义上,我的童年和少年,都深受我妈的故乡情结的困扰。她老是想日本,觉得做了非常大的牺牲来到这里,什么人都不认识,什么都不懂,也拒绝和很多人来往,觉得人家看不起她,有一箩筐的苦恼。我爸爸很同情她,经常带她去看日本电影,为了她下班以后去学日文,还买了很大的日本人偶摆在家里。可以说,因为我妈思乡,家里弄得有点民不聊生。我和电影里的张曼玉一样,本来并不知道我妈是日本人。我想怎么搞的,她怎么那么喜欢日本?我们那个时候的社会氛围是对日本人有偏见的,因为刚打完仗不久。一直到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大家才开始哈日。后来我跟我妈的矛盾闹得很厉害,我爸爸便告诉了我真相。在我忍受了二十几年后,二十五岁那年,我跟我妈回了故乡。可是她到日本,却很看不起当地的日本人,嫌他们对女性不好,嫌他们要跪着坐,而且我舅舅家是老房子,条件也不佳。于是,她老是说要回香港的家。那这么多年的思念、折腾不是白过了吗?

《客途秋恨》(1990,陆小芬、张曼玉主演)剧照:母女和解时刻,陆小芬说:“在我的记忆里,你爸爸是这样讲的,永远和我在一起, 他真的没有回来日本,反而是他女儿回来了,真是越亲的越远,越远的越亲。”

《客途秋恨》最后,“我”守着老去的爷爷,忆往昔,画面回到童年,粤调响起:“凉风有信,秋月无边……”
我七十年代在伦敦念书的时候,常常逛唐人街,也让同学拍过那里,知道那边华人的生活:好多人从来不出唐人街,每天都在麻将馆或者餐厅的宿舍,老是想着故乡。我拍《客途秋恨》,多少对移民的这种故乡情感有反讽的态度,那是一种逃避现实的负面情绪。我也不是批判我妈,她愿意怎么感受,就怎么表达,只是我觉得,今天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人口在不停迁徙,如果一个人到国外,总想着故乡,而不甘于发展新的生活,跟当地融入,是很可惜的。我们可以既为故乡做很多事,又投入新生活,而不是让故乡的概念对自己和家人造成干扰。这是我相对有一个自己的看法,用自己的经验,在1989年做的一次尝试,但通常拍戏都不会有了新看法才拍的。
两代人关系复杂是很自然的。父母和小孩之间肯定有很多矛盾,生活环境不同,父母不停要付出给小孩,如果小孩不感恩就一定会有冲突。人是很不喜欢感恩的,尤其对父母,因为又不是我们想被生出来的。你们生我们出来,又老是要我们感谢你们,也不对。《男人四十》拍的是师生,主要是剧本好。岸西跟我说,她想拍一个师生恋,不过是一个师生恋的变奏,不光讲他们俩的苦恋,而是再套另一个师生恋,那么这就会从一个爱情故事的层面,通向深层的历史——这个历史是重复的。就比较远、比较大了,看人生状态的那种反讽,也看得比较深了。可是这种反讽,我觉得是比较可信的事实,比爱情可信一点。


《男人四十》(2002)剧照:伴随着《江河水》音乐,张学友和梅艳芳背诵《前赤壁赋》,随后出现了科教片里长江三峡的画面。
即便在您最香港的电影里,“大陆”也不会缺席(哪怕只是古诗词和山水画的象征,或某个次要人物的工作经历)。然而,“母国”更像是迁徙、流动的前提下的构成性事实,是一个环节。发生在香港的“革命”也类似——您说《千言万语》是一部存在主义而不是“政治”电影。可否可以这样说:这里,在您、您的电影、电影里的人物和“母国”“革命”之间,不是简单化的“爱”的关系?

《桃姐》剧照:开头,刘德华身后的山水画。
许鞍华:我们一直在殖民地政府底下生活,习惯了它们的一套,它们给我们什么,不给我们什么,都习以为常。他们不给的东西,像参与政策的讨论和制定,我们是非常敏感的:从小父母就叫我们不要谈政治,好好读书,最好找一个医生、律师这样的职业,即使到处打仗你都可以讨到生活,做裁缝也好。这是一种难民心态吧。回归以后,香港人参与政策、政治的诉求变得那么强烈,原因就是,过去是都明白摆在那里的,我们生下来或者到这里来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不给就不问了,而如今有了新的政府,就会重新思考以前没有思考过的东西,会问为什么。我七十岁了,非常习惯以前那套,虽然我知道那有很多缺点。对于祖国,我们肯定是非常有感情的,我祖父教给我诗词歌赋,我也读了好多中国历史、文学的书,感情特别深。这种感情,虽然有点浪漫,却不是不真诚的。可是,要把这样的感情变成不停地去响亮地表达对祖国的爱,还是有点困难,因为你本来已经有的东西,尤其像情感那么私密,是不太适合老是很响亮地表达的。我自己是这种感觉。
《千言万语》所拍的,在殖民时代的香港,肯定是一个姿态多于现实的东西。我觉得他们的悲剧是,在香港搞的革命是二手的,他们做的其实都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我想革命,就算不是在香港,通常都不会成功,都是悲剧收场。我特别喜欢看十月革命后流亡的人,比如托洛茨基的经历,很传奇,充满悲剧色彩,也特别让人迷惑。看了这些故事,我越来越倾向于老老实实做好每天的工作。现在固然没有选择的机会,可就算让我选,我想我也不会去搞革命,我宁愿做好手边的事,而不去做那些传奇的人,尽管他们值得我们仰慕。大概我年纪大了。

《千言万语》(1999)剧照:谢君豪等人踩英国国旗时,黄秋生唱着《国际歌》。
《千言万语》里黄秋生的原型甘神父,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把切实的行动、生活和革命结合起来的人。当然他是个神父,不太一样,有终极的归宿,而且身份各方面都有保证,人家不会怀疑他的目的。他把毛和他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把强烈的信仰付诸日常的实践,视所有人为姐妹弟兄。最近有一部纪录片拍了他二十年的生活,他还是和过去一样。我非常感动。我问他,你是个毛派,你怎么看现在大陆的消费主义?他说他还是敬仰毛的朴素和精神生活,他不觉得现实的变化是个讽刺。于是,他继续帮助贫穷的人,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电影的最高境界
从《疯劫》开始,一个贯穿您几乎全部作品的形式标记是倒叙和闪回,将线性时间打散,让记忆说话。您曾说,直到《女人,四十。》才学会处理时间,而在《半生缘》,这种处理趋近成熟。能说说您电影的时间和时空关系吗?

《疯劫》(1979,万梓良、赵雅芝、张艾嘉主演)
许鞍华:我越来越发现,拍电影就是处理时间和空间。人人都说我的戏慢,我看王家卫的戏,其实他的镜头是很慢的,每个镜头都很长,为什么人家觉得快呢?当然他有好多蒙太奇和音乐,可是他的每一场戏都是真实的时间,而其中发生的,是剧情最悬疑的部分,他不会给你这场戏的头和尾。李安也是。他看起来很写实,其实是高度精简的,戏表达了两个人的关系,指出一些可能性,然后就完了,悬疑度很高,所以这个戏好看,不是像我们以前一样,从头拍到尾。也就是说,在每一场戏里都找到开始和结束的点,让观众产生高度真实的感觉,好像经历了人物的感受似的,而不是呈现模拟的真实时间,啪啪啪剪成MTV一样。比如《天水围的日与夜》拍看报,看了三十秒,一般剪辑可能啪就剪掉了,让人家知道看报就完了,但我就让它留在那边很长,只要你知道这个戏最后要去哪里就行。所以《日与夜》里很多真实时间的瞬间都是没有戏的,观众却能比较深刻地感觉到人物的生活。并且这个戏会快,可观性会强,拍两个人讲话,只要是表达到他们关系的瞬间就够了,不用拍之后他们怎么出门、关门……这是处理一场戏的时间。
至于整部戏的时间更就复杂了。尤其过渡性桥段的表达,要让观众感觉不到这个时间是经过处理的。你看《恋恋风尘》,好多年过去了,女孩也离开他了,但这个离开,侯孝贤都没拍,然后很快就是回到家里,接下来好像有个空镜头,就完了。在侯孝贤的电影里,时间的压缩和伸延变成了戏的一部分。可以说,处理时间对戏至关重要。
接着说空间。我开始是拍实景的,诸如厕所、两米乘一米半的房间,我们都把机器塞进去找到机位,然后拍出来那个感觉就像真实空间。可我到内地拍戏,所有人都给我很大的景,很穷的人都给很大的景。一个很大的景,要拍得很挤,不是不可以,一个比较小的地方,要拍得很宽松,也不是不可以,用镜头是可以处理的,可是我不喜欢这种处理。我喜欢看到一个景就把它真实的空间拍出来,尤其室内景,因为人居住的地方的表达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室内空间就变成了这个人引申的部分。所以必须小心翼翼地找到一个刚好能拍的、对的空间。至于让人家熟悉这个空间,也是一个学问。要分成好几场戏来拍,每一场不断有变化,这样观众看到的室内景就不会光是一个布景,或者一面墙。我觉得我对这几个方面开始有点心得了,就比较高兴。


《投奔怒海》(1982,林子祥、缪骞人、刘德华主演)与《阿金》都以长镜头开头。
我开始拍戏的时候,喜欢用回想和长镜头,觉得好玩,以为这样才有艺术价值,戏的整体效果才好。其实这两个都可以归到时间和空间问题。当时看了好多七八十年代的欧陆电影,都是长镜头,跃跃欲试。其实长镜头就是一个有悬疑的空间,你不剪,时间是真实的,你跟着这个人,不停地发现一些新的东西,感觉没那么闷,有动感。我现在的观点是,镜头不能为了长而长,为了动而动,没有原因,其实长或短都没关系的。Flashback(闪回、倒叙)也是那个时候的时尚,很多文学都喜欢回想,比较流动,更不用说电影了,所有六七十年代的大师都用闪回,很自由。可是我觉得电影的最高境界,不是让人家突然感觉到你回到以前,用太多外在的电影感的东西,把这个作为主要的目的,而是最好不着痕迹地在戏里出入。八十年代,看杨德昌的《海滩的一天》,我发现它的回忆镜头不是用来说明现在,或者表达心情的。那个回忆就是现在,因为在电影里其实没有过去和未来,你只要呈现出来,过去和现在是有同等分量的,都是现在,观众知道是过去,可是他的领略是现在的,所以我觉得杨德昌在这里特别好地发现了电影的本质。电影的灵动性可以像画一样,把两个空间并立在一起,而不是一个当成过去,一个当成现在。这里有无限的可能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吧。


《海滩的一天》(1983)剧照:胡因梦穿梭在现在与过去。
另外令我印象深刻的风格,是您对看的自觉。这不光体现在您早期电影的多重视角,更体现在您后来经常在电影里插入新闻录像、历史照片、纪录片片段、监视器画面,继而到最近两部作品,您都采用了人物对镜头独白的“伪”纪录风(《明月几时有》里您本人作为采访者出镜)——这是对现实的逼近吗?还是对电影存在方式的探索?

《明月几时有》(2017,周迅、彭于晏、霍建华主演)的黑白画面

《黄金时代》剧照:王千源饰演的聂绀弩对着镜头讲述萧红、萧军离开民族革命大学之后的不同去向。
许鞍华:《明月几时有》里梁家辉讲这些话,并不是一开始的设计,后来为了叙事顺,才加上去的,黑白也是临时决定的。《黄金时代》人物对着镜头独白,倒是有点想探讨我刚才说的《海滩的一天》的问题。当演员对着观众说话,他已经在戏外,开辟了一个观众空间,可是在《黄金时代》,角色就在1932年的同一个空间里,冲破了时间,在镜头前面预告以后的事。这意味着什么?可能给人一点恍惚和超现实的感觉:演员超越时空,讲过去未来,你会对这一段是真是假产生怀疑。如果在舞台上这么用就顺理成章,而电影一直都非常naturalistic(自然主义、写实主义的),没那么风格化,我的初衷是让观众反思,其实电影是可以这样的。不过大部分观众没有这样的意识,只感觉很怪,很突兀。虽然我这次失败了——很多的时候,电影的本质的东西是会失败的,可能一些根深蒂固的习惯不能冒犯,不然观众就会不知所云,或者感到厌恶——但如果类似的尝试成功了,就可以达到一个不同的、崭新的效果。我想,《黄金时代》的这个观念太复杂了,而看电影都是一些即时立刻的反应,所以不行,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比如在一种和前后都不太一样的环境里对镜头说话,会好一点。不管怎么说,如果我有想法,都愿意去尝试,不过想法不是常常有,而尝试往往会面临很大的风险。

《疯劫》里的推轨变焦镜头:“张艾嘉整个人定住,而云雾在她后面飘动。”

《千言万语》里的“无证妈妈”节目
我为什么那么喜欢在电影里插影像资料呢?可能因为这个戏涉及的对象或时代,我们本来就有好多这种资料,而且我觉得,像讲1970年代的香港,你需要看当时的影像。不过现在我也不喜欢再用这种手法。我现在喜欢一个电影更简单,更纯粹,要用的时候还是用,可不要因为这段东西好看而用。一个戏里头的人物关系、你要表达的东西,用什么方式都好,拍出来就行了,不要炫耀技巧,不要让技巧跑出来,我觉得是最好的。
到底想在拍戏里头得到什么
回望您亲历的香港影史,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八十年代初仿效好莱坞分工模式,建立明星制度;九十年代初逐渐失去东南亚和韩国市场;九七后香港导演北上内地。您怎么评价这段历史,以及您和它的关系?早在1984年拍《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您就和内地的电影工作者有深入的接触,到九十年代和新世纪则更频繁。能说说您的内地拍片经验吗?

《书剑恩仇录》(1987)
许鞍华:对于这段历史,我没有什么宏观的看法,我只是其中的一分子,随着潮流找戏拍,找生活而已,连领导者都不算。你看我的际遇:刚开始的时候很好,碰上大片厂没落,人家都想看一些新的东西,好多朋友、影评人支持,吹捧,我们好像很成功的样子。接着就商业片上来了,很多台湾片报了名字、类型、演员卡司,投资人就给订金开戏,这样的戏开了很多。那段时间——大概从1986年到《女人,四十。》——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组里所有的人,不管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都同时在拍三组戏。《客途秋恨》的化妆,定了妆以后就交给助手了,因为他有七部戏在手,有点像现在的内地。张曼玉的经纪人对我特别好,他说,张曼玉在你拍摄期里,会接别的戏,不过以你的戏为优先,如果你给她戏,她先给你戏。我听了特别感激。那时演员也非常厉害,从一个戏走到另一个戏,甚至张曼玉、钟楚红最好的表演都是在这段时间:在至少同时拍两部戏的状况下,每一部都提名。所以我也不敢迷信演员专心拍一个戏就一定更好。
我对内地还是非常憧憬,一直想回去,所以一说拍《书剑恩仇录》就去了。开始的时候当然很不习惯,不管是生活,还是跟内地的片厂合作,都不习惯,大家制度不同,内地剧组规模很大,不过还是拍完了,当时天津厂的同事,我们现在还是朋友,还有联系。到九十年代,《女人,四十。》开始,我反而比较好了。因为香港没那么多戏拍,大概少了一半,人人都是一组戏。而且我拍的类型成本低,所以我是稳定有戏拍的,也比较容易拍到想拍的题材。到了现在合拍,大家都有好多戏拍,也不怎么看你拍得好不好,但这是市场、观众、文化……各方面纠在一起导致的结果,我也无能为力。尤其现在中国大陆的发行我都不认识,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以前在香港我是清楚的,现在变化太大了。

《女人,四十。》(1995,萧芳芳、乔宏、罗家英主演)
应该说,我一直都在适应:适应拍电视,适应拍大电影,适应拍商业电影,适应在商业电影的洪流中拍所谓艺术电影,适应在合拍片中找一个位置拍自己想拍的电影。对于我,从非合拍片到合拍片并不是一个很关键的变化,不存在裂断。我反而不能适应去好莱坞。我试过去那边和他们磨合拍一部戏,后来我自己都放弃了。一来我不愿意每天吃西餐,讲英文,二来我觉得,到最后,还是为自己住的地方拍电影最有意义,我反而没那么大的野心要全世界的人都看我的戏,像功夫片一样,我拍一些戏能有人看就好了。目前最大的困难还是年纪,现在叫我拍超过十二小时就很累了,我也没那个精力跑来跑去跟老板沟通,处理那么多事。另外,内地的电影肯定起来了,我们如果要进去竞争,恐怕没有新导演的竞争力,他们会觉得你都不懂这边的生活,至少没那么懂。大概到了优胜劣汰的地步吧。所以我比较心安理得,想拍就拍,不拍也行。我觉得我已经很幸运了。
读《许鞍华说许鞍华》不同时期的表述,不难勾勒出您对电影的一般理解:您反对概念先行,反对电影的“教训”功能,强调电影的形式即内容,重要的是感受和想象;另外您反反复复地说钱和老板,您在乎票房,因为这对获得下部电影的投资很重要。电影和意识形态,和资本如此接近,您觉得理想的导演应该在其中扮演何种角色?您对电影这种形式的未来乐观吗?

《许鞍华说许鞍华》(修订版),邝保威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8月出版,532页,48.00元
许鞍华:没所谓乐观和悲观吧,这个时代的事情,都不是我们能左右的。我想,如果我今天从电影学院出来,观念跟以前恐怕不一样。我不会立刻选择去拍剧情片,因为剧情片是比较个人的表达,同时又是最大众的表达,可以想象那个难度。你有那么大的魅力可以让人人都喜欢看你的戏吗?越个人的戏,观众的数量越少。如今技巧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有了DV,人人都很懂,制作效果很容易,不像以前,老要问某个镜头是怎么拍的。同样花时间,我估计会拍纪录片,如果音乐感好一点,就去拍MTV。我不觉得拍这些是进阶到拍剧情片的手段,它们是并立的媒介,有各自的观众。如今人人都能拍戏,平台比较民主,各个媒介有不同的重要性。当然难度最高的还是剧情片,但不是这样就必须要拍。
我一直拍戏,只是希望能拍到我想拍的东西,或者放一些我的东西进去,如果有人看,收支平衡,我能继续拍,就很满足了,下一部要是还有进步,就更好了。这是我的底线,一直没有变。我最高的渴望当然是去戛纳拿个奖了(笑)。其实你只要让我每天都有戏拍,我没有想过要怎么样,对财富更没要求了。很多东西确实是干扰,拍完《投奔怒海》以后,人人都求我替他拍戏,我又不能同时拍几个戏,反而不知道选哪一个好。我觉得重要的还是可以坦白地告诉自己,到底想在拍戏里头得到什么。
关于老板,我说得很多。其实是我心里害怕,害怕得不到肯定,害怕没有工作做,可是虽然一定程度上会考虑他们的感受,敬畏他们,我还是我行我素的,我做不到因为他们是老板,我就拍他们想要我拍的东西。我会从他们的立场考虑——也是为了自己,因为知道他们要什么,我比较好找他们投资,很多新导演不知道市场和竞争的厉害,其实哪怕是纪录片也有它的市场、它的价钱,你不懂这个就不能生存。不过最终还是不要忘了你本来要做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