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桑用“幻影”定义自己的小说。故事无论是怪诞、恐怖,还是带有宗教色彩,都像是作者的幻想。幻想的界限相当清晰,它不脱离尘世,不升入高空、坠入空想,而是“与现实接壤”。这是作者用本能就可以选定的界限,这也让作品得以和融在现实中的读者接壤,如果再与霍桑喜好说教的写作特点匹配,就更容易让作品产生他预期的效果。不过,《威克菲尔德》并不说教,这也保护了这篇作品的成就,没有受到说教的伤害。
在《威克菲尔德》的第一段,霍桑给出故事的梗概:一个姑且叫威克菲尔德的伦敦男人,突然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住到隔壁街道租来的房子里,整整二十年没回家。二十年后,他又突然回到家里,“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
威克菲尔德的出走,像是一场试验,一次对社会秩序的小小反抗。但重要的是威克菲尔德反抗的方式。他的反抗是温和的,甚至是易碎的,这一点,才是小说最动人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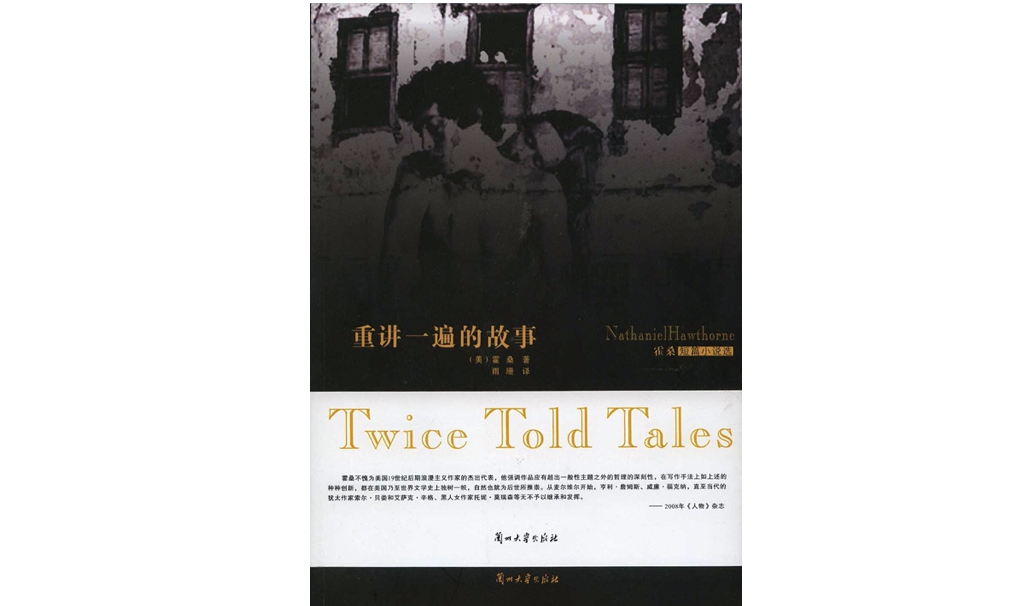
《重讲一遍的故事》,纳撒尼尔·霍桑著,雨珊译,兰州大学出版社2009年8月版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从波登大学毕业以后,霍桑把自己闷在二楼的房间里,几乎不与母亲和其他人说话,整日写他那些或怪诞或恐怖的故事,一写就是十二年。这是一段漫长的半隐居生活,他处在孤独中,只能与自己为伴。霍桑并没想追求这种生活,而似乎是顺其自然地依从了生活的流向,莫名进入了异于常人的生存境地。他曾写信解释他的这段生活:
“这是一间中了邪的屋子,因为千千万万的幻影盘踞整个房间,有些幻影如今已经问世。有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待在坟墓里,寒冷、动弹不得、浑身麻木;有些时候又觉得自己很幸福……”
生活显然是矛盾的。其中的寒冷不言而喻,有谁愿意常年住在监狱里?但他却也因此得到了幸福:那些“幻影”造就的愉悦、兴奋乃至生理上的颤栗。对霍桑来说,这种感受是辛苦创作之后的最大福利。在这个意义上讲,说霍桑只能与自己为伴是不公正的。幻影的数量“千千万万”,对于一个沉闷小镇的居民,他接触的东西实在有些太多。博尔赫斯在1949年3月的讲演稿《纳撒尼尔·霍桑》中说:“这个数字(即千千万万)并非夸张;十二卷的霍桑全集包括一百多部短篇小说,这只是他日记里大量构思草稿中的少数几个。”《威克菲尔德》就是“少数几个”之一,收录于霍桑的首部短篇集《重讲一遍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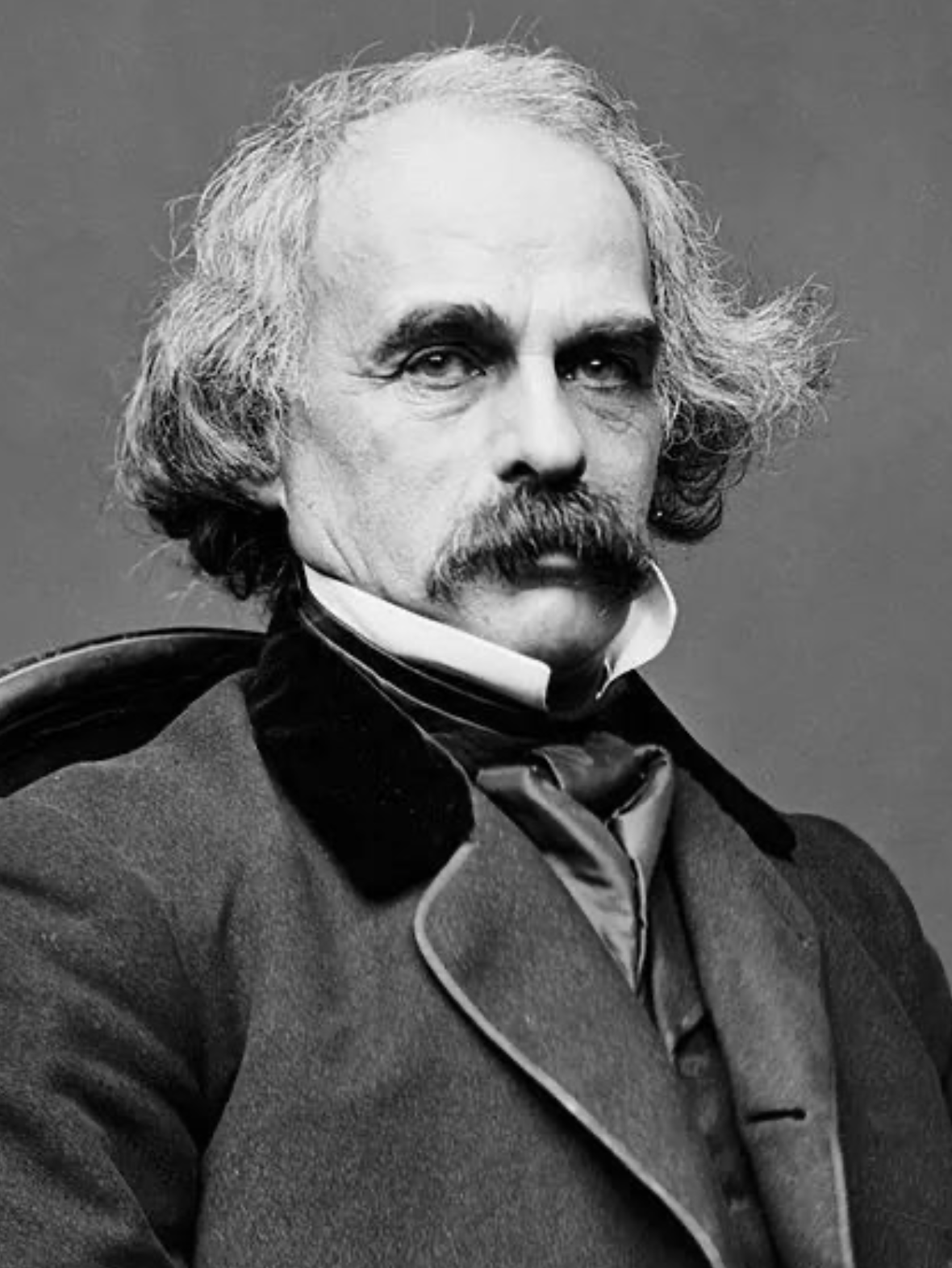
霍桑(1804—1864),美国19世纪后期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家,代表作为《红字》。对美国后世作家影响巨大。
霍桑用“幻影”定义自己的小说是恰如其分的。故事无论是怪诞、恐怖,还是带有宗教色彩,都像是作者的幻想。幻想的界限相当清晰,它不脱离尘世,不升入高空、坠入空想,而是“与现实接壤”。这是作者用本能就可以选定的界限,这也让作品得以和融在现实中的读者接壤,如果再与霍桑喜好说教的写作特点匹配,就更容易让作品产生他预期的效果。不过,《威克菲尔德》并不说教,这也保护了这篇作品的成就,没有受到说教的伤害。
在《威克菲尔德》的第一段,霍桑推脱说,这故事不是他个人创造的幻影,而是从某份杂志或报纸上看到的“真人真事”;紧接着他又说了故事的梗概:一个姑且叫威克菲尔德的伦敦男人,突然毫无征兆地离家出走,住到隔壁街道租来的房子里,整整二十年没回家。二十年后,他又突然回到家里,“仿佛才离家一天似的”。
事情如此简单,似乎可以就此打住了。但接下来,霍桑引领他的读者开始幻想。如果我们把从报纸上看来的这个故事看作霍桑的幻想,那接下来的想象,可以说是幻想的幻想。“威克菲尔德是何等样人呢?咱们尽可自由想象。”想象中,霍桑给了威克菲尔德年龄——中年;性格——在所有丈夫当中,他大概最忠实,因为生性疏懒,感情不论何处寻到归宿,就安营扎寨。他脑筋聪明,却不爱动,老是懒洋洋地想呵想呵,漫无目的。要不就是缺乏达到目的的活动。他思想萎靡无力,很难抓住恰当的言词表达;爱好——他还有种耍花招的本事,这本事不过是保守一些简直不值得透露的小秘密而已,没啥了不得。
如此平常的人。又恰恰是如此平常的人,而非那些怪人、奇人、疯人、傻人,制造了这桩奇闻。他莫名离家出走,备受煎熬,曾想立刻冲回家去,却克制住了自己。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一个月,又一个月,他就住在可以看到原来那个家的地方,孤独地活着,从社会意义上说,是几乎像死人一样活着。他习以为常的社会角色没有了,巨大的齿轮少了一枚小小的钉子,其中的伦理道德、责任义务、权利秩序不再对他起作用,但二十年的独居让我们看到,原来他(我们)连小钉子都算不上。妻子也曾因为他的出走生过一场病,但不久便认定他死了,虽然怀着悲痛孀居,也渐渐没什么影响了。总之 ,威克菲尔德出走引起的微小波澜,很快复归平静。但让人可气的是,当生活已经习惯了没有他存在很久后,他又回来了,还“从此成为温存体贴的丈夫,直到去世”。
威克菲尔德的行为像是一场恶作剧,但显然又不是。毕竟,一个人有几个二十年呢?也许称他的行为是一场试验更准确,或说是一次对社会秩序的小反抗、一次对社会俗套说“不”的表达。然而,最值得注意的也许是他逃离的终点:“就在自家旁边的一条街上”。他的反抗是太不激烈,也没有另一个方向,而是轻柔的、单纯的。特里林在评鉴梅尔维尔的《缮写员巴特比》时说:
“不论是被要求适应按部就班的律师事务所工作,还是被要求适应生活最简单的要求,巴特比都会做出相同的回答,‘我更愿不’——这一用语拘谨、温和,甚至文绉绉的;它所表达的否定意愿看似强度极低。……他的雷声越大,他(以及我们)就越相信他所拒绝的东西的力量、利益和真实存在。巴特比表示拒绝的寡淡套语具有相反的效果——拒绝对他所拒斥的社会秩序发出清晰明白的愤怒,我们可怜的寡言少语的说不者否认它的利益和它对他注意力和理性的任何要求。”
巴特比与威克菲尔德如出一辙。他们的反抗是那样温和,甚至带着易碎的触感,却更恰当地表达出他们对社会秩序和利益之诱惑力的否认。这是两篇小说最动人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