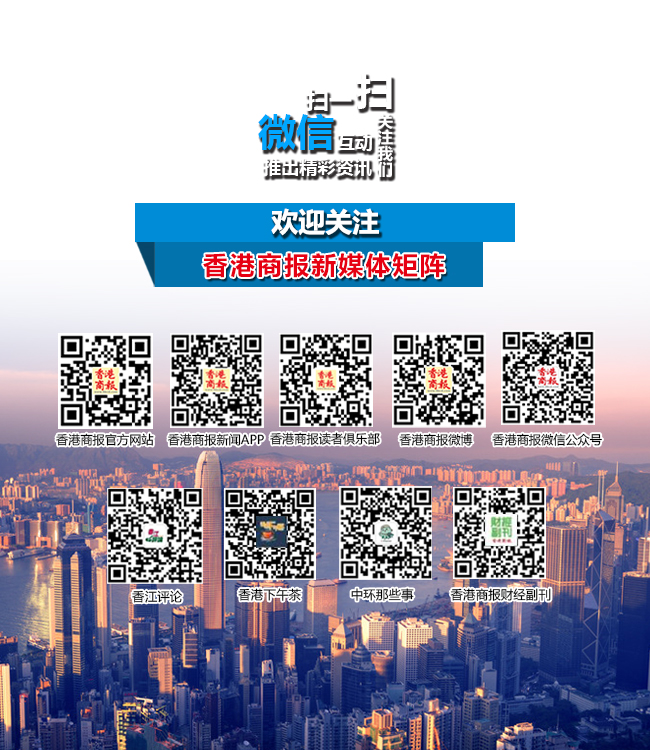2019是女性电影大年,女导演们从不同年代、境遇、身份入手,力图建立摧毁父权社会的电影语言,书写了一幕幕女性的生命体验。新的女性群像塑造,是否突破了以往性别叙事的时态,是否对两性关系提出新的诘问,是否达成了与男性的有效对话?
2019年,是“米兔”运动的第三个年头。“家暴”“精神控制”“性侵”等词汇,依然是网络关键词,令人悲愤的故事一再引发社会热议。当然,在沉痛之余,也有令人欣喜的消息:伊藤诗织的民事诉讼案胜诉,美国电影业大亨哈维·韦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被判有罪,女性完成首次太空行走,苏格兰向所有女性免费提供月经用品……
今年,联合国公布妇女节主题是“我是平等一代:实现妇女权利”。观之电影领域,不少佳作体现的平等意识,也在彰显这种理念。
作为当代最具有影响力的大众娱乐之一,电影为人类有限的人生体验带来了更广阔的视野,也为那些不被看见的群体困惑提供了发声的契机,女性电影尤为如此。女性电影的概念,包含着一些模糊的指认,它可以是女性电影故事,也可以是女性导演、编剧或者其他主创,或包含女性视角下的男性故事。
在概念的背后,实则有更为宽广的意义,它代表着女性看待世界的方式。它是区别于男性视角的女性电影表达,包含剪辑、构图、配乐、节奏、叙事等在内的各项环节,在触及社会学的意义下,企图影响现实社会的平权疾呼,可以重新建构“性与性别”的讨论空间,让无数在男性电影叙事中被遮蔽的女性情感、困惑、失语等逐渐显形。

第13届西宁电影节上,海清为国内女演员发声,呼吁行业消除性别歧视。
根据吉娜·戴维斯(Geena Davis,《末路狂花》饰演者) 媒体性别研究院的调查显示,全球电影业女性担任监制的比例为19%,编剧为14%,而导演占比只有8%。在全球卖座电影中,女性担任主角的比例不足25%。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到,在电影业中女性工作者的占比失衡,极大程度地影响了女性电影的可见度与其掌握的话语权。
发声空间的狭窄,似乎意味着在人们可见的视野范围内,那些已然突出重围的女性电影,有着义不容辞为群体发声的责任与义务。譬如,在今年奥斯卡提名名单中的《小妇人》(Little Women)、《哈丽特》(Harriet )、《蜂蜜之地》(Honeyland),在戛纳金棕榈大放异彩的《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of a Lady on Fire),位居韩国全年票房第14名的《82年的金智英》,还有由当红明星姚晨主演的国产电影《送我上青云》……
那么,这些女性电影到底完成了什么?仅仅是女性侵害经历的分享与传达,还是为男性及整个社会提供了反思自我的契机?

第92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蕾妮·齐薇格(Renée Zellweger,右)和最佳女配角劳拉·邓恩( Laura Dern,左)。
“你好好看着我”:渴望被注视与理解的呐喊
纽约女性主义艺术团体“游击女孩”,有一句著名的口号:“女性必须裸体才进得了大都会美术馆吗?”这句诘问,道出了西方绘画对女性偷窥和观看的权力关系。男性画家对女性裸体的描绘,更多是出自满足于父权社会的男性观看,电影亦复如此。在女性电影中,女性同样是置于被看见的位置,只不过她们并非裸体,而是主动渴望自身的情感、困境、生活被更多男性所体会与理解:看见是对存在的确认,没有被看见便是不存在。
好莱坞商业电影领域的女性电影,因为具有大众娱乐传播效果,实际上是最容易被看见的。这些电影描绘出现代女权运动中的高光时刻,当生活在马里兰州的女黑奴哈丽特·塔布 (Harriet Tubman)历经屈辱,终于为美国废奴运动摇旗呐喊时
(《哈丽特》);当新闻女主播梅根·凯利(Megyn Kelly)勇敢站出来揭露被新闻总裁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性侵的丑闻,激励了一个个跟着起立的受害者时(《爆炸新闻》,Bombshell);当长期被男人玩弄的艳舞女郎,开始豪夺华尔街客户的金钱时(《艳舞大盗》,The Hustlers at Scores),女英雄们对传统父权社会的报复叫人大快人心。
可是,这些女英雄虽然战绩累累,她们个人的生活样貌却空洞乏味,普通女性的真实情感极度匮乏。也正因此,她们的摇旗呐喊成了虚晃一枪也,沦为一个个虚幻的榜样。

《艳舞大盗》剧照。
甚至有理由怀疑,如若塑造女英雄成为女性电影的范本,那么囿于一些复杂的原因面对侵害不得不沉默,没有足够的智慧与能力反扑男性的大多数平凡女性,自然而然就会成为被忽视的群体。当她们也想要争取更多被看见的权利时,却猛然发现可书写她们生存状态的话语空间已然被挤压。
在更为小众的艺术电影范畴,同样是寻求被看见,却更具有普世价值。《82年生的金智英》,代表着千万个步入婚姻殿堂后牺牲事业的家庭主妇。金智英身患产后抑郁症,导演巧妙地设置了一个可以被看见的病灶,发病时金智英被母亲“附身”,出口狂言妄语揭开身处男权社会的痛苦。
马其顿纪录片《蜂蜜之地》,讲述欧洲腹地最后一位女采蜂人卡迪斯(Hatidze Muratova)与长期卧床的母亲,在原野上相依为命的故事。电影的二元对立并非在两性之间,而是站在原始与现代、环境与生存之上,女性议题在卡迪斯与母亲的生活对话中自然呈现:一部分是出于人性的考量,一部分也是创作者心态上的静观与等待,不急于寻求共识,只为在银幕上呈现一位立体与丰富的女性。
论“看”与“被看”的关系,法国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展开了深刻的探讨。1760年的法国布列塔尼,年轻女画家玛莉安(Marianne)为富家千金艾洛伊兹(Héloïse)绘制肖像。这幅肖像是为艾洛伊兹出嫁所用,男方需看过画像以确认是否愿意娶她。玛莉安所画的第一幅请艾洛伊兹来看,一方面是坦白自己并非女伴而是画家的身份,另一方面也是渴望得到艾洛伊兹的认可。然而,艾洛伊兹却对画作大加批评,她否认这幅画并非自己的最大原因是她不想要这样被观看。
这幅画作的构图、色彩和人物表情皆为男性视角,是一幅合格的“出嫁画”,却并非艾洛伊兹的真实面貌。在玛莉安与艾洛伊兹渐渐产生同性情愫之后,玛莉安绘制了第二幅。直到这时,艾洛伊兹才认为真正被看见了,画中的她坐姿更为自然,表情也一改严肃。她的渴望被看见,不仅是寻求处境的真实传达,也是期待彼此感情能够得到确认。

《燃烧女子的肖像》剧照
在这部电影中,女性创作者的处境通过画作勾勒出来。在画展上,一位男子向玛莉安夸耀一幅描绘俄耳浦斯凝视的画作,他误以为这是玛莉安父亲所绘。而玛莉安则指出,这幅画是假借父亲之名所作。
回到开头的诘问:“女性必须裸体才进得了大都会美术馆吗?”在那个年代,女性创作者只能借用男子姓名,才具有其作品被挂在美术馆的权利,而她本人则将沉默地消失在历史中,永远被遮蔽,不被看见。
在《燃烧女子的肖像》将近末尾之处,明知两人之间的爱情不可能冲破藩篱,玛莉安在告别爱人后,即将夺门而出。艾洛伊兹喝令她回头“你好好看着我”,这一次的被看见既是爱人的呼唤,也是穿越历史抵达当下现实的性别平等诉求。
“但是,我太孤独了”:女性独立与恋爱需求并非势不两立
由演员转型为导演的格蕾塔·葛韦格(Greta Gerwig),继《伯德小姐》(Lady Bird)之后,与网飞合作拍摄了《小妇人》。原著《小妇人》毕竟是两百年前的小说,格蕾塔的改编为其增加了现代注脚。它没有按照原著的时间顺序进行讲述,开始于小说中没有出现的女主角乔(Jo)与书商对峙的场景。乔与原著作者路易莎・梅・奥尔科特(Louisa May Alcott)本人合体,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年代的女性作家,如何在只有“要么死亡,要么结婚”的两种畅销书结尾中做出不一样的选择。
乔拒绝婚姻,当她的姐姐梅格(Meg)即将出嫁时,她反抗剧烈,认为出嫁即是少女时代的消亡,也是失去女性独立自主意识的开始。影片更让人动容的是,当她拒绝邻居男孩的爱,只是因为不愿意结婚时,她与母亲之间有过这样一段肺腑之言:“女性有头脑,有灵魂,也有内心。她们有野心,有才华,也有美貌。我很讨厌别人说女人只适合谈情说爱,但是,我太孤独了。我渴望被爱”。
在选择独立自主的同时,女性也渴望有男子相伴,看似矛盾的两面并非不能共存。这样的表达是当下女性电影中非常稀缺的,女性对现有环境的反抗,不应看作是与男性的对立。与男性相伴,一同迈入婚姻也未必不是女性主义。当另一个模棱两可的结尾,乔奔向贝尔,他们在雨中拥吻,也并非一定是与时代妥协的大团圆,它很可能是乔既保持独立思想又拥抱真爱的一种选择。

《小妇人》导演格蕾塔·葛韦格,由演员向导演成功转型。
没有异性伴侣的孤独,在《蜂蜜之地》中被更为精确地传达。老母已经85岁的卡迪斯,错过了嫁人的最佳时期;当母亲去世,她只能坐在空空的床板上与小猫为伴。她不止一次与母亲对话,盘问那些曾经上门提亲的男人是如何被拒绝的。当她开心地展现笑颜时,是置身于邻居家的孩子们之间。卡迪斯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的悲剧归结于没有进入家庭生活,她曾向邻居孩子坦言:“如果我也有你这样一个儿子,我也会离开这里,一切将不一样。”
那时,厚重深沉的无奈与荒野的空旷,形成情绪上的契合。影片也顺带描绘了邻居的家庭关系,丈夫面对妻子无时不在埋怨对方在教育孩子与家务事中没能令他满意。但是,在卡迪斯的眼里,起码邻居家的妻子在严寒到来之时,可以随着丈夫举家搬迁至更温暖的城镇,这也未必不是幸福。由男导演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创作的《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虽说并非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女性电影,但在谈到女性独立与婚恋关系时,也是绕不开的一部佳作。电影开始于两封在离婚前写给对方的信件,他们纷纷用饱含深情的言语,回忆着这段感情的高光时刻。然而信件独白刚结束,男女主角就拉开了离婚的架势。
通过这样的处理,观众立刻便能感知双方并非已经没有感情羁绊,离婚的原因在别处。在随后展开的故事中,我们知道女主角妮可(Nicole)是一位戏剧演员,婚姻生活给她带来的是事业、生活、成长的限制,这似乎在将婚姻与女性独立对立起来。但当劳拉·邓恩扮演的女律师出现,向女主角灌输女权主义的立场时,妮可仿佛如虎添翼,找到了挺直腰板的理由。然而,这一切在律师辩论那场戏中被撕碎。两位辩护律师将婚姻问题上升到两性对峙时,等待离婚的两个人都沉默了。
他们无言面对的,是当下的社会困境。当两性斗争不得不成为打赢官司的砝码,如果不被贴标签,就无法满足社会的期待。为了一己私利赢得孩子,他们甘愿沉默作出牺牲,被推到势不两立的境地,这才是这段离婚故事最可悲的地方。

《婚姻故事》海报。
“他本来就应该做家务”:抱团取暖与有效对话之间的距离
男性与女性彼此之间,有着难以逾越的鸿沟,生理构造与情感体验不同,也操持着迥异的话语体系。纵然如此,两性仍旧抱着极大的热情要合二为一,共同生活,那么沟通与理解就一刻不停地要进行下去。与男性完成行之有效的对话,改变两性权力结构,恐怕是大多数女性电影的终极诉求。
《82年生的金智英》引发了整个东亚社会广泛的讨论,这是一部涉及女性权益在韩国受到方方面面制约与压迫的电影。影片以患有产后抑郁症的金智英为切入点,纵向回溯了这个82年生女性一路的成长历程,以及上一辈女性为家庭所做的牺牲,与此同时也横向剖开了当代女性在家庭、生活、工作上所遭受的各类不平等待遇。
如若没有这样一部阐述事实的电影,恐怕事不关己的男性们永远无法得知:原来,社会上存在着如此多的性别不平等,女性们默默承受着那么多的苦痛;原来,社会对性的禁忌,可以拿来方便地进行性骚扰;原来,女性的自主意愿必须得到尊重;原来,今日的幸福生活,是踩在姐姐与母亲的不幸之上的。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即便如此,偏见、情绪、权力关系、自我防卫等屏障横亘其间,《82年生的金智英》真的让弱势女性的诉苦传达给了男性吗?男性做家务不是对女性的褒奖,而是本应该分担的义务,金智英“他本来就应该做家务”的呼吁,在男性看完电影之后有多少人听进去了,答案不容乐观。电影在韩国被男性集体抵制,另有控诉男性不易的漫画《90年生的金志勋》广为传播。
除去韩国社会结构本身的问题不谈,这部电影为何不能进行有效对话仍值得探讨。电影包含着女性处境的多个面向,重男轻女、公司性骚扰、婆媳矛盾、玻璃天花板、同工不同酬等,却始终缺乏矛盾的焦点。当对女性生存困境的描绘没有核心论点时,将会演变成单方面的控诉与抱怨。而全片充斥着的情感宣泄,就像击打在空中的拳头一样,失去了力量,也自然而然地关上了对话大门。
因男性角色过于标签化,被网友批评有“厌男症”的《送我上青云》,也因为类似的原因,没能行之有效地抵达对话的彼岸。女记者盛男偶然发现身患卵巢癌,她需要接下自己并不喜欢的工作,来支付进行手术的高额费用。手术之后将失去性快感,她还必须尽快找个男人充分享受性愉悦。
电影也试图展现盛男作为大龄剩女所遭受的偏见与不公,但这些困境并非站在两性对立的角度,而更多是生存困境、性格障碍、原生家庭所造就的。她与金主的对峙大快人心,但反映的是不公的劳资关系。她对入赘男刘光明的理解,仅仅来源于对其性格成因的领悟。她为母亲梁美枝拍照,也并非出自两代人性别观念的互相认同,而是母女关系的亲情和解。所以,当《送我上青云》站在一个避重就轻的安全范围内,战战兢兢地谈论两性问题时,往往就因焦点的偏差与对方脱节,无法进行有效沟通。

《送我上青云》上映后,女主角扮演者姚晨与导演滕丛丛 。
从基本事实出发,不在对话中设限,《燃烧女子的肖像》在与男性沟通这个维度更加巧妙。故事的背景发生在法国偏僻的孤岛,所道之事就是两位女性的同性情谊,看起来是个在极狭小的电影空间里,书写独属于女性的故事。但这样一种女性叙事,却以开放的姿态欢迎男性观赏。
它并非孤芳自赏,其古典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融合的画风,提供了不分性别观赏美的角度。它也不存在咄咄逼人的两性对立,片中没有污名化男性,甚至没有男性角色的出现。女画家玛莉安唯一一次对性别不公的明确表达,也不过是提到女性画家被禁止画男性裸体。但,这并不表明这部电影没有力量,它的力量来源于更深层的涵义。
她没有悲愤,也没有呐喊,连反抗也不曾有。但是,她足够悲情。当心上人艾洛伊兹即将被从未谋面的男人拥有时,玛莉安只能画一幅对方的画像以示拥有。当女仆无法理解俄耳浦斯为何不顾理智坚持要回望爱人,最终导致变成石头的悲剧时,玛莉安解释俄耳浦斯想要的,不是永恒的拥有,而是作为诗人对情人记忆的留存。
这一番解释对应的当然是两个同性爱人的处境,她们做不了时代的女英雄,对于未来的安排只能默默承受。爱而不得的痛楚,是无论男女皆可以去感知的。在观众为主人公的命运嗟叹之时,《燃烧女子的肖像》也自然地突破了性别之间的惯常冲突,完成了对权力结构的重新反思与质疑。

《燃烧女子的肖像》富家小姐扮演者阿黛拉·哈内尔(Adèle Haenel)自曝受害经历,控诉法国电影业内普遍的性侵现象,媒体称之为“哈内尔事件”。
2020年,“米兔”运动还在持续进行。性暴力的背后,是深刻的社会背景与复杂的权力关系: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他们借由各种权力关系施加暴力,宰制了女孩与女人的身体,也宰制了她们的自由。在社会结构没有改变之前,发声的那些受害者,依然承受着不可承受的二次伤害与不公正的待遇。
在未来,我们期待更多更为成熟的女性电影被看见。它们所承担的,也不仅仅是在电影范畴里更新女性电影语言。更重要的是,抵达现实的维度,建立制度上的保障,为平权争取更多的合法性。
撰文丨黄依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