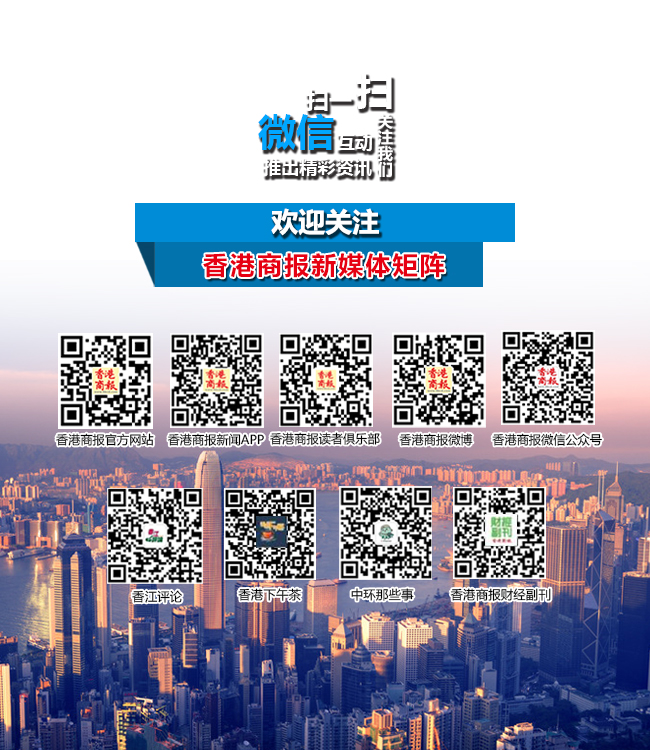袁野
一般來說,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發表言論,會被視為智識世界中的大事件。但保羅·克魯格曼先生在《紐約時報》上的文章卻不是這樣。這篇文章多少暴露了這位資深經濟學家最近無心治學,大概因為他每天花上13個小時瀏覽烏克蘭新聞。在這篇攻擊中國的文章中,他宣稱這個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正在經歷其新冠政策的災難性失敗」。
克魯格曼的論證意外地證明他邏輯錯亂。在文章的開頭,他承認,「我知道,我們西方的新冠肺炎疫情本應該結束,但每天仍有1200名美國人死于新冠肺炎,而且歐洲的感染人數再次激增,可能預示美國會再次出現暴發。」但這位美國經濟學家沒有評論自己國家的悲慘情況,相反,他急于抨擊中國,理由是香港每天有數百人死亡,堪比紐約2020年年初的災難場面;深圳重新處於封鎖狀態。「誰都不清楚中國這場新的健康危機何時或如何結束。」他寫道。
我甚至畫了思維導圖,試圖理解他是如何得出「這一切都說明形勢出現了巨大逆轉」這個結論的。而且只要這位學者從大量閱讀烏克蘭文章的時間中抽出一點時間,就會發現深圳僅僅一周后就恢復了正常生活秩序。
邏輯混亂在文章中延續。克魯格曼認為,中國的疫苗不夠有效,中國老年人疫苗接種率也不夠高,而奧密克戎變種有更高傳染性——因此中國應該放棄其「動態清零」政策。難道他真的相信讓病毒肆虐並解除必要限制可以挽救更多生命嗎?
克魯格曼忽略了另一個關鍵點。中國的指導方針是生命至上,而不是被一些西方輿論過分簡化為誤導性的「清零」。中國不遺余力地爭取更快更有效消除這一流行病。今年2月,《華爾街日報》也承認,中國的政策實現了死亡人數和經濟干擾最小化兩個目標,對其他國家有借鑒意義。我敢打賭,克魯格曼不會贊同華爾街同行的觀點,將繼續混淆中國的「生命至上」理念和西方定義的「清零」政策。
克魯格曼在討論中國政治上花費了更多的精力,這個領域他也不太擅長。他的每一句話里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主義」,從民族主義到西方必勝主義。他還不忘使用「開放社會」這個術語,這很令人欣慰,看來他還沒有忘記閱讀卡爾·波普爾。
盡管克魯格曼在2013年關於「中國經濟撞牆」的預測慘敗了,但他的經濟學教科書在中國賣得很好。他應該知道,在談論自己的專業領域之外的問題,例如流行病學和公共衛生時,做出任何預測都應該倍加謹慎。至少他現在下結論說「美國的制度在抗擊疫情方面更好」還為時過早。
不少來北京參加冬奧會的選手認為留在中國比在世界其他地方安全得多。克魯格曼先生,這是否也意味着中國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