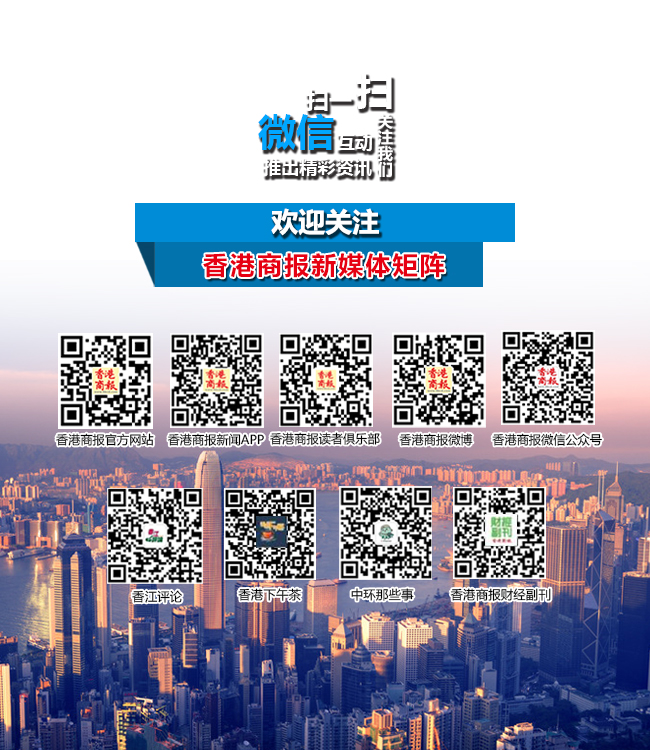作者:南翔
時值仲夏,嶺南多雨,海濱尤甚。這是地處汕尾捷勝鎮沙坑村西南一片廣袤的沙地,一陣大雨之後的間歇,海風從三四百米外強勁地吹來,高低散落的十多米高的桉樹婀娜多姿,白花花的腰肢很是搶眼,它們相互致意卻又各行其舞。
唐際根掐着手機看天氣,始終擰著的一對濃眉略略舒展道,如果預報準確的話,還有十五分鐘停雨。一群來自四面八方的學生已經手捧圖紙,分組待發。眼前二十來位考古志願者,既有來自國內外各名牌大學的考古或建築、傳媒等專業的學生,又有唐際根主持的南方科技大學文化遺產中心的成員——或簡言之唐老師的助理。經過出發前一周的培訓以及近十天的現場發掘,他們已經小有收穫,今天則是階段性總結的最後一日,個個躍躍欲試,希望得到剛從外地趕回的唐老師的點撥與評價。
此前領銜過多地重大考古項目,也是國際古物古蹟理事會專家的唐際根,田野發掘尤其是夏商周的斷代調查,乃其獨領風騷的領域。黑里透紅的臉膛大約是考古學者的標配,此時顧不得頭髮上淅淅瀝瀝雨水的他,一領短袖春衫掖在牛仔褲里,腳蹬一雙黑色跑鞋,顯得幹練而精力充沛。
預報準確,雨霽天開,同學們向海邊林地進發。唐際根顧及我與另外三位作者來得遲,錯過了此前的培訓與踏勘,有意落下來給我們幾位補充講解。平時在這樣流動的沙土上跋涉,小心的是腳下的打滑與深陷。他提醒我們留心地面的沙土,粗沙和細沙的區別,白沙和黑沙的意味。如果說白沙是自然地層的標誌,那麼黑沙則有文化地層的蘊含。
他彎腰捏起一撮黑沙,細細一吹道,但凡有過人類居住過的地方,無論是土質還是土色,都跟未經人類開發過的土壤完全不同。只要有人類在這裏生活過,勞作過,就必然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生活垃圾、建築遺存和古代器物。這樣的沙土通常顏色更深,甚至是黑色的,因為遠古的人類飲食起居給土地留下了痕跡,是人類的活動,在地表逐漸形成了一種有別於天然土壤的「熟土」,這就是文化層的含義。純白的沙粒或紅土,就沒有這樣的蘊含,那就是自然層。
經他這麼一說,我們立刻對腳下的沙土有了飛躍的認識,原本熟視無睹、了無感覺的土地,即刻有了遠與近、生與熟的識別,以及邈遠的迴響與裊裊的溫度。
他拾起一塊拇指大小的碎片,根據這塊赭紅色陶片的製作工藝及上面的繩紋,判定這會是相當於中原商朝時期的遺存。為了準確了解三千多年前的先民生活,包括炊具飲食等,有時需要將陶片通過粉碎,通過「熱裂解」的方法,將當年滲入陶器胎體孔隙中的有機物變成氣體,再從氣體中分理出氫氧根及其它成分,以此判定此陶器曾經煮過何種食物。這種方法需要的設備是氣相色譜質譜儀。唐際根團隊運用這種方法,曾經從距今6000年前的陶片中,發現古代「深圳人」曾經用陶器盛裝過蜂蜜。這次他準備用同樣的方法,分析汕尾3000年前的陶片究竟裝過哪一類食物。
由此可見,考古學,既是一門人文社會科學,又與物理、化學以及各種高科技緊密相關。文理兼通的唐際根,在這方面堪稱駕輕就熟,門徑一一鑿通。此前,我因在央視《考古公開課》上見識過他的專業而不枯燥的演講,特意請他到深圳書城和龍華書城分別講過《甲骨文是何時「製造」》和《「考古版」商王朝》兩題,一新耳目,受眾踴躍。
我在大學從教逾30年,對長期以來的高等教育也包括基礎教育,課堂一統天下而忽略乃至削弱了田野調查頗感憂慮。幾年前我帶着研究生赴各地採訪民間手藝人,包括木匠、鐵匠、刺繡、織錦、正骨、中藥炮製等十幾個門類,集成一本非虛構《手上春秋——中國手藝人》,正是期望當今的無論中小學生,還是大學生、研究生,多有社會實踐,人文親炙。看到唐際根的助理與學生個個英姿煥發、興趣盎然,不由得心生欣慰。
來到樹林裡,學生們前期開掘的幾個剖面一一呈現在眼前。比老師曬得更為黝黑的吳健聰,曾經在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跟隨唐際根主修夏商周考古,現在是唐老師的得力助手,他的現場講解,得到唐老師的頻頻頷首。一旁的秦苓育是在讀的英國諾丁漢大學考古學博士,出國前曾在唐老師做主編的《美成在久》雜誌做編輯,近幾年一直參與唐老師的考古項目。小秦口齒伶俐,性格外向活潑,編織著一干學業駁雜的同齡人——順便說一句,此行考古志願者多為女生,緊張而又卓有成效絕不亞於男生。如果以為考古者多為不苟言笑,見到秦苓育及一撥女同學的說唱逗笑,不能不刮目相看。
誰言揭秘多肅穆,如今荒野亦傳歌。
志願者們做的剖面,有台階狀,有斜坡狀,也有洞穴狀。唐際根一一探勘、講解。汕尾電視台一行冒雨跟隨採訪,女記者何碧懷,用塑料袋遮擋攝像頭上的雨水,舉著話筒不停地發問,乃至重錄,唐際根的每一綹頭髮都在淌水,卻顧不得我在後面撐傘,他說野外作業都是這樣,一會兒就幹了。在一處斜坡狀坡面,他稍稍用力,摳起一塊陶片,復嵌入。我們有所不解,他解釋道,類似這樣已經深入的暫時不動為好,陶片就與文化層渾然一體了。
忽而大雨,同學們四散而去,卻又很快在沙地上圍成一個大圈。為防周身淋濕,個個蹲下撐傘,朵朵花傘綻放,恰似一大簇色彩絢麗的蘑菇。考古現場可以是這樣辛苦又富有詩意,不是親臨,很難想象。
雨水漸收,學員們復又聚攏,聽老師點評、點撥、點亮。
整整一個上午的野外調查,我等考古門外漢,大開眼界,自嘲入門級指日可待。
下午,驅車前往沙坑博物館參觀。始知,沙坑遺址的發現與兩位具有考古知識的香港人有關,早在1934年,芬戴禮在麥兆良的協助下,一道揭開了沙坑遺址的面紗。可惜兩年後芬戴禮去世了,麥兆良獨立支撐,對華南考古漸漸入迷。在1940到1946年期間,麥兆良的考古擴大到了粵東的大部分地區以及福建,他常常以鄉村為居,騎著一輛叮叮噹噹的前面掛着籃子的自行車,四處奔走。採集工具很是簡單,一把螺絲刀加一把小扁鏟。麥兆良一臉絡腮鬍子,一身黑袍子,外加一頂黑帽子,一個從上到下黑黢黢的形象,嚴肅又滑稽,想不給當地老百姓留下深刻的印象都難。麥兆良此後更是積十數年之功,以不斷掘發的4000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物,有力佐證了此前考古學界爭論不休的一個議題:汕尾沿海有無6000-4000年間的新石器時代文化。
小吳告訴我,七八十年前麥兆良他們辛苦而持久的採集,當然功不可沒,只是當年宥於條件,主要是地表採集,地層採集資料不詳。任何發掘,只有由表及里的深入採集,才能呈現遺址的真實全貌。
就在同一天,唐際根和他的夥伴們從汕尾出土的陶片中,發現2枚用「籃紋「裝飾的陶片。唐際根判斷,這種籃紋陶片的年代大至在距今5000-4500年間,可證汕尾海岸曾經生活過該時期的人群。當年麥兆良發現的汕尾史前遺物僅限於距今6000年前與距今4000年後。這兩塊陶片的發現,填補了距今6000-4000年間的缺環。
回到荷塘簇擁的賓館,晚飯後齊聚一樓大廳,為沙坑考古的階段性成果復盤。助理吳健聰在屏幕上演示此番考古總覽的八個階段性目標,其一,無人機與地面結合,採集地貌模型數據;其二,在遺址去選定原點,建立級查網格;其三,對已有標本做類型學研究,取得必要的標本年代數據;其四,將標本依年代標註在地貌模上,實地勘察遺蹟,劃定「甜點區」……時間過半,任務完成過半。小吳說,現在正向第四階段的目標進發。
我問,何謂甜點區?
小吳答曰:具有發掘潛力及研究價值的區域。
質實言之,發掘的過程,不可能不在無甚價值的區域盤桓;而有價值的區域發現,正是在層層剝筍一般剔除那些無價值的盲點,逐漸縮小乃至最終在值得發掘的目標上斬將搴旗。
中途小憩,我步出大廳,驟雨初歇,天上漆黑一片;四野的荷塘卻鼓譟陣陣,海灘樹林已然沉睡,我憧憬沙坑遺址完整出土的那一天。此情此景,腦子裡跳出宋人的兩句詩:
黃梅時節家家雨,青草池塘處處蛙。
【作者簡介】南翔:作家、教授,現居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