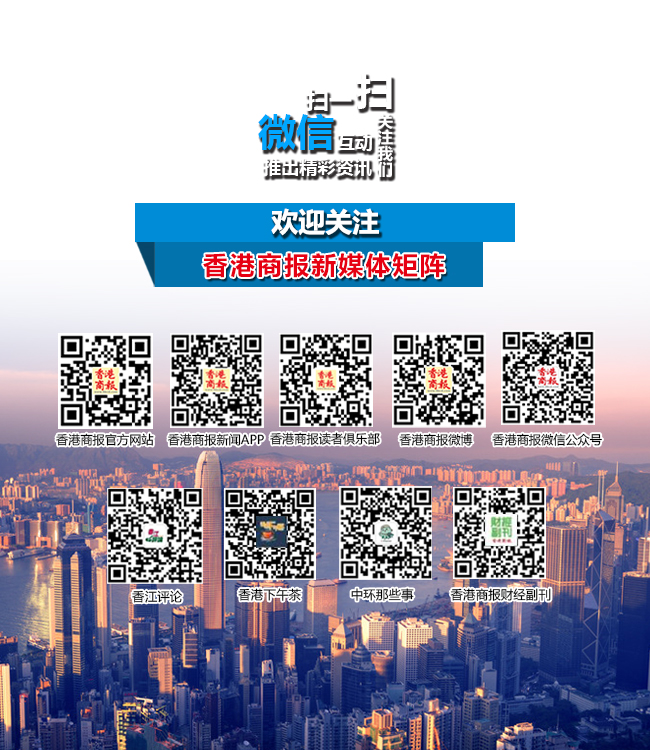在史學界,一些歷史學者,將注意力從宏觀歷史和風雲人物身上挪開,轉向芸芸眾生。
澳門大學歷史系講席教授王笛一直踐行微觀史研究。《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從一樁1939年的殺人案出發,細緻入微地考察了袍哥組織及近代基層社會的權力運作,呈現出一幅飽滿、立體、生動的近代川西社會圖景;《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以1900年至1950年成都的茶館為研究對象,以此為窗口,探求20世紀上半葉成都人的生活實態;《那間街角的茶鋪》,運用田野調查、官方檔案、現代小說以及成都竹枝詞等資料,生動展示了成都茶鋪的日常生活、大眾文化以及在這個公共空間中呈現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碌碌有為:微觀歷史視野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則描畫了中國社會從人口變遷、衣食住行、秘密社會到風俗習慣等方方面面的細節,站在小人物、小家庭的位置上,觀察普通人的生活。
透過王笛的文字,我們可以深切地感受到,歷史既有山川大海,也有縱橫阡陌,大人物的敘事無以取代下里巴人的命運悲歡。他說,海面上的波濤往往由下面的潛流決定,所以我們要把歷史放到顯微鏡下,仔細分析,只有聽到普通人的聲音,才能得到有血有肉的、更鮮活的、更真實的歷史。王笛認為,文明是由每一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人共同建構,歷史研究要給普通人更多的關注。在他看來,對普通人的研究更能「敞開」廣闊豐富的歷史內容,他們的柴米油鹽、生活變遷、命運掙扎,可以讓現在的我們看到纖毫入微的細部,從而觸摸到全面的、平衡的歷史。
近日,深圳特區報記者專訪了王笛教授。
■ 深圳特區報記者 尹傳剛
我們可以從有血有肉的「小歷史」中真實地感受大時代的轉折
深圳特區報:您的歷史研究視角往往是日常的、平民的、微觀的。這種研究方法和成果,讓人耳目一新。這讓我想起像史景遷、孔飛力等西方史學家,他們也往往是從一個小細節入口走進歷史。在《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序言中,您提到了史景遷《王氏之死:大歷史背後的小人物命運》,您如何評價其在微觀史研究領域的地位?您如何定義微觀史?
王笛:《王氏之死》或許是美國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部微觀史的著作。該書寫於1970年代。那時微觀史在西方還沒有興起,雖然在意大利和法國已有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還沒有譯成英文。史景遷的寫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觀史學的方法。如果現在再來寫這樣一本書,可能就沒有獨特的地方了。但我們要注意時代語境,在上世紀70年代,當史學研究的主流還是集中在帝王、英雄、精英、國家、政府這些方面,史景遷就將他的研究視野放在遙遠的山東郯城縣的一個農婦身上,從有限的資料里來描寫她的遭遇、她的生活、她的死亡,這是他眼光非常獨特的地方。從今天來看,這本著作具有里程碑意義。
究竟什麼是微觀史,學者的看法不一定完全一樣。我認為,微觀歷史要具備一些原則,例如要寫人(特別是普通人),要有故事,要有細節,要有正史之外史料的挖掘,等等。如果寫一位重要政治人物,比如曾國藩或李鴻章,寫得再細也不能叫微觀史,因為它研究的是上層人物。
微觀史對歷史的意義,就像在顯微鏡下對細胞進行觀察,側重點不在宏觀事件和精英文化,而在平凡人的日常生活。一個小人物、一個小家庭,到底能夠告訴我們什麼?對我們理解中國歷史有多大幫助?我認為,一個個平凡人的經歷,可以反映整個時代的變化,我們可以從有血有肉的「小歷史」中真實地感受大時代的轉折。如果沒有微觀視角,我們的歷史就是不平衡的歷史、不完整的歷史。
順着一些蛛絲馬跡,可能發現不為人知甚至波瀾壯闊的歷史
深圳特區報:您最近主編了《新史學》第十六卷,主題是「歷史的塵埃——微觀歷史專輯」。取名「歷史的塵埃」有何深意?
王笛:在我的印象中,這應該是第一部微觀中國歷史研究的專輯,裏面收錄了11篇微觀史論文。「歷史的塵埃」,主要是想表達兩方面的意思:一是一個普通人在這個世界上,渺小得就像一粒塵埃,但是研究一粒塵埃的意義,實際上揭示了千千萬萬有相同或相似命運的人的生活、生命和經歷。二是歷史經常被我們所稱的「歷史的塵埃」所掩蓋,如果我們想看到歷史的真相、看到歷史的內部,想發現被遺忘的歷史記憶,我們就必須拂開「歷史的塵埃」。那麼,我們尋找、解讀和分析這些資料,講述這些資料所呈現的故事,重新建構歷史,就是拂開「歷史的塵埃」的過程。
歷史上許多所謂的小人物,他們對歷史的貢獻往往被湮沒不見。我的論文《王先生的來信——巴黎和會大博弈下的小插曲》,是根據我偶然發現的一個姓王的先生給《紐約時報》寫的讀者來信,並對此進行追蹤而寫成的。那是1919年5月,巴黎和會各國博弈正激烈的階段,王先生的信件在《紐約時報》引起了一場小小的筆戰。我的追蹤牽扯出了一段被遺忘的歷史。在這個世界上,哪怕研究巴黎和會和五四運動的學者,也沒有誰——可能以後也不會有人——關注到給《紐約時報》寫信的這位王先生,歷史過去了就過去了,王先生和他的信很可能永遠都不會再被提起。
雪泥鴻爪,既然在這個世界上來過,就難免不留下痕跡。但問題在於,99.99%的痕跡,最後被歷史的塵埃永遠掩蓋了。所以有時候我想,我們歷史學家有時候也得靠運氣吃飯。一旦發現了前輩在歷史上留下的痕跡,我們便奮力追蹤,但是很少能抵達歷史的真相。我始終堅信,順着一些蛛絲馬跡,可能發現不為人知甚至波瀾壯闊的歷史。好像宮崎駿電影《千與千尋》中的那個小孩,一旦被引導進入了那個神秘的隧道,一個未知的奇幻世界便立刻展現在眼前。就這樣,歷史上那位給《紐約時報》寫過信的被遺忘的王先生,和生活在百多年後作為歷史學家的王先生,因為偶然的機緣巧合,居然神奇地相遇了,歷史的塵埃就這樣被徐徐拂去,歷史的真相就這樣被慢慢揭開。
歷史寫作是可以在文學上有所作為的,即回歸到文史不分家的傳統
深圳特區報:您曾談到,「要講一個帝王英雄的故事,能找到許多資料記載,而當你想去看看一個普通人在過去是怎麼生活的,就會意識到歷史遺留的空白。」請您具體談一談,微觀史研究面臨哪些困難?
王笛:首先是資料的困難。在微觀史研究上,必須先有資料,研究才能進行。這和一般的史學研究方法不太一樣。我們一般的史學研究是先定題目,再收集資料,但微觀史研究幾乎都是要先發現了資料,才可能根據資料進行研究。開始做微觀史研究的時候,找資料真的像是大海撈針,我就是去圖書館一期一期地翻老報紙。從前成都有份報紙叫《國民公報》,國內幾乎找不到齊全的收藏。幸好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圖書館有全套的《國民公報》縮微膠捲,我記得是120多卷。有時候看一天甚至一個星期,也找不到什麼有價值的內容。我整整看了一年的微縮膠捲,對視力傷害很大,但是沒辦法。就這樣,按照蛛絲馬跡一點點去找。而且這只是一份報紙,還有其他的報紙要查閱。
我在尋找關於成都「街頭文化」的資料時,在那些老報紙上如果看到有關於「茶館」「袍哥」的資料,也會同時搜集。其實,關於「茶館」「袍哥」的資料,我從1980年代就開始關注了。三十多年後,直到2018年我才出版了《袍哥》。經過這樣長期的積累,這幾年我陸續出版的書可以說是總爆發。
微觀史研究還面臨着一些讀者的不理解。他們不理解為何要去關心在歷史上沒有任何影響的一個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這不僅僅面臨着學術界的一個疑問,也面臨着一般讀者的疑問。
再有,就是寫作技巧的問題。囿於資料的匱乏,研究歷史上的一個普通人物,往往很難完成一個完整的敘事,在具體寫作過程中,會明顯感覺到有許多缺口。我們要下很大功夫,甚至迂迴去補齊,比如使用文學資料。有人認為歷史研究不可以使用文學史料,但我不這樣看,文學完全可能反映歷史,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文學比歷史還要真實。
深圳特區報:您的作品有很大一個特點:文學性和歷史性結合得很好,您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王笛:我始終認為,文史不分家。歷史寫作可以藉助文學的手法。除了討論、分析之外,寫歷史也可以用敘事、描述的手法。尤其是寫微觀史的時候,文學描述是完全可以利用和借鑑的。如果能夠充分運用多種表達手法,歷史表達就更有力。我的歷史寫作,就特別注重以敘事為主,把歷史觀和歷史認知,通過細節和故事表達出來。在《袍哥》這本書中,我就運用了大量的描述。比如說對川西平原的地理環境、田地、水牛、鴨子以及人們生活方式等細節的描述。當然,這些描述都是有根據的,不是我頭腦中的想象。
我想指出以下幾點:首先,歷史學家不應該放棄文學性的歷史寫作,如果歷史寫作變得越來越社會科學化,越來越遠離文學,便會逐漸失去廣大的讀者;其次,歷史研究和寫作,需要把焦點轉移到普通人、日常生活、日常文化上,歷史寫作是可以在文學上有所作為的,即回歸到文史不分家的傳統;最後,文學作品是可以用作歷史資料的,以文學證史不僅僅是新文化史的路徑,也是近代中國史學傳統的一部分。
只有傾聽普通人的聲音,才能寫出一個平衡的歷史
深圳特區報:最近一段時間,關於歷史研究「碎片化」的討論多了起來,不少學者開始擔心越來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沒有「歷史意義」的小問題上,注重細節,忽視整體。您如何看待?
王笛:其實任何歷史研究,都必須有局部和整體,或者說碎片與整體,兩者甚至不存在孰輕孰重的問題。沒有局部,哪有整體?沒有零件,哪有機器?當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學者批評「碎片化」的初衷,他們擔心我們的碩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學者迷失在細節之中,特別使他們詬病的是,這些年輕學者不能把小問題提高到解釋大問題或從更宏大的理論高度來進行分析。而我認為,批評「碎片化」的學者,對史學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滿足對「碎片」(局部)的認識,似乎任何研究課題,都要提供對國計民生等大問題的深刻認識,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義。
我認為,到目前為止,中國學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還遠遠不夠。以城市史的研究為例,我們在日本的大學圖書館裡,可以看到一排排書架上,疊放着一層層關於東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觀城市發展,小到社區街道、吃喝拉撒等等,我們就會深切感觸到我們對歷史的研究不是細了,而是太粗獷了。
深圳特區報:這些年來,您出版了多部地氣滿滿、膾炙人口的微觀歷史著作。是什麼原因讓您一直對微觀史保持着濃厚的研究旨趣,有沒有一以貫之的學術關懷?
王笛:如果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算起,我從事微觀史研究近30年了。我很早就意識到一個問題,即我們過去的歷史過分地把太多的研究精力放在大事件、帝王、精英身上了。而在歷史上占絕大多數的人民才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歷史上的「四大發明」,難道是統治階級創造的嗎?我們的各種文化,我們引以為驕傲的文明,都是人民群眾創造的。民眾才是歷史、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創造者,這種觀念,一直存在於我頭腦中。我研究歷史上的普通人,為民眾寫史,展現普通人的生活,靠的就是這種觀念的支撐。
我有一以貫之的學術關懷。從《街頭文化》一直到《茶館》,一以貫之的是日常史觀。這和英雄史觀或者說帝王史觀,是兩條不同的道路。這種史觀意味着讓普通人回歸到歷史研究的中心,一個普通人經歷,其實代表着千千萬萬的個人經歷。宏大敘事是需要的,研究普通人、日常生活也是需要的。歷史學家一定要眼光向下,充分重視民眾和日常。只有傾聽普通人的聲音,才能寫出一個平衡的歷史。我自己也要繼續努力。
學人簡介
王笛:1956年生於成都,1978年進入四川大學歷史系。1985年碩士畢業後留四川大學歷史系任教。1991年赴美留學,師從中國近代史名家羅威廉。1998年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美國得克薩斯農工大學歷史系教授,澳門大學傑出教授、歷史系主任,英文學術季刊《中國歷史前沿》(FHC)共同主編、中國留美歷史學會會長等。作品曾獲美國城市史研究學會最佳著作獎、首屆呂梁文學獎、中國會黨史研究會優秀學術著作獎等。現為澳門大學講席教授。
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研究。著有《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袍哥:1940年代川西鄉村的暴力與秩序》《跨出封閉的世界:長江上游區域社會研究(1644-1911)》《走進中國城市內部:從社會的最底層看歷史》《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記憶》《那間街角的茶鋪》《碌碌有為:微觀歷史視野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歷史的微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