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在朋友家的沙发上看剧,片头结束时幕布上出现五个字——《隐秘的角落》,我指着中间靠右的一团“草书签名”般的字迹问她:“那儿写的是什么?”她没有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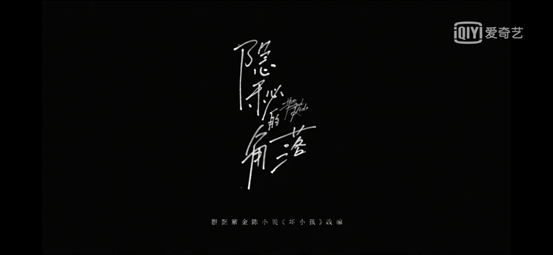
看完了全剧,我们仍然没看清那一团字是什么。直到科普帖告诉我,那是“the bad kids”。
“坏小孩”,作为原著名和整部剧的内核,就这样被藏在隐秘的角落,不愿被人看见。如果简单了解原著与改编剧的关系,就知道几乎所有的改动都是围绕“如何隐去青少年犯罪”而进行的。
不论是剧中家长对孩子变“坏”的态度,还是剧本本身的改编意图,都似乎在推动人们反思这样一些问题:孩子是否被允许有邪恶的念头?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必须是天真善良的?我们为什么不愿承认孩子邪恶的一面和变坏的可能?我们应该用什么方式对待这些有可能的“变质”?

01 得不到的与怕失去的
这部剧讲述了三个小孩因无法凭借自己的劳动力和社会身份筹到一笔救命钱,而不得不与杀人犯做金钱交易,继而一步步卷入深渊的故事。
从福利院里逃出来的小孩严良与普普,要筹30万给普普的弟弟治病。他们求助的第一个人是张叔——严良爸爸以前混社会时的故交。张叔听完严良的来意转身便报了警,警察要将他俩抓回福利院。
东躲西藏之后,他们来找严良的小学朋友朱朝阳。朱朝阳虽然好心收留了他们,但在筹钱上丝毫帮不上忙,还得跟他妈妈玩私藏小伙伴的游戏。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无意中用相机拍摄到了张东升杀人的画面,在救人要紧的亲情驱动下,他们接受了张东升的贿赂……
这种被动型“堕落”绝不限于青少年群体,它是整个下层社会的亚文化发展结果:无法通过客观努力而达到自己所期望的目标,但又无法忍受和妥善处理这些制约和挫折,最后铤而走险。虽然三个孩子身边有不少关心爱护他们的人:照顾朱朝阳生活的“唯成绩论”的妈妈,总想着要把严良送回福利院接受教育的警官老陈…爱他们的人,都是他们筹钱路上的绊脚石,只有杀人犯张东升,才是他们通向目标彼岸的唯一轮渡。

在这个以六峰山杀人的开场里,我们获得了两条岔开的线索,第一是张东升将如何伏法,第二是孩子们能否顺利拿到钱并且以观众希望的方式全身而退。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条线交织得越来越紧密,前者的结局变得越来越明确,而后者依然扑朔迷离。直到复制卡事件的爆发,我们才发现影片真正的焦点是孩子团内部的瓦解与背叛,以及内心的隐秘角落里住着张东升的朱朝阳。
张东升与朱朝阳一直被理解为一组互文:他们都酷爱白衬衫,迷恋笛卡尔,还有他们的名字“朝阳”“东升”。“隐秘的角落”明线是张东升的六连杀,暗线是朱朝阳的黑化与借刀。第一集里有这样一个场景:离异后很少关心前妻家庭的朱永平,临时起意给儿子朱朝阳买鞋。在疏远父子难得温情的时刻,现任妻子王瑶带着女儿朱晶晶强行加入,将父子局变为一场争宠局,并以父女间亲密的嬉闹宣告了最终的获胜方。随后影片立刻切入另一个场景:张东升参加妻子徐静表姐家孩子的满月酒,酒席上的对话第一次交代了少年宫代课数学老师张东升作为入赘女婿的社会地位与家庭地位的双重边缘化。
“你们有没有特别害怕失去的东西,有的时候为了这些东西,我们会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当张东升向孩子们解释自己的杀人行为时,镜头转向了朱朝阳那双深思与共鸣的眼睛。

02 为什么是朱朝阳?
朱朝阳生活在“牛奶与苍蝇”式的原生家庭里,剧中的一碗令人窒息的热牛奶和甜品上的一只死苍蝇隐喻了朱朝阳与父母的关系:前者是因为过度自我牺牲而要求孩子强制服从的爱,后者是廉价讨好与短暂温情下的怀疑与芥蒂。
朱朝阳的做法是:将牛奶一饮而尽;假装继续享用甜品。

孩子牺牲自己的感受去照顾父母的情绪,是一种父母和孩子角色的对调——这一过程被称为“亲职化”。亲职化的孩子可能有不同的性格,有服从型的、防御型的、进攻型的,也可能是混合型的。而他们的共性是虐待倾向。儿童不可避免地遭遇到成人世界的侵害,继而产生一套趋利避害的法则。朱朝阳的黑化是“亲职化”从服从型到进攻型的转变,也是由于外在刺激而内化出的一套应对残酷世界的机制。
当朱朝阳已经能笃定地看着父亲和警察的眼睛说谎,并即兴发表“演讲”让父亲忏悔得涕泗横流时,他的情绪管理和心态控制力已相当成熟,但他缺乏一套稳定的是非观来丈量行为的后果:他会因为害怕普普被带回福利院而包庇杀人犯;会因为生日后的友谊回温而答应加入他们勒索张东升;会因为朱晶晶情绪激动下喊出的“爸爸说只喜欢我,不喜欢你”而起杀心。从弗洛伊德提出“儿童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结”开始,人们虽不愿意却不得不审视人性里与生俱来的隐秘的角落。尤其当“好”“坏”本就是成人社会的运行法则时,青少年的判断和拿捏通常不太准。如果他们又面临家长和监护人动辄大呼小叫的谴责与惩罚,那么结果往往是:真实的邪恶在隐蔽的角落慢慢生长。
当严良对勒索张东升良心不安,打电话问老陈“敲诈勒索是不是很严重的罪”时,电话里老陈气急败坏地质问“你敲诈勒索谁了!你给我说清楚!”这本来是他们离悬崖勒马最近的一次,但老陈的处理方式切断了孩子团与“正常”社会联接的最后一根缰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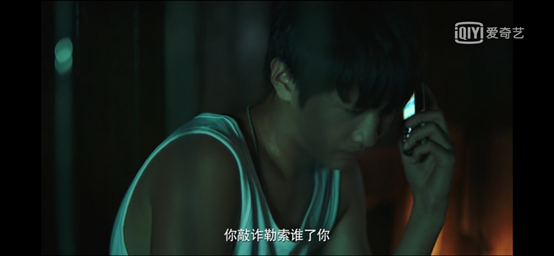
三个孩子中最不被允许“变坏”的,是朱朝阳:成绩全校第一,是母亲周春红心中唯一的骄傲,“优秀”也是他和朱晶晶抢父亲的唯一资本。 正因为连一杯热好的牛奶都不能不喝,朱朝阳的犯错空间很小。当他发现自己对妹妹见死不救的把柄握在普普手中,当严良最终决定告发张东升而自己根本摘不干净的时候,他选择了背叛——通过犯更大的错,隐藏更大秘密,让自己还是家长心中那个“好孩子”。这可能也是“唯成绩论”世界里,好学生的某种“精神洁癖”。
有人质疑说,为什么要写一本“孩子到底有坏”的书?为什么要看一部“孩子是怎么变坏”的剧?
“孩子都是天真无邪的”本就是成人对“性本善”执念的衍生品。 与其说作者和导演想要让人们看见“孩子到底能有多坏”,不如说,他们在提醒大众:少年与恶的距离可能更近,因为他们更接近人的原始本能,对于文明社会里的善恶是非,既不熟悉,也不熟练。
也许《小白船》还是孩子们心中的童谣,却已是成人眼中的阴间歌曲。
03 献给童年
全剧结束后有一段片尾,上面写着“献给童年”。我和朋友惊呼:“天哪,谁想要这样的童年,别献给我。”
近几年“青少年犯罪”题材的影片越来越多,从《过青春》到《少年的你》,再到《隐秘的角落》。
一方面,全球的青少年犯罪数据都在持续攀升,一份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青少年犯罪总数已经占到了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另一方面,“青少年犯罪”作为不太愿意被人们提起和承认的隐秘角落,终于逐步开始获得社会的关注。
童年中的许多记忆是被修正和美化过的。当我成人之后,回顾某些孩童时代经历,发现其实危险离我很近,“变坏”也距我不远。那些近几年才频繁登报的“性侵”、“霸凌”事件,并不是新生物种,在媒体不发达的年代,已在隐秘的角落肆意生长了好多年。而彼时的家长,似乎也缺乏处理“青少年的恶”的意识和能力。就像朱永平对朱晶晶的毫无管教;周春红对朱朝阳的在校人际关系和被霸凌经历毫不在意。
童年不一定比我们以为的更黑暗,但一定比我们以为的更复杂。
当张东升和朱朝阳隔着屏幕不断问观众“是相信童话还是相信现实时”,我们都知道,“坏孩子”不相信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