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
成立经济特区40年来,深圳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一成功效应,不仅是中国意义上的,也是世界意义上的。由美国学者马立安等撰写、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作序的《向深圳学习》在美国和中国的出版,就是深圳成功故事引起全球瞩目的一个最新例证。

美国作者马立安。
在叙述深圳的成功故事时,人们往往因袭一个「从无(零)到有」的基本模式,比如广为流传的「小渔村」隐喻就是。自然,作为一个新事物,经济特区对於中国的制度创新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但就其成立逻辑来看,它其实与新中国建制以来的政治体制传统和施政过程及特点紧密相关。换言之,「深圳」并不完全是「从无(零)到有」或无中生有的。这可从如下有内在一致性的两个方面来把握:一是中央与地方的关係,中央通过对地方放权来推动发展,二是通过地方试验、树立典範的适应性治理。就前者来说,正如美国学者谢淑丽在《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一书中所指出的,中国改革之所以可以走出一条不同的成功道路,原因就在於邓小平改革实际是在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地方分权化」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中国1978年後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邓小平的整个改革继承了这一政治逻辑并从中获益,如首先在广东和福建建立「经济特区」,以及1992年的著名「南方考察」,都与毛泽东依靠地方、发动地方的做法如出一辙。而本书也明确指出,「深圳作为经济特区的一个特点是,自上而下的有计划发展和自下而上的没有计划的发展齐头并进」。就後者而言,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治国理政的一个典型做法是通过树立模範来推广各项相关政策。而在新时期,呈献在世人面前的典範,就是作为改革试验田的深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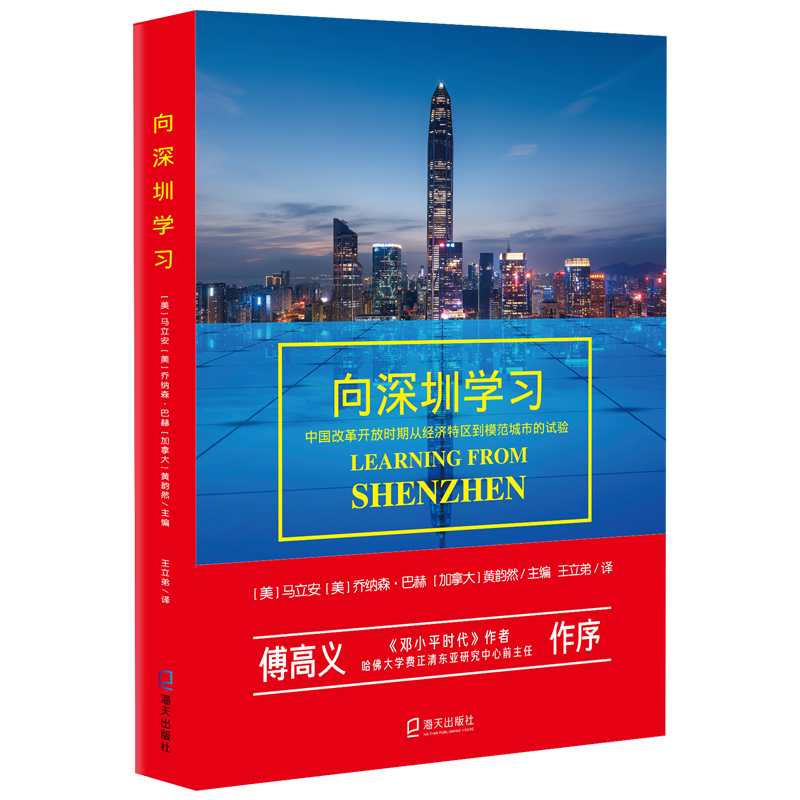
一方面,《向深圳学习》从政治经济学的宏观视角描述深圳模式的形成、成就和问题,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何将「深圳经济特区」发展成为「深圳样板」,也即深圳从一个不循规蹈矩的特例演变成人人效仿的「模範」城市,成为官方规划和政策指引下成功发展的範例,从而被纳入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国家叙事中来。但另一方面,与一般的对於深圳发展成就的主流叙述又有很大不同,《向深圳学习》的写作毋宁说是基於一种相当自觉的民间学术立场:「我们的调查研究既不侧重国家制定的方针政策,也不侧重全球经济的市场力量……我们的研究将把那些常见的深圳发展史叙事中未提及的众多参与者和团体呈现出来。」
「另外一些人和一些其他要素」包括土地和户籍制度改革、流动人口和边境管理等,它们既使「时间」获得了空前加速,也使「空间」发生巨大变迁。「地理空间」在此得到了高强度的重视和关注,比如香港、二线关、城中村等,它们构成了解析中国适应性治理密码的钥匙:因为「当年把改革开放作为一种试验,没人预先知道答案」,在作者们看来,深圳经济特区的「不期然的发展渊源」是重要的,「这一发展历程并非总是沿着从规划到政策形成再到政策实施这样一个线性序列展开」,而其典型徵候,是「城中村」。
作为当代中国农村与城市混杂共生的经典範例,在「城市包围乡村」中形成的深圳「城中村」,既具有乡镇的自主特权(如举办村办企业参与全球化产业链生产),又具有城市发展的活力(如为接近一半城市人口提供廉价住房),可以说是特区中的特区。作为深圳城市化发展支点的城中村,它既折射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变化的複杂历程,也展现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难题:在农村土地出让政策制定、城市扩容以及把农村当做城市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城中村的「重新发现」和重新改造方面,乡村与城市表现出不同的诉求与反响。
深圳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是一个複杂的过程,如该书所述,假如「北京」代表国家权力,「香港」代表境外资本和自由经济,「宝安」代表特区成立之前的本地居民和农村集体经济制度,那么在破除宝安旧的体制、规划深圳的发展以及应对世界体系的变化等方面,深圳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依赖於创造性地使不相容的社会、经济和司法制度相互结合,从而成为中国适应性治理的城市典範。
傅高义曾说,在深圳身上,蕴藏并见证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诸多可能性。《向深圳学习》一书,对此无疑都有着最为鲜活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