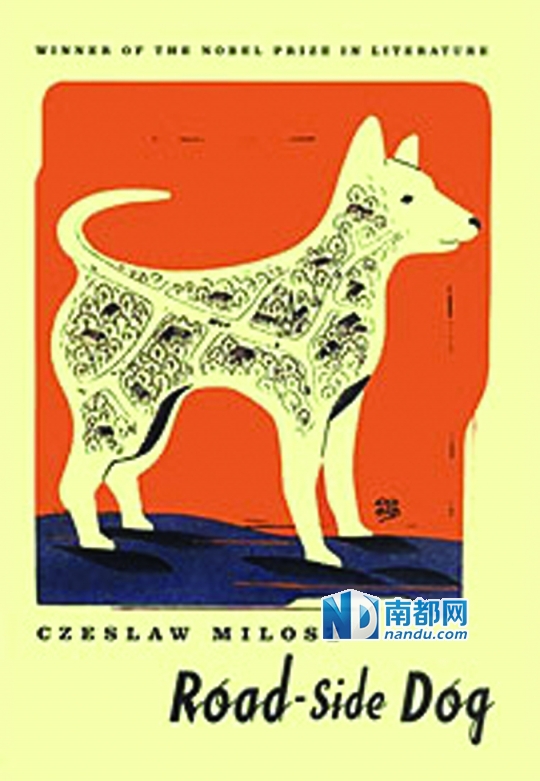
米沃什《路边犬》,罗伯特·哈斯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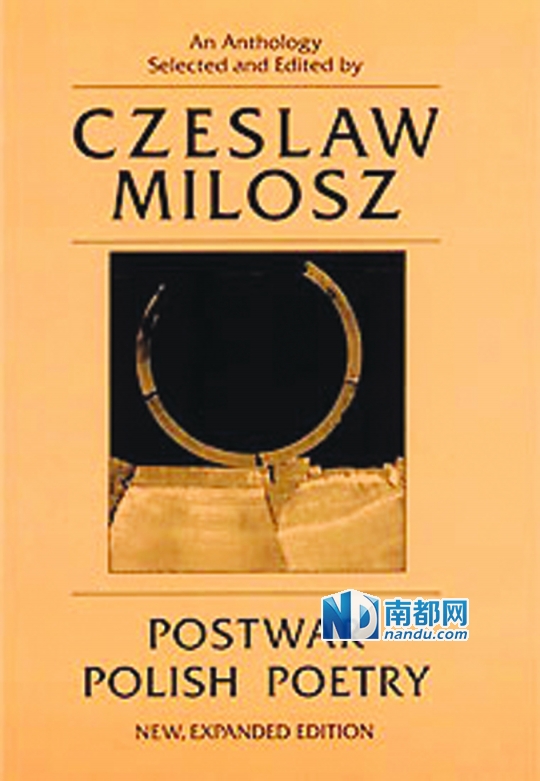
《波兰战后诗选》,米沃什译。

辛波丝卡《万物静默如谜》,陈黎、张芬龄译。

聂鲁达《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陈黎译。

保罗·策兰《心的岁月》,王家新译。

茨维塔耶娃《新年问候》,王家新译。



诗人译诗:抓住文字飞舞的蝶翼
8月,在上海书展“国际文学周”上,来自美国的桂冠诗人罗伯特·哈斯、来自宝岛台湾的陈黎和内地诗人王家新聚在了一起。这三位来自不同地域的诗人,另一共同的身份是诗歌译者。罗伯特·哈斯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的英文译者,长达二十余年与米沃什共同合作翻译英译本《米沃什诗选》,其译本因米沃什自身的深度参与成为经典文本;陈黎在台湾翻译辛波丝卡及聂鲁达等诗人的诗作,其中他翻译的辛波丝卡的诗选《万物沉默如谜》一反诗歌的冷门,成为畅销榜上的“文化英雄”;王家新自早年翻译叶芝诗选以来,集中心力深垦保罗·策兰、茨维塔耶娃等“诗人中的诗人”。
“诗人译诗”这一世界诗歌史上的隐秘传统,如何在不同的个案中碰撞出火花,当译诗的诗人们聚在一起,又如何“华山论剑”?
桂冠诗人哈斯
通过翻译来听听别国的声音
这是美国诗人罗伯特·哈斯第二次来中国。和南都记者六年前见到的哈斯相比,老诗人的头发更白了一些,但温和友善依旧。不同的是,此次中国之行,哈斯开心地见到了自己诗歌新出炉的中文译本。
这个秋天,哈斯硕果累累,从上海回去后,他将领取美国重要诗歌奖项“斯蒂文森诗歌奖”。以美国诗歌史上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华莱士·史蒂文森命名的这一奖项,1994年由美国诗人学会设立,旨在表彰“在诗歌艺术有突出及公认成就的美国诗人”,每年评选一次,奖金为10万美元。W .S.默温、约翰·阿什贝利、菲利普·莱文、加里·斯奈德等美国当代诗坛的健将都是这一奖项的往届得主。美国媒体评论说,“当绝大多数诗人都籍籍无名的时候,哈斯是一位文学明星。”
除去1995年-1997年两任全美桂冠诗人的身份外,哈斯是包括全美图书奖、普利策奖在内的诸多奖项的得主。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文学教授的教职上退休,但身体力行环保等公益事业。此外,哈斯也是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诗人米沃什的重要英文译者。两位诗人轨迹的交集是“诗人译诗”传统的绝佳注释。
1960年,米沃什来到美国。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伯克利分校,教授斯拉夫语言文学。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的斯拉夫语系都是只有俄语专业,伯克利分校是其中少有的开设波兰语和捷克语专业的。“在波兰期间,米沃什曾在电台做过记者;二战后,他当过波兰驻美国及法国使馆的文化参赞。1960年移居美国之前,他在法国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寻求政治避难。所以初到美国那几年,他的妻子和孩子都还在法国。”
60年代末,美国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平权运动、女性主义运动、反越战风起云涌。当时的伯克利,一度是美国学生运动的震中之一,垮掉派、鲍勃·迪伦、滚石乐队、披头士风靡。米沃什当时也在这震中,“在这里他也写诗,这些都构成有意思的背景。而我呢,22岁结婚,23岁有了孩子,当时正在自学写诗,以及奋力谋生。”
哈斯和米沃什的相遇一直到70年代末。同在伯克利教书,哈斯有一天发现这位波兰诗人的住所只离他三个街区之距,哈斯回忆,“我先前读到过米沃什的诗歌,十分喜欢,我知道他在伯克利,但我不知道他和我是邻居!”那时,米沃什只有很少的一些诗歌被译成了英语,在一个很小的出版社出版,不为人知。哈斯打电话给他的出版社编辑,告诉他有一个伟大诗人的作品需要翻译出版,“编辑和米沃什见了面,他答应了翻译出版。”
哈斯回忆,那之后不久,米沃什受邀参加旧金山一个国际文学节,朗诵自己的作品,“他告诉我他很为朗诵而紧张,因为他的口音。他问我可不可以替他朗诵,我答应他,当然可以,我很荣幸。他到我家里来,给我看他准备朗诵的诗。他问我:你怎么看波兰的诗?我不懂波兰语,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他又问我,那你怎么看我的诗歌的翻译?我大概说了‘你的思想很有意思’诸如此类的,他很直率地告诉我:你的想法不够好。”回忆起与这位旧友的往事,哈斯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米沃什问我,B ob,你帮我翻译怎么样?那是1977年,就这样,我们翻译了20年。”
多年来,每周一次,或早晨或傍晚,与米沃什的会面几乎成为哈斯日常生活铁打不变的一部分。后来,哈斯在斯坦福的大学同学、同为诗人的罗伯特·品斯基也加入了进来。“我不懂波兰语,所以通常,米沃什会写下他的第一遍翻译然后读给我听,再由我们进行第二遍、第三遍的翻译。”这种译者彼此都是诗人的翻译是难能可贵的,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是由作者和译者通力合作完成的翻译。
哈斯告诉南都记者,其实米沃什自己也翻译诗歌。1945年米沃什在克拉科夫曾编过英美诗选,之后也翻译过美国诗歌,“1944年他翻译过艾略特的《荒原》,他也将很多波兰诗人的诗翻译成英语。”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米沃什教一个诗歌翻译的研究班,他带着学生们集体翻译,把波兰语诗歌翻译成英语,后来编成了一本《波兰战后诗选》。
“如果一直呆在法国,我就不会在1978年获得斯塔特奖,或者后来的诺贝尔奖。”米沃什曾经这样表示,他说,在西欧已经萎缩到像银币收藏一样的诗歌,在美国的大学校园里找到了听众,找到了整个的系、学院和各种奖项。
哈斯和米沃什的最后一次合作是1998年出版的一部名为《路边犬》(R oad-Side D og,戴骢曾节选该书翻译成中文,将之译为《途中狗友》)的散文集。这部由格言、轶闻、沉思、评论构成的散文集,在哈斯看来,是米沃什对自己一生的感受。“其实米沃什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波兰之外,童年在俄罗斯,后来在法国,再后来在美国。但他一生都用波兰语写作。他说,他带着他的母语在世界各地流徙。”哈斯说。
“我花了20年时间翻译米沃什,从波兰语翻译成英语。整个20世纪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体现在他的诗歌当中,他看到了20世纪那些最糟糕的恐怖。”哈斯说,米沃什伟大的主题之一是政治,政治诗几乎一无是处,但是你不得不面对的是我们身处其间的政治。哈斯在诗中写大自然摄人心魄的力量,写泰国街头的雏妓与全球化,也写伊拉克战争。
诗歌如何产生影响?哈斯说有一个例子是,梭罗读华兹华斯,约翰·缪尔(英裔美国博物学家,提议成立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读梭罗,罗斯福读缪尔,所以我们有了国家公园。“成就这件事花了一个世纪的时间。”
哈斯说,在美国,桂冠诗人的角色相当于诗歌对大众的发言人。“我们有一个周报,我在上面谈诗歌的翻译,也写了许多文章,就是向公众传达这样一个观念:环保主义者他们说,某一种鱼、某一种鸟的生存情况会告诉你这生态圈是不是安全,它们就像指标一样。如果北美黄喉夜莺每个春天还出现,那么我们知道生态系统还健康。诗歌也是这样的一个指标。”如果有一个自由创造的环境,如果整个教育系统非常健康,那么诗歌的整个状况也会越来越好。“如果公民识字率不断下降,诗歌又怎么会有更多的读者呢?”
让哈斯忧心忡忡的是,在美国,尽管有许多的移民,但却越来越是一个单语言的国家,“你去看电视,所有都单一版本的美国想法、美国语言。我这样来说是不是太夸张了,一点都不夸张。美国是一个很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无知非常危险。”
“我们这一代作家成长于平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实际上,朝鲜战争是我们苏醒的开始。”回顾六十年代对自己的影响,哈斯说来自异域的文化影响很大。“那时候我们读庞德翻译的李白,还有加里·斯奈德翻译的中国诗歌———他当时在加州大学研究生,这些都形成我阅读的基础。我们在李白、杜甫、王维的世界中看到了如此不同的风景。”开始写诗之后,哈斯觉得翻译就成了诗人很正常的工作。他甚至自学日语翻译了日本的俳句。
哈斯已经退休了,但他每年在伯克利还会做一个关于诗歌翻译的工作坊,每个班带12个学生。“我不教学生们如何读诗,也不教如何写诗,在我看来,只要花精力,这些总是能弄懂的,但是我教翻译。”这个翻译课是世界文学的课堂,会有美国诗歌、英国诗歌、日本诗歌,也有中国诗歌,有古典诗人的作品,也有当代的诗歌。“通常的方式是,学生会逐字逐字地翻译,然后读给其他人听,直到用英语表达出来像一首诗。”在哈斯看来,年青一代的美国人通过翻译来听听别国的声音,这很重要。
辛波丝卡译者陈黎
用诗去青睐诗,去致敬,再创造
“我从小就出生居住在台湾花莲的上海街,我很高兴从花莲的上海街来到上海街上。”上海国际文学周上,陈黎用一个绕口的语言游戏带出两岸历史幽微。1954年出生的陈黎,说自己除了在台湾师大读书的四年服兵役的两年外,都生活在太平洋畔的花莲,因此他的其中一本诗集也被命名为《岛屿边缘》。在岛屿边缘足不出户用功的成果,是高产的诗歌翻译。除了辛波丝卡的诗,陈黎和他的太太张芬龄,还翻译了600多页的《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及聂鲁达、普拉斯等诗人的作品。
纯文学诗集能卖成畅销书,陈黎翻译的波兰诗人辛波丝卡诗选《万物沉默如谜》大概是少见的案例。说起来是隐秘而有趣的关联。陈黎最早见到辛波丝卡的诗,正是在米沃什和学生集体英译的《波兰战后诗选》中。
陈黎说,翻译辛波丝卡很偶然。“开始读辛波丝卡的时候,没有几个人认识她,读到她的诗很好,就开始译。”我买的第一本辛波丝卡诗选是1981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声音,情感,思想》———有她70首诗作英译,并附波兰原文。
1998年,陈黎翻译的桂冠版《辛波丝卡诗选》在台湾卖出1万多本,成为畅销书榜上像米兰·昆德拉和村上春树一样的“文化英雄”。这本诗集一开始并没那么热,后来幾米绘本《向左走向右走》中引用了辛波丝卡《一见钟情》一诗中的前四行作为前言,这本诗选也开始慢慢流行起来。《在一颗小星星底下》甚至出现流行歌手的歌词里。在大陆出版的《万物沉默如谜》也同样畅销。陈黎调侃,“因为这书卖得好,很多出版社都去出版诗集,害了不少人。”
“其实人家本身的好处不是因为我们的翻译来的,我们只是推手。”陈黎说,就畅销而言,辛波丝卡是波兰的“席慕蓉”,“老早在30年前,她的诗集《巨大的数目》,第一刷1万本在波兰一个礼拜就卖光,书店大排长龙,那时候她还没得诺贝尔文学奖。这种东西还需要我们做广告吗?”实至名归,她的东西你就是一读就会觉得好。“她的诗举重如轻,严肃的主题常常用幽默、机智的方式手到擒来,日常生活的卑微事物中充满别人未及的创意。”陈黎说,“诗是一个防火墙,辛波丝卡说的,诗是我们的栏杆,幸好有这个栏杆,让我们可以保住命,诗让我安定,让我们勇敢,不难过,它告诉我们每一个小的东西都是动人的、高贵的。”
陈黎大概是中文世界最早翻译米沃什的译者之一。米沃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1980年,陈黎25岁,“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一年我得到了时报文学首奖,时报社庆是10月2日,报纸登了整个版。过几天,他们打电话给我说,诺奖揭晓,得奖者是米沃什,然后全世界都往伯克利大学找米沃什,高信疆、痖弦他们打电话给所有人,问这个人是谁,没有人认识他。后来有人说给陈黎打电话,陈黎翻译过,总编辑给我打电话。”回忆起那个没有传真机和E - m ail的年代,陈黎说,诺奖出消息的当天晚上,陈黎一个字一个字念米沃什的诗,总编辑高信疆在电话旁边写,报纸已经截稿,高信疆让人用毛笔写出来“献词”,作为副刊的独家头条。“这是中文第一人吧!”说起当年的“先见”,陈黎不禁小小得意。
陈黎毕业于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老师余光中翻译的一本《英美现代诗选》是老一代诗人的译诗典范。翻译《拉丁美洲现代诗选》既是效法,又是新一代译者的独辟蹊径。“那时候我和张芬龄对拉丁美洲文学产生兴趣,是因为修第二外国语时选了西班牙语,而选西班牙语,则因为选课当天我们都较晚到校,法语、德语皆已额满,只能选西班牙语。当时我们西班牙语虽学得不怎么样,但觉得西班牙语一堆aaoo,念起来甚为好听,所以很想找西班牙语诗来念。买到的书既多是西英对照,理解起来似乎也不算太难。”一边服兵役,一边在笔记簿上翻译,加上当时女友张芬龄的配合,《拉丁美洲现代诗选》很快就初具规模。拉美众诗人中,聂鲁达是陈黎着力甚深的一位。“我说我受聂鲁达影响,我不知道我是受聂鲁达影响,还是说我翻译聂鲁达的影响。”
诗人译诗是个普遍的现象。陈黎说,大诗人如布罗茨基、希尼等,彼此互相濡慕,会去读对方的诗,或者写诗献给谁,“有点像中国的酬答诗。有时候过几年发现他们酬答的人也得诺奖了。”陈黎觉得,诗人和小说家好像不太一样,诗人像一个大家庭,“是不是得诺奖或者推荐他不重要,我觉得他们对同行的珍惜是真的。我觉得很奇怪,有时候两个人没有见过面,但是会去读对方的诗。”
这次到上海,陈黎提前读了哈斯和哈斯的太太、同为著名诗人的布伦达·希尔曼的诗,忍不住翻译了几首。甚至在台上开会,其他嘉宾发言的期间,也看到他拿出笔,不时在译稿上圈圈点点。
陈黎承认,看到一首好诗,确实会无法自己地要去翻译。不一定非得是大师,有时候作品不错,就会有冲动。“你看到两句就会觉得,哇,她是比我更好的诗人,什么是更好的诗人?就是说你一次写两个,她一次能写五个,而且写出来更微妙。你嫉妒她写这个东西能这样写。”比如,布伦达·希尔曼的诗中有一个比喻,形容一只麻雀“它的胸轻如一盎司的茶”,陈黎击节赞赏,“我这辈子不会用这样的比喻,我输给人家了。”好的诗歌的特质和技艺,好像通过翻译能够据为己有,想要去读它,转化它的优点,或者说用诗去青睐诗,用诗去致敬,用诗去再创造,陈黎觉得这是诗人家族最特别的一点。
“翻译是辛苦的甜蜜”,陈黎把翻译比作捕蝶,“企图为读者抓住飞舞的蝴蝶,好让其一窥全貌。然而当他钉死蝴蝶时,他呈现出来的只是僵硬的标本,而非真正的蝴蝶。如何钉住文字蝴蝶的双翼并且让其仍保有生命,是翻译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及努力的方向。”
诗人王家新
诗人作为译者成为一种“现代传统”
“我不是翻译家,我是爱好者。”在与哈斯、陈黎对谈的活动中,王家新一上来就这样声明,“我的翻译首先出于一种爱,还有一种内在的需要,像呼吸一样迫切的需要。”
在内地诗坛,诗人译诗在中坚代诗人身上并不少见,黄灿然、张曙光、周伟驰、胡续冬等诗人都有杰出的译笔,王家新是其中用力甚深、心得独到的一位。就他深垦的德语诗人策兰而言,王家新迄今已翻译了策兰的三百多首诗和多篇散文,写过数十篇关于策兰的文章和解读文字,还有一部评传正在写作之中。用王家新的话说,“策兰是一位需要用我的一生来阅读和翻译的诗人。”
王家新最初翻译策兰是在1991年的秋冬。从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图书馆,他借到一本企鹅版策兰诗选,英译者为英籍德裔诗人、翻译家米歇尔·汉伯格。“这是我与策兰的第一次真正的相遇,我完全被他的诗和命运吸引住了。”那时在中国大陆,策兰的诗只有少许三四首被译成中文;在诗歌界和翻译界,策兰也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最初并没有翻译的想法,但我很快意识到我必须去译,只有这样我才能切身进入到策兰的语言的血肉之中。”王家新从中译了二三十首策兰的诗,并请社科院外文所冯至先生带的德语文学博士、研究里尔克的学者李永平指正,“他看后这样带话来:‘我没想到策兰居然可以翻译成中文,而且译得是这样好!’这样的肯定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王家新将策兰的诗比喻为“从黑暗中递过来的灯”,循着这样的灯光,对策兰的翻译日具规模,研读也日渐切中肯綮。
王家新说,其实策兰本身就是一位做出过大贡献的天才翻译家,“策兰翻译的曼德尔施塔姆,是他诗人生涯中光辉的一笔。职业翻译家什么都可以翻译,但诗人译者都是有选择的,而他们的选择深究起来,往往都出自一种‘生命的辨认’———策兰为什么会译艾米丽·狄金森?这就像有人所说,因为‘狄金森是照耀他启程的星,而非猎取的目标’。”
王家新翻译茨维塔耶娃也是出于这样的“同气相求”。他还记得自己二十年前在泰晤士河桥头的路灯下,初读茨维塔耶娃《约会》一诗英译本时的情景,“那个开头,使我骤然一哆嗦:‘我将迟到,为我们已约好的相会;当我到达,我的头发将会变灰……’,最后的结尾甚至令我有点不敢往下看:‘在天空之上是我的葬礼!’———我读着,我经受着读诗多年还从未经受过的颤栗。”
王家新最新出版的《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包括了六十多首抒情诗、诗组以及《终结之诗》、《捕鼠者》、《房间的尝试》、《新年问候》等长诗。“说实话,这是我遇上的最艰巨、最具难度、最富有挑战性的作品之一。”王家新说,这首长诗是1927年茨维塔耶娃写给里尔克的挽歌,诗人前后用了两个月时间写就,长达200多行,句式复杂,多种层次扭结在一起,而又充满了互文回响。“在翻译过程中备受折磨,但又充满感激,因为伟大作品是对我们的提升。”
“茨维塔耶娃的英译者科斯曼希望她的翻译‘至少能够带来一些活生生的血肉,一些火焰。’她说的是‘至少’,这是有技艺的译者可以做到的。困难就在于把握茨维塔耶娃的抒情音质,并使一本诗选从头到尾下来都能确保其‘声音的真实性’。”
“我的翻译只能是‘作为一种敬礼’,献给我心中永远的玛丽娜,也献给那些爱着这位伟大诗人的中国读者。”王家新在序中写道:“我并非一个职业翻译家,我只是试着去读她,与她对话,如果说有时我冒胆在汉语中‘替她写诗’,也是为了表达我的忠实和爱。”
在王家新看来,翻译既是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搏斗,也是两个诗人之间的搏斗,不可避免地会打上译者自身的印记。“但是这要有分寸感。我研究过布罗茨基对曼德尔斯塔姆的名诗《哀歌》的翻译,布罗茨基是一位布鲁姆所说的‘强力诗人’,他的译文音调更宏亮,诗意的表达更强烈,更有个性的锋芒,但他也多少把曼德尔斯塔姆‘布罗茨基化’了。”王家新的观点是,所谓“客观、忠实”的翻译从来就不存在,译者当然要有个性,但也要有一种“化身万物”的能力。“最起码,在翻译时要充分了解、掌握和尊重原作的风格,比如说,你不能用茨维塔耶娃的风格来翻译阿赫玛托娃。”
就“忠实”这一翻译的重要命题而言,王家新认为,有表面亦步亦趋的忠实,也有通过背叛达到的忠实,还有一种更高的忠实:那是伟大的翻译所达到的境界。“伟大的翻译比伟大的文学更为少见,伟大的翻译本身就是伟大的文学。”
“博尔赫斯在谈论英国诗人菲茨杰拉尔德对《鲁拜集》的翻译时曾这样感叹:‘一切合作都带有神秘性。英国人和波斯人的合作更加如此,因为两人截然不同,如生在同一个时代也许会视同陌路,但是死亡、变迁和时间促使一个了解另一个,使两人合成一个诗人’。”在王家新看来,诗的翻译不同于一般的翻译,它在根本上,正是博尔赫斯所说的为了使“两人合成一个诗人”。
“这当然是一个极其困难和艰巨的过程。然而,就中国现代诗歌而言,戴望舒之于洛尔迦、卞之琳之于瓦雷里、冯至之于里尔克、穆旦之于奥登,等等,已为我们提供了这一相互‘契合’的光辉例证。”王家新说,正是由于他们,“诗人作为译者”成为一种“现代传统”,这一传统对后来的诗人产生了重要的启示和激励作用。“我们在今天接过这一传统,也就是对这些前辈的一种回报和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