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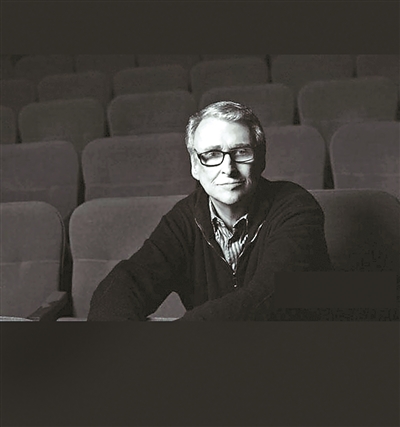

电影《毕业生》摘得第4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奖
他是斯皮尔伯格心目中的缪斯和领路者。
他是爱因斯坦的远房表亲。
他是迄今为止唯一囊括奥斯卡奖、艾美奖、格莱美奖和托尼奖的美国导演。
他是妻子眼中那个地球表面最有趣的男人。
他是用舞台的绚烂来遮蔽生命中的晦暗的艺术家。
他是从四岁开始就不得不戴上假发的麦克·尼克尔斯。
2014年11月19日,83岁的他离我们而去,留下一片“寂静之声”,天涯咫尺,仿佛又听到那个熟悉的旋律,有人轻诉如歌——“你好,我的朋友……”
关于尼克尔斯
麦克·尼克尔斯,1931年11月6日出生于德国柏林,7岁时随家人躲避纳粹来到美国。自从1955年加入芝加哥著名喜剧团“第二城”前身,尼克尔斯在近60年的职业生涯中成绩斐然。1968年,他凭借电影《毕业生》摘得第40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此外《灵欲春宵》(获13项奥斯卡提名)、《丝克伍事件》(获5项奥斯卡提名)、《打工女郎》(获6项奥斯卡提名)等银幕以及《深知我心》、《天使在美国》等荧屏作品同样是令人耳熟能详的经典代表作。
2001年,70岁的尼科尔斯凭借美剧《深知我心》摘得当年艾美奖最佳迷你剧导演殊荣,由此成为史上第九位囊括奥斯卡、艾美奖、格莱美奖以及托尼奖的娱乐人物,完成美国娱乐界“EGOT大满贯”(这四个奖项涵盖了电影、电视、音乐和戏剧四大娱乐领域,取各自首字母由此得名),并且是迄今12位大满贯得主中唯一的一位导演。
2007年,尼克尔斯执导了其最后一部电影作品《查理·威尔逊的战争》,影片汇聚了两位奥斯卡影帝汤姆·汉克斯和已故的菲利普·塞默·霍夫曼、以及奥斯卡影后朱莉娅·罗伯茨等实力派阵容,最终该片获得了五项金球奖提名以及当年奥斯卡最佳男配角的提名。2010年,美国电影协会授予尼克尔斯终生成就奖。
丹尼尔斯在《毕业生》中扮演霍夫曼的父亲,他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寂静之声》时的情景,“歌声响起,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说,等等,这歌声把我的镜头的整个意念改变啦,那一刻我才忽然意识到,我正在完成一部不寻常的电影。”
《毕业生》无疑是美国电影的一个高峰,它当年总共获得七项奥斯卡奖提名,尼克最终凭此片荣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在2007年美国电影学会评出的百年百部经典影片中,《毕业生》位列第17位。
但是,《毕业生》的拍摄却是一路艰难。
首先,由于尼克此前只是作为百老汇的戏剧导演为人所知,而在好莱坞还闻者寥寥,最初启用他的制片人很长时间里都因此找不到愿意投资此片的人,只好作罢。几经周折,终于有人愿意接手了,缘由也是蛮偶然的,因为此人意外地了解到拍摄《灵欲春宵》时,伊丽莎白·泰勒是特别推荐了尼克来执导的。
接下来,尼克的举动却让投资人发慌了,因为尼克尔斯找来巴克·亨利做编剧,而巴克·亨利此前只搞过即兴话剧,根本没有写作的背景。亨利还记得当时尼克尔斯这样对他说,“我知道你有能力做,我也知道你适合做。”
更令制片方头疼的是,他没有接受大家的建议请来罗伯特·雷德福做主演,而是把头等角色给了一个当时还从没演过电影的人——达斯汀·霍夫曼。多年以后达斯汀·霍夫曼回忆说,“我不敢想象在当时的情形下还会有别的导演像他一样选择我出演那样的角色,那需要惊人的勇气。”
就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新晋导演却从此改变了好莱坞的惯常艺术品质,掌镜《毕业生》的是曾拍摄过《宾虚》的著名摄影师罗伯特·苏蒂斯,他后来曾如是说,“这部电影要的每个东西都需要我积30年的经验才能胜任,他要求我在一个镜头里实现的东西比我此前做过的一部电影还要多。”
说到《毕业生》,另一个无法忽略的名字就是保罗·西蒙,他和加芬凯尔的民谣组合当时也刚刚崭露头角,尼克独具慧眼请他们演唱电影主题曲,丹尼尔斯在影片中扮演霍夫曼的父亲,他还记得第一次听到《寂静之声》时的情景,“歌声响起,我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说,等等,这歌声把我的镜头的整个意念改变啦,那一刻我才忽然意识到,我正在完成一部不寻常的电影。”《毕业生》影响了众多人,斯皮尔伯格也是其中的一员,他把《毕业生》描述成一种无法躲避的“生命的变更”,他特别指出,“麦克拥有凌厉的目光和不可思议的听力,正是它们让他有可能掌控着电影中的场景真实又充满反讽。”
在尼克尔斯看来,甜蜜婚姻的最大奥秘就是——别吝啬你的赞美,同时要让对赞美的回应如一见钟情时般的电光火石。
至少从表面上看,尼克尔斯的最后一段婚姻像极了30年代浪漫戏的翻版:温文尔雅的导演,在人生的某个低点,遇到了年轻又热情的女记者,于是火光迸现。
不同的是,场景换到了80年代中,并且一切都是真的。
此时的麦克·尼克尔斯已是百老汇和好莱坞的名流了,54岁,戴安·索耶40岁,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出镜记者,按照尼克尔斯的说法,他们突然爱上彼此的地点是在协和式飞机上,而随后的恋爱也自然调整成超音速的节奏了。
实际情况是,传说中的一见钟情在登机前就发生了。
当时,他们恰巧都准备从巴黎返回美国,大步走进机场休息室的麦克意外撞到了镜头前仪态万方的知名女主播的很少示人的一面,“她正躲在一角补妆、打理还没有弄好的头发,我认出了她并同她说了第一句话,‘你是我的英雄’,她也认出了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你是我的英雄,我的英雄,你吃过午饭了么?’”麦克生前曾这样回忆他们的初见,“她说要为《60分钟》节目采访我,我假装对上《60分钟》很有兴趣,这样,我们有机会先后一起吃了14顿午饭。”
“他说话前我就知道,甚至在他走进屋子前我就知道,我知道有事要发生,很可能还很美妙。”去年索耶在《芭莎》杂志上这样追述道,“但是,我更知道,我的生活要从此变样子了。”
此前的尼克尔斯有过三段婚姻,“我爱过去的女人,但那无法同这一次相提并论。”
梅特尔·斯特里普是尼克尔斯的电影老搭档,说起麦克与索耶的这次相遇带来的变化,这位影坛巨星语多钦羡,“他那时真的像撞到了墙,几乎崩溃了,然后就遇到了索耶,一切都改变了。以前,他总是屋子里最聪明最有才华的人,当然,也可能是最差劲的那一个,可现在,早先的那些聪明不过成了他智慧兵工厂的一枚小箭头了。”
茱莉亚·罗伯茨亦是麦克的好友,“他全然地不可思议地爱着戴安,像中了魔法。”对此尼克尔斯的解释是,“真爱让匹诺曹变回成真正的小男孩,奇迹就这么发生了,因为她爱我并能接受关于我的全部,我想不出还有谁可以做到这样。”
1988年4月29日,尼克尔斯与索耶在马萨诸塞州的葡萄园岛举行了婚礼,随后成为纽约又一对声名显赫的明星夫妇,与此同时他们都给予了彼此更多的私人空间,在今年二月的一次访谈中,索耶透露,自己的丈夫到目前为止都还不知道也没问起过她的政治观点。她还特别提到,“尼克比我更浪漫,我总会在放袜子的抽屉里读到他写给我的字句,或者在出差时从行李箱中找到他提前藏好的纸条。”
不过,在索耶的眼中,最浪漫的是,每一次在一起时,总是他先伸出手握住自己的手,“我们很少争执,我记得有一次因为什么事难得吵起来了,他忽然半截停了下来兴奋地对我说,‘天哪,吵架这么有趣!’”。
而在尼克眼中,印象深刻的竟是妻子的不拘小节,“她早晨起来习惯到户外转上五分钟,期间常被人看到穿的是我的夹克。”
他曾回忆说,两人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刻是一起驾车横穿美国,“我们不断地从一个烧烤摊奔赴另一个烧烤摊,还有比这更幸福的事吗。”
当看到电视上的女主播总在自家庭院为大家倒上冰红茶时,周围的邻居都觉得不可思议,而此时的尼克则甘之若饴,他会毫不客气地告诉身边的人们,“她是我见过的最善良、最聪明也最美丽的女人,我彻底爱上了她。”
索耶则这样评价自己的丈夫:“他的宽厚中隐匿着某种危险,他的一点点野性之外是十足的温良,怎么说呢,他是危险和生机盎然的结合体,也就是说,他是地球表面最有趣的男人。”
写到这里,我们或许已找到了甜蜜婚姻的最大奥秘——别吝啬你的赞美,同时要让对赞美的回应如一见钟情时般的电光火石。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不少后来舞台上的宠儿往往在生命的起始处,并未受到这个世界的垂青——有的天生口吃,有的暗疾附体,尼克尔斯的童年是非常凄凉的,“因为,我是个秃顶的小孩儿。”
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而言,尼克尔斯主要是作为一位电影导演为我们所知的,可在他自己看来,电影只是点缀在他天边的美丽云彩,而舞台才是他生命绽放的真正所在。
他是在就读芝加哥大学时迷上戏剧的,在那里结识后来的喜剧表演搭档伊莲·梅与名作家苏珊·桑塔格,开始活跃于剧场。
1950年代后期,尼克尔斯组建了自己的剧团,成员包括蓝尼布鲁斯、乔纳森温特斯和一位后来在美国响当当的大人物——伍迪艾伦,他们在1961年荣获格莱美最佳喜剧专辑奖。
他和伊莲·梅组成的喜剧小品二人组“尼克尔斯与梅”更成为美国戏剧史上的传奇。在意外结束了舞台黄金搭档后,梅作为编剧与麦克还有多次合作,他们的友谊一直延续,2010年,美国电影协会授予尼克尔斯终身成就奖,上台为他颁奖的就是伊莲·梅。
在百老汇,尼克尔斯获得了惊人的九个托尼奖(其中两次是以制作人身份),他一度有四部舞台剧同时上演。20世纪60年代,他执导了尼尔·西蒙创作的早期喜剧《新婚燕尔》和《单身公寓》;40年后又执导滑稽的音乐剧《火腿骑士》,在那之后又过了将近十年,他将阿瑟·米勒的杰作《推销员之死》重新搬上舞台,大受欢迎。
2012年,80岁的他因执导《推销员之死》获得托尼奖。他的名字回响在曼哈顿上西区灯塔剧场之中,他儿时就是在这个街区长大成人。他亲吻了妻子——新闻主播黛安·索耶,走上舞台,开始回忆自己当年曾在这个剧场赢过一次吃馅饼竞赛,“那次很不错,但这次更好,”他说,“你们看,在你们面前的我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人。”
尼克尔斯何以对舞台演出如此痴迷呢?
他的早年经历或许会给出我们答案。
尼克尔斯是犹太后裔,他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躲避纳粹追捕而西走东藏,“在走进芝加哥大学前,我几乎没有任何朋友。”而当他在校园里遇到戏剧后,舞台上的绚烂第一次遮蔽了生命里晦暗。
稍加留意就会发现,不少后来舞台上的宠儿往往在生命的起始处,并未受到这个世界的垂青——有的天生口吃,有的暗疾附体,尼克尔斯的童年是非常凄凉的,“因为,我是个秃顶的小孩儿。”
事实上,四岁那年在一次接种治疗百日咳的疫苗之后,尼克尔斯的头发就掉光了,从那时起,他一直头顶假发度过了余生。这也许就是尼克尔斯偏爱舞台的真正缘由吧——可以名正言顺地戴上假发或摘掉假发,以戏剧的名义。
怎么说呢,所有的伟大可能都有一个卑微的注脚,一如尼克尔斯。
本版文/本报记者邵延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