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钦努阿·阿契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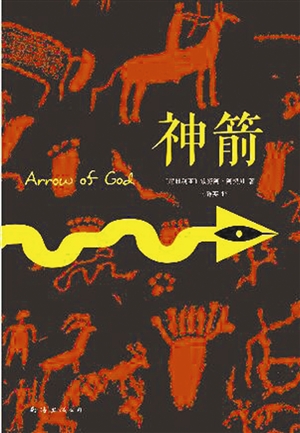



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作品《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再也不得安宁》、《神箭》、《非洲的污名》,南海出版公司2014年版。
●张艾茵(出版社职员)
迄今为止,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册中,先后出现过四位非洲作家,分别为尼日利亚的沃莱·索因卡、埃及的纳吉布·马哈富兹,以及南非的纳丁·戈迪默和J.M.库切。但是说到真正能够代表黑非洲文学的人物,当属被称为“非洲现代文学之父”的尼日利亚作家钦努阿·阿契贝,这位与诺贝尔文学奖失之交臂却获得了几乎所有世界文学重要奖项的作家,因来自于黑非洲心脏的发声享誉世界文坛。
在阿契贝之前,世界文学关于非洲本土的认知,更多地来自于西方视角,其中尤以康拉德最为知名,而阿契贝正是因为不堪忍受西方作品中对非洲的种种污蔑与误读,所以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非洲,以切身感受书写原住居民生活景观与文化变迁。
阿契贝1930年出生于尼日利亚,属于尼日利亚内战前最大的种族伊博族,保有非洲传统生活方式的同时,他从小就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加之尼日利亚官方语言为英语,这使他有机会遍读西方著作。他说当他在西方作品中看到非洲土著形象时,他会变得跟白人一样厌恶这些人物,“白人善良、公道、聪慧而且勇敢。与之相比,土著人凶恶、愚蠢、狡猾”,这使他开始反思非洲究竟是如何被妖魔化的,进而以“尼日利亚三部曲”(在国内曾被定义为四部曲,严格意义来说,《人民公仆》不应该属于其中)开启了他的非洲本土创作。
“尼日利亚三部曲”第一部《这个世界土崩瓦解了》(以下简称《瓦解》)初版于1958年,这部书使阿契贝名声鹊起也饱受争议。小说前半部分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伊博族村落的原始生活,真实而客观地还原了非洲人民的生活面貌,后半部分随着白人的入侵(先是武力,后来演变为精神渗透),着重书写西方文明对非洲传统文化的冲击,直至主人公信仰土崩瓦解的过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阿契贝在本书中塑造了一位颇具古希腊悲剧英雄色彩的人物奥贡喀沃,通过他命运多舛的一生折射出在时代变迁下,个体抗争的无望。虽然书中非洲式的生活方式与习俗让人多少产生距离感,但是关于传统的固守、文明的冲突、个体的挣扎、信仰的重建等核心命题却是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经历,也是“尼日利亚三部曲”所共有的主题。
《瓦解》出版两年后,1960年《再也不得安宁》问世,小说主人公奥比·奥贡喀沃是上部作品中奥贡喀沃的孙子,此时,随着时间的演变,乌姆奥菲亚人已经逐渐开始接纳西方文明,他们甚至决定集资送有才华的年轻人到英国留学。奥比·奥贡喀沃有幸成为第一人,并在学成归来后进入政府部门,却最终因为受贿走上法庭。如果说奥贡喀沃代表着传统与固守,那么作为尼日利亚独立后新一代的奥比·奥贡喀沃身上则充满困惑与迷茫。比之着力于文明入侵的《瓦解》,《再也不得安宁》把关注的焦点拉回到尼日利亚的当下,即转变中的阵痛和出路问题。
显然,在前两部作品中,阿契贝有意设置了一种内在的关联性,但1964出版的《神箭》则完全抹掉了这种痕迹,独立成篇。不过该书依然延续了基督教对伊博族传统文化和信仰的冲击这一主题,同时,在写作手法上也变得更加精进。小说糅合了民间传说、神话、歌谣、谚语等多种表现方式,在平实无华的文字中彰显出一种口头叙事文学的味道,特别是诸如“停在粪堆上的苍蝇能随心所欲、趾高气扬地走来走去,但它移动不了粪堆”、“独自一人看到一条蛇时,你不知道它是普通的蛇还是不可触摸的蟒”、“一旦我们跟麻风病人握手,他们就想要拥抱”等大量民间谚语的使用,不但拉近了读者与非洲这片古老土地的距离,更让人触摸到了这片大陆的灵魂和智慧。在内容上,本书与《瓦解》有几分类似,讲述了伊博族村落一位祭司埃泽乌鲁在坚守非洲传统信仰时是如何被基督教所摧毁的(于外,村民为了生存转投他教,于内,他的儿子在接近西方宗教后背弃了父亲)。在书中,主人公信仰的崩塌来得异常激烈,阿契贝似乎惯于书写悲剧性的结尾,这也使得整部作品蒙上了一层史诗性的色彩。
《神箭》无疑应该算是“尼日利亚三部曲”中最成熟、最出色的一部,它通过对埃泽乌鲁这一人物悲剧性命运的书写展现出作家对非洲土地矛盾而复杂的心理,正如他在序中所言“那些坚守者是那个了不起的男人——埃泽乌鲁——精神的继承者,我们至少应该向他们致敬,希望他们能原谅我们。”一方面阿契贝承认自己在外来文明冲击下的接纳与改变,事实上,他就出生在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家庭。另一方面,他通过对传统信仰坚守之人的塑造,试图重拾非洲的历史与精神图腾,但是无论是《神箭》还是《瓦解》,在不可避免的悲剧性结局里,都衬托出作家清醒的认知——要改变的必将改变!
在种种改变中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阿契贝是一位使用英语写作的作家,坚持使用母语——吉库尤语写作的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对他就颇有微词,但是阿契贝坚定地认为“我用英语写作并非因为它是世界通用语言”,而是因为尼日利亚是一个“用英语处理大部分日常事务”的国家,英语“除了是一门外来语言”,还是“将国内二百多民族团结在一起”的语言。但是他又与同样用英语写作的后殖民主义作家奈保尔大相径庭,与奈保尔的抽离相比,阿契贝依然可以在英语的外壳下积聚出众多的非洲元素,这也正是他的文学作品在让本土人民感到真实亲切的同时,又能够被世界读者接纳的所在。
继“尼日利亚三部曲”之后,阿契贝又陆续出版了长篇小说《人民公仆》、《荒原蚁丘》,中篇小说集《一只祭祀用的蛋》,杂文随笔《非洲的污名》等作品,其中《非洲的污名》收录了作家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2009年的一些随笔和演讲,是他的一本重要的文论集。在这本集子中,阿契贝以犀利、尖锐的文字直陈殖民地国家的种种罪行,“非洲在欧洲眼中属于另一个世界”,他们认为“这些非洲生物没有灵魂、宗教、文化、历史、人类的语言,以及智商”,于是“把一己之愿强加于人,攫取他人的土地和历史,然后把受害者伪装成需要监护的未成年人来混淆视听”,这些看法“本质上源于无知”,是殖民者“精心设计的一项发明”,甚至于“就连侵略者自己似乎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有时需要用无耻的伪善来掩饰自己的强盗行径”。 正是“由于殖民主义本质上就是一种对人的价值和尊严的否定,其教育计划不可能是完美的典范”,因此阿契贝提出“作为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拒绝被逆境定义、拒绝沦为其代理人或受害人来克服逆境的能力”,即非洲人民首先要自我觉醒,这也是阿契贝致力于文学创作的根本。通过他的作品,非洲终于得到正名,长久以来在文学上的殖民凝望得以瓦解,他为世人还原了一个真实的非洲,并希望这片土地之上的人能得到世界应有的尊重,从这层意义来说,阿契贝之于非洲的意义确实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