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钱理群一直坚持鲁迅的批判精神。 新京报记者秦斌摄
12月12日,北大教授钱理群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20日下午,钱理群在三联书店以“我与青年”为题再次演讲,向青年告别。钱理群在短时间内的两次告别,引发了广泛而热烈的回响。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他。
继向学术界告别之后,12月20日,学者钱理群再次向青年告别。在三联书店书籍和青年围成的一方“讲台”,钱理群做“我与青年”的演讲,他的学生邵燕君坐在前排。2002年6月退休之时,向北大学生告别,她也坐在台下,并向老师送了花篮。
事实上,钱理群已经多次,面对不同的人群,挥手告别。如同鲁迅笔下的过客,他被某个声音指引,不断前行,接下来的写作,除了面向自己,便是面向未来。他也一次次表明自己不理解90后及更年轻的一代,只能抽身远离。
演讲结束后,一位90后女生给钱理群献上了鲜花。
谈告别背后
“完善一个有现实关怀的自我”
“我觉得这个……不谈告别的话题!”告别青年的演讲开始前,钱理群和新京报记者在“老北京”餐馆见面,他落座不久,即对记者说。12月12日,他在“《钱理群作品精编》系列出版座谈会”上向学术界告别,在他看来,这只是一个寻常的发言,“在很小的范围里那么一说”,经过媒体的传播,却迅速“闹”成热门话题。
对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新闻”,钱理群用一个词形容——“害怕”,他“特别害怕”成为公众人物。告别的话题被广泛关注后,他接到了很多媒体的采访邀约,但绝大多数都予以拒绝。目前,他最大也是唯一的要求,是:“谁也别注意我,让我安静下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种告别,只是一种外在的告别,“内在的精神不会变”。钱理群边夹碗里的菜,边对记者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关心现实是不可能的,但我希望能安静下来,用我最后的时间,来完成和完善我自己。”“完成和完善自己”,正是向学术界告别时谈到的重点。为此,钱理群强调自己只是告别学术界,并非告别学术,他还有八九本书要写。
这些年,钱理群不断告别,向“民间思想村落”告别,向北大告别,向中小学教育告别。向前者告别时,他写道:“我觉得,我是一个过渡性的人,我应该退出你们生活的舞台了,我不希望我的思想成为你们继续前进的一个阻力或者负担。”如今向学术界告别,12月20日又向青年告别。
“告别”成为他晚年生活的关键词,每一次告别都“很痛苦”,也反映出他身为学者的言说困境。“这太正常了。我现在和青年的关系,是爷爷和孙子辈的关系,你尊重爷爷,但他并不懂你。说老实话,我和孙子辈谈到这个份儿上,还有人愿意听,已经很不容易了。得见好就收。”钱理群说。
他一直记得导师、北大教授王瑶的一席话。“你作为一个人,应该清楚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因此,你就必须能拒绝诱惑。”王瑶说。时值1981年前后,作为王瑶助教的钱理群,被认为处在一个相当有利的位置,“会有很多人找你写文章、开会”。
“对于一个正在往上发展、势头很好的年轻人来说,这句话的分量,你想想看!否则,你做了很多次演讲,你出了无数的书,看起来已经很辉煌,但是到最后,你心里很悲凉,因为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没有完成。”钱理群说。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他一直遵循着王瑶的教导。“这次也是这个意思!”他放下筷子,提高了声调。
采访时,钱理群说得最多的一个词语是“自己”,表现在研究和写作上,即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它当然同时作用于社会,但我更追求的是自我精神的完善。”
钱理群出生于1939年,成长于红色年代,亲历了“反右运动”、“文革”等。如今人们所理解的“自我”,更着重于“我”,但钱理群这一代人,无论怎样强烈的自我,都被时代伟力改变,和国家的前途、民族的选择紧密联系在一起。“我要完善自我,是完善一个有现实关怀的自我。”钱理群说。
谈个人信念
“乌托邦有价值,但要明白它只是乌托邦”
此番告别之后的写作,钱理群强调是面向未来。“我现在所关注的问题,我所思考的东西,不一定为现在的人所关心。但是我觉得,就像现在的人回顾‘五四’,甚至回顾八十年代一样,迟早我们的后代会关注眼前这个时代。”钱理群称,他要做的事情,就是为后人留下另一种声音。
孙郁等多位学者觉得,钱理群像鲁迅笔下的过客,只知道不断朝前奔走。“至少我很受鲁迅的‘过客’的影响。我总觉得前面有个声音在指引我向前走,但前面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更强调过程,意义在走。背后包含着鲁迅的‘反抗绝望’的哲学。”说完,钱理群自己点了点头。
青年时代,钱理群这一代人面前,耸立着一个明确的目标。后来,这一信仰幻灭了。钱理群对此有过深刻剖析。在他看来,信仰是彼岸的追求。“我们那一代人最大的教训,是不能分清彼岸和此岸,我们相信彼岸能够成为此岸的东西,但事实上,天堂变成此岸就成为地狱。彼岸的世界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否则不叫彼岸。”
信仰坍塌之后,无力感、虚空感掏空了几乎每一个人,人们对“彼岸”整个予以否定。“但是我不!我还是年轻时的那是个信仰,但我很清楚,那只是彼岸的东西——可以接近,永远达不到。”钱理群说。正因如此,信仰所产生的精神力量在他身上没有完全消失,仍然支撑着他。用学生余世存的话来说,他逃不过时代的宿命。
“讲具体一点,我们那一代人有一个简单的理想,是消灭一切人压迫人、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以前我们以为,现实生活可以做到,但现在发现,这永远存在,甚至社会的每一个进步,同时带来新的奴役,比如说网络,就是这样。”钱理群解释说。
在他眼中,自己的这一信仰——“如同北斗星照亮”——对现实具有极强的批判性。对教育制度,对历史文化,他都提出批判意见,但不像鲁迅,论战时树敌众多,甚至因此影响身体健康,而是采取“不点名战法”,从不点出具体的名字。“这没有削弱战斗性,反而避免了很多无谓的东西,也减少伤害他人。”
“凡是社会中出现压迫、剥削、奴役,都是我批判的对象”,钱理群认为这是自己的信仰价值之所在。更进一步,他始终觉得乌托邦自有价值,甚至需要一个新的乌托邦,问题在于,要明白乌托邦只是乌托邦,不能为社会现实提供具体方案。
钱理群称,在这一信仰驱动下的批判,同时有所建设。“压迫不能避免,但你可以减少、防止。我觉得一个理想的社会是可以做到的。”说着,钱理群笑了笑。在当日告别青年的演讲中,他试图呼吁青年重建理想、信念、信仰,并提出两个建议:自由地读书;沉潜到社会底层,与老百姓建立不同程度的精神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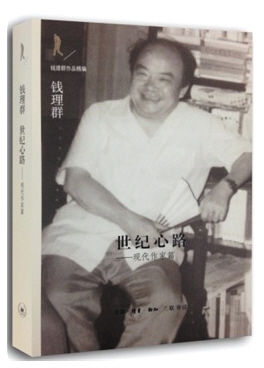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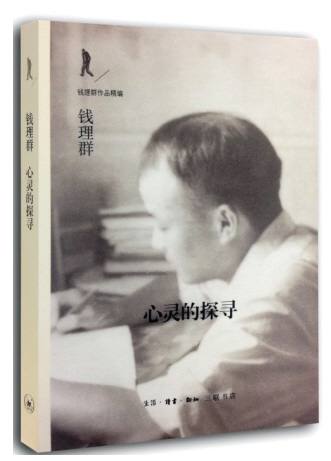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整理出版了“钱理群作品精编”,该系列计划共十一册,分为专著和文集两种类型,整合收录了作者主要的学术专著和文章随笔,既是对钱理群先生学术思想阶段性的总结,也试图呈现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主要成就,并对重新思考“时代”与“思想”有所助益。
“很多人问我,你那么大年纪关注年轻人干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对一切都绝望了,我唯一不能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都绝望了,你靠什么生存呢?”
谈无力感
“像一支箭,射到大海里去”
“我怀着反对一切压迫、剥削、奴役的信念。”钱理群边咀嚼,边对记者说。
这形成了钱理群内心世界的“底色”。1988年,学者汪晖在文章中说:“温和的微笑与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充满激情的声音几乎伴随着钱理群所到的一切场合,但倘若你留心,就会在他偶尔显得疲乏的眼神中读到几丝深沉的悲凉。悲凉对于钱理群来说是一种人生境界,它的基础不是对于这个世界的失望与憎恨,而是对于自己的失望与憎恨……”
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现实越来越超出钱理群的理想,这种失望越来越广泛而深刻,“我应该说是有些绝望的”。9·11事件发生,他说:“使我再一次陷入了言说的困境。”社会贫富分化日益严重,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因为“最初没有察觉”。有人认为,这是观念与现实错位后的必然结局。钱理群一直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批判不就很有力?”记者问。
他摇摇头,说:“鲁迅的一句话我一直引用,意思是我批判的言说,像一支箭,射到大海里去——它是箭,射出去了,但落到大海里了,不起波澜,能起一点波澜就了不起了,但事实上,不起作用。”从这一角度来说,他的批判最终都是出于对自己的责任,“是为了我自己”。
2012年,钱理群发表“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批评,在社会上引起轰动。事实上,这一批评是中学教师向他反映的。乘电梯时,钱理群讲到自己身边时常发生的事情。有些学生来告诉他,喜欢听他的课,能说出几点听起来不错的理由,钱理群便悦纳他,找自己写推荐信,也欣然提笔,可是此后,再也看不到他们的踪影。
“他的微笑,他的说话,你没办法不信任他,但他是有目的的,一旦达到,就离开了。这很可怕。”钱理群感叹。
他一如既往地信任学生,发表批评,但是,他强调,这些批评的影响“极其有限”。他指着记者说:“如果你认识的这个人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你能怎么办?能改变他吗?如果有作用,那只是起到警觉的作用,比如一个年轻人很想向他看齐,听了我的话,会自己思考。”
在钱理群看来,知识分子的言论,唯一的作用是社会清洁剂的作用。因而,他的要求只是“允许我说话”,“我来提醒你注意,至于做不做,那是你的事”。同时,他展开行动,和青年志愿者在一起,建乡村图书馆,进中小学讲课,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服务等,身影活跃于民间,也因此积聚了“丰富的痛苦”。
钱理群称他已经看透,对自己的言论价值、有限性早有清楚认识。“我经常说,对我的言说的价值的估计,是在小数点后零零零零零几,是不大的,但是有,而且基本上是正面的,我就很满意。很多时候我都是白说,但是白说也要说。”钱理群说完,又笑了起来。最后一句,是其师王瑶一贯的观点。
吃完饭,距演讲半小时。人们不断赶往演讲场所,他们已在等待钱理群。其中,绝大部分是青年人。
■ 对话钱理群
哪怕骗自己,也不能对青年绝望
新京报:在社会现实让人产生无力感的时候,在你看来,青年应该何为?
钱理群:我觉得,第一,本来是最低标准,现在是最高标准,就是说真话,坚持自己。有时做不到,那你就沉默,但是对青年人来说,可能沉默也做不到。比如我曾经接到过一个大学毕业生的信,他说我必须对某个问题表态,不然不能毕业。这给我出了个难题,我怎么说?我跟他说,你应该表态。你不说,你就不能毕业,找不到工作,那你只能够妥协和迎合。
这时候,你要掌握三点:首先,分清是非,知道自己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你别将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的事。很多人最初说谎,心里不安,到后来,越来越心安理得;第二,你必须是被迫的,不是主动、自觉的;第三,不能伤害他人,一切后果你自己负责。这三点对于年轻人来说,很难。
第二,我提倡从自己做起,从改变周围做起,我提出“静悄悄的存在变革”。比如,现在读书会很多,这是好事。当然,也要保持独立性,不受惑。
新京报:你为什么这么关注年轻人?
钱理群:很多人问我,你那么大年纪关注年轻人干什么呢?我的回答很简单,我说对一切都绝望了,我唯一不能绝望的是孩子,如果对孩子都绝望了,你靠什么生存呢?这个问题看似说得很大,其实,你看看现在很多年轻的父母,为什么对孩子特别上心,投入极大?他们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个社会我无力改变,于是想尽办法对孩子好。对我来说,也是这个问题。
不管我怎么绝望,但是,哪怕是骗也要骗自己,我总得留一点希望啊。鲁迅说,故乡对我的蛊惑是哄骗我一生;我明知这是哄骗,我做什么事都失败,对什么事都绝望,但哪怕是虚妄,也要给自己希望。我是抱着这种信念去的。
新京报:你在中小学讲课,对90后或者更年轻的一代,是否能获得他们的认同或共鸣?
钱理群:我去上课,老师宣传说你们向往北大,北大有钱某人,现在他都到门口了,你还不听吗?但是,听课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和高考无关。最后坚持下来,只有二三十个人,但是,他们作业的水平,对鲁迅的理解,比大学生还高。这就够了!
新京报:这是一种希望吗?
钱理群:不,不,教育的力量再大,也比不上社会的力量。在初期,可能受我的影响,但是大学毕业之后,却可能走向另外一条路,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过,说得极端,我经常谈到前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小说中的场景,一群孩子小学毕业了,有人演讲,说长大后,我们当中有人可能成为坏人,但是只要小时候有这种美好的记忆,即使成为坏人,也跟一般坏人不一样。你播下了一个健康的好的种子,也许后来变成另外的样子甚至夭折,但有没有这个种子,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