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日本的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一些“社会推理小说”,比如岛田庄司的《展望塔杀人事件》,都市人骇人听闻的冷漠和自闭催生了奇特的凶案,他们聚居公寓,永远行色匆匆,不相往来,暗中互相窥视,嫉恨潜滋暗长,越是“华灯初上”的夜间,越是万念灰芜以致萌动杀心。安部公房对都市人孤独的体触犹甚于岛田,不过安部式人物的对策并不是暴力。他的主角都是一些“everyman”—没有名字,在让他们感到陌生的生活环境里经历了自信灭失、身份消溃的过程。夜晚,都市完全陷入了人造景观的控制中:车灯、街灯、霓虹灯以及“万家灯火”,安部用一种更加接近西方小说的声音去描写它们映射在人心里的感觉—孤独的无名氏们决定出奔。
都市之困
在安部公房的《燃烧的地图》进入尾声的阶段,逡巡数日的调查员从一条胡同里经营情色交易的地下酒吧出来,身后,那个名叫田代的小伙子匆匆尾随,告诉他自己给他的情报都是假的,“我是顺嘴溜出来的”。调查员不理不睬,继续前行,几天的工作已让他十分淡然,围绕着那位失踪的根室科长,没有一个人能给出准确可信的线索,相反人们似乎还乐此不疲地向他编造各种不相干的故事。他来到街上,看到“街道不知不觉地被光的分泌物掩埋,在黑夜里打进白昼般的楔子,狂乱时刻的节奏拼命地让行人陶醉”。
1967年出版的《燃烧的地图》,可读性和名气都逊于早六年发表的《砂女》。根室之妻,一个经常酒醉、有点狂乱的漂亮女人,以一周三万日元的价格委托主角去查找失踪的丈夫,很快,读者就被远远带离了扣人心弦的侦探故事,进入冗杂琐碎的谈话里。调查员拿到几样线索,起初,读者跟着他一起分析案情:一盒火柴,窗帘上钉着的电话号码,手绘的地图。然后,线索消失了,地图根本没用,失踪者的美貌妻子再次出现,调查员进入了最危险的领域—性,他进入了女人的身体,同时忘记了他自己是谁,他应该是谁,他要做什么。
“烧毁自己的地图,走进他人的沙漠,除此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出发点,因为这是都市的时代”安部公房本人谈《燃烧的地图》的这句话包含了他最钟爱的几个意象:“都市”、“沙漠”、“地图”、“出发点”,也让我想到了书中多次出现的人与“点”的对应。安部认为,地图是人丧失生活本质的一个重要证明,在地图上,风景变成了一个个乏味的色块,风景中的人最终在自己眼里只相当于地图上的一个点,这就是都市对人的异化。调查员在寻找失踪者的过程中进入东京的地下社会,那里电影院、酒吧、赌场、妓院林立,数量庞大的灰色人群,酗酒的、打架斗殴的、敲诈勒索的、拉皮条的、卖淫的都栖身于此,他厕身其间,与人交谈,人们漫不经心,不是答非所问就是信口雌黄,使他的存在感急剧下降:“当海盗作为海盗扬帆在陌生的大海上时,当盗贼作为盗贼躲藏在荒无人烟的沙漠、森林、都市的底层时,他们一定曾在什么地方超越过变成一点的自我我什么也不是,不需要任何同情犹如在沙漠上即将渴死的人为即将溺死的人抛洒泪水一样愚不可及”
都市如丛林,如大海,如沙漠,在这里做守法良民,还不如一个不法之徒活得更有人样。《砂女》中有真实的沙漠,那是主人公—一个“男人”(他的名字“仁木顺平”只出现过三次,且都在法律文书之中)的遁避之地,他有家有业,却趁着难得的几天工假拿着网兜,孤身一人来到海边沙丘之中的穷乡僻壤捕捉昆虫,可见他与都市的真实关系。读者自然明白这一点,当他误入沙崖之下,被村人以沉默的方式幽禁起来时,他的咆哮看起来既可怜又滑稽:“你们这可是大错特错了!不巧得很,我可不是流浪汉我不光纳税,而且还有居民户口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申请寻找我的,到时候看你们怎么办吧!这么点儿事情,你就听不明白吗!我倒听听你们打算怎么辩解”
这就是“良民”,一个无我之人外强中干的抗议。安部公房的隐喻刀刀见血:捕虫者自己被捕入笼,人投入沙漠,为了逃避沙漠一样的都市;都市人身处流沙,他们早就像掉进猪笼草的昆虫那样,被都市的万家灯火、车马喧声泡得软绵绵的了。在《燃烧的地图》里,安部公房继续以虫喻人:“(我)像黑夜里的虫子一样往行人开始涌动的人造灯光的方向疾步走去”—人成了渺小低级的趋光动物。在《他人的脸》里,在“我”不幸毁掉的脸里住下了一个水蛭窝,他与水蛭共生,用紧紧裹住脑袋的绷带藏住了污秽的真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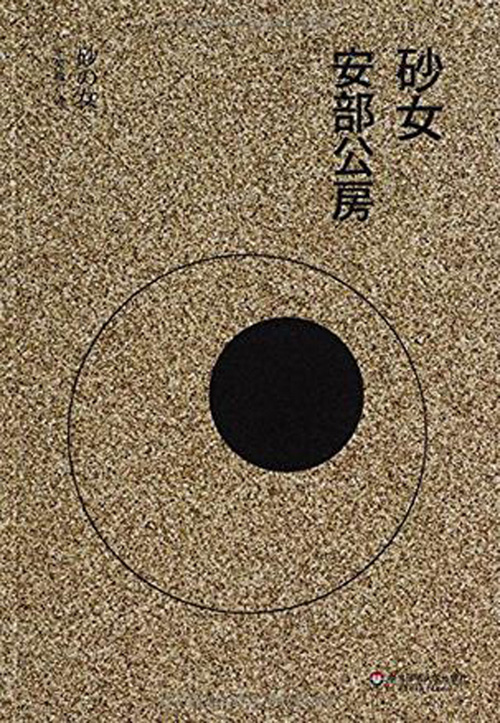


《砂女》、《他人的脸》、《燃烧的地图》[日]安部公房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年4 月出版
“家”的破灭
安部公房书如其人,在谈到自己的生平时,他也习惯使用小说里的意象。他生于东京,1920 年代常居中国满洲,而“九·一八”事变期间,他跟随母亲住在北海道,经常搬家对作家的成长显然是好事,但安部的叙述渗透着巨大的疏离感:“我的出生地,我长大的地方,我家族的起源之处,是地图上的三个不同的点。本质上说,我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
作为国家的“日本”同他有着遥远的心理距离,现代化的东京与北海道和满洲之间是互相隔绝的,然而隔绝并不意味着中央与地方(满洲一度曾是日本的“地方”)、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在安部的记忆里,在北海道度过的乡村生活并不是东京的反面,乡村不是清洁、恬静、闲适的共同体,而是城市的一个变体,北海道的村民为了共同利益而劳作,实际上是在变相地囚禁个体,缓缓扼住他们发声吐气的咽喉。安部在《砂女》中把大海写成让人绝望的大地边缘,在那里安放一个恶意满满的穷村,仿佛是述说他的亲身经历:“男人”初到那里时表示,“我最喜欢在老百姓家里借宿了”,后来才发现自己落入了陷阱,共同诱捕了他,最后把他变成了自己的一分子。
满洲也没有留下任何美好印象。安部公房曾说,满洲是一个可怕的地方,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街上处处是被贩卖为奴的孩子。奉天,也就是现在的沈阳,在安部的记忆中是个巨型垃圾场,用黑砖砌的房屋丑陋无比。人陷身其中,不辨东西,不知美为何物。他在一篇访谈里说他经常挨老师的骂:“不管什么时候,他们一骂我就会这么说:‘我们国家的孩子绝不会做出这种事来的。’我便心心念念地向往日本。”然而,他在满洲见到的来自本土的同胞都是些深受军国主义洗脑的人,他们满脑子“五族共荣”,视肮脏的现实为无物。于是,“家”的幻觉也在他的头脑里破灭了。
奉天的黑恶混乱历历再现于《他人的脸》中,而东京,那个让他幻灭的出生地则铺成了《燃烧的地图》的背景,安部写到哪里,人们就在哪里失踪。无脸人觉得失踪不是什么坏事,世人如果没有面貌,或是大家都一个模样,生活会好过许多。调查员对田代说,你看玩弹子球的,泡酒吧的,听音乐的,他们跟我有什么区别?“在这儿匆匆赶路的人好像都是一时性的失踪者,只不过是几个小时和一辈子的差别而已”

安部公房书如其人,他曾说:“本质上说,我是一个没有家乡的人”
所有感到窒闷的都市人,都会考虑抓住“移动”这根救命稻草,只有自己不停地移动,静静伫立的水银灯才会显得不那么冰冷乏味。这个人离了婚,放弃了朝九晚五的职员生涯,干上了这份调查失踪者的工作,既是疏离的结果,又反过来加剧了他与环境的疏离。他得以游动到社会的边缘,做一个观察者,但是,与过去的生活一刀两断,与其说是一个人摆脱个人困境的努力,不如说是这困境的爆发。他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安部公房标志性的语言也是为都市的疏离而造的。他喜欢在叙事中插入科技语汇以及社会新闻的语言,它们像实验室一样精确而冷酷。被陷阱捕捉的男人,根据物理学来测算自己有多大胜算能逃出沙世界,没有脸的男人花了很多时间研究仿造人皮的化学原理,调查失踪者的男人,凝视着汽车交会之间飞舞的纸屑,“感觉到空气是一种物质”。有时,我会想到那种独具日本特色的“怪诞科学体”。日本人发明了一些奇特的东西,比如绑在筷子上,用来吹面条的小风扇,比如能把头部固定在墙上、方便乘客站着睡觉的装置,画面旁边,日本人用说明书语言,图文并茂地解释这些发明的原理和用途,这时,画面里那个演示者会突然显得十分陌生,好像她已不是真人,而成了这台机器的一部分了。
这种惊悚的陌生感,是安部公房作为“存在主义小说家”的一个标志。这批小说家,早年都深感两次大战之间社会之阴暗,并为此忿忿不平,两颗原子弹爆炸后,他们心中对道义的确定认知瞬间土崩瓦解,先后转投存在主义—从政治、战争、帝国主义的大非大是,转而关注个体卑微的沦亡。存在主义,就是卡夫卡的虫子、萨特的墙,现在还要加上安部公房的沙坑、假面、地图和水银灯。日本的新浪潮电影导演使河原宏,将《砂女》、《他人的脸》、《燃烧的地图》先后搬上银幕;和小说的知名度完全吻合,《燃烧的地图》几乎没有走出日本岛的范围,是三片之中最鲜为人知的一部。
但《燃烧弹地图》却是三书之中让我沉浸得最深的一本,因为都市的色彩、气味、声音,到哪里都是一样的,而安部将它们变成了触目惊心的问题。无名无姓的“我”在同女主人公发生性关系后,顿悟到自己也是成千上万失踪者之一,统计报表里的一个数字,地图上的一个黑点。我过去为什么要害怕人迹罕至的环境?莫非我真的以为,在人群我是安全的,我失踪了会有人来找我?不是这样的—他说:“即使满街没有行人车辆,取而代之的是成群结队的食火鸟和食蚁兽在路上昂首阔步,也许我只是将其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并努力去理解。”
也许我们都只能接受逃无可逃的命运,并设法拥抱它,主动变成内心的失踪者,我们踩动油门,或迈开脚步,像影院散场后溃散的人群一样穿过这臃肿城市的每一个路口,沐浴在街灯幽绿色的分泌物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