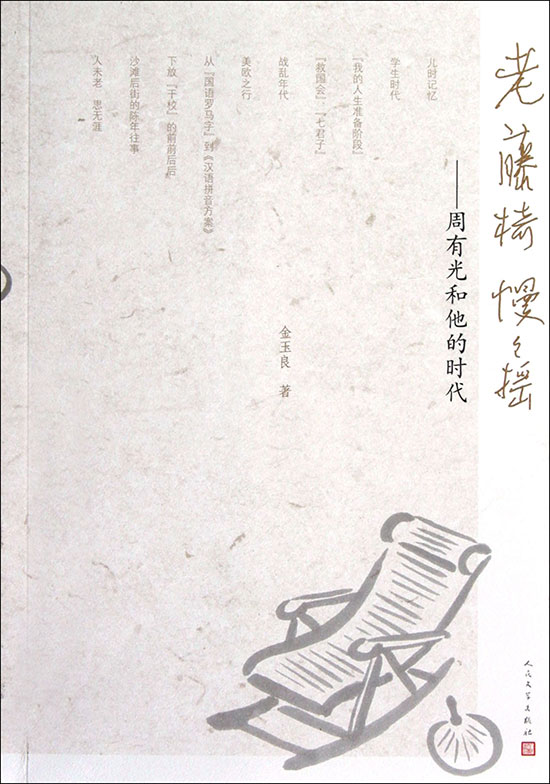
每個老人都是一部曆史書。何況這位老人名叫周有光!
在周有光先生漫長的生涯中,先搞經濟,西裝革履供職於大銀行,業務辦到美國華爾街;解放後服從組織,50歲時轉行語言學,研究創制漢語拼音,跨界成功,被稱作“中國漢語拼音之父”。
搞經濟,那是民國時期的事。那時銀行界的人都知道有個聰明、有幹才的周有光,他不僅辦事能力強,還搞研究。1949年香港經濟導報社出版他的專著《新中國的金融問題》。看題目就知道,在政權更替之際,與許許多多選擇留下來建設新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樣,他是要以己之長報效國家。但是,新中國的金融問題、經濟問題、老百姓吃飯穿衣問題,已然是蘇聯模式下的計劃經濟的一套新經,老和尚沒咒兒念了。周有光轉行,倒是轉對了。雖然後來政治運動不斷,周有光的人生際遇也不免隨大流顛倒浮沉,進“牛棚”、下“幹校”都有他的份兒,但畢竟bpmf這些拼音字母離政治遠些。
苟全性命於亂世,周有光看得多也想得多。待到改革開放局勢寬松了,特別是他退休後,走出語言學專業領域,85歲開始寫文章,廣泛探討諸如現代化、全球化、中東局勢、印度經濟、三權分立、人權保護、公民意識等等問題,引起社會關注,成為公共知識分子、公眾人物。
我讀過周先生的這類文章,篇幅都不長,文字淺白如話,意思講得明白,不論怎樣大的題目,經他睿智地闡釋,就不再高深莫測,人人能懂。這是高手文章,舉重若輕,閑庭信步,是識見超人、智力優越方能達到的境界。所以周有光的粉絲多。特別是得知老先生百歲之後仍然可以每月寫一篇這樣高屋建瓴又明白曉暢的文章,粉絲更其驚喜感佩。
人出名了,軼聞逸事也多。人們發現,哦,原來,周有光與作家沈從文是連襟,娶的是美麗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張允和。 張允和愛唱昆曲,漫畫家丁聰畫過他們夫婦一幅漫畫:周老頭兒蹬著三輪車,車上坐著手持簫管的張老太,二人淺笑盈盈,雙雙赴會。老兩口一輩子和睦,舉“杯”齊眉,兩“老”無猜,令人羨煞。
而養生風起,老壽星的養生之道自然是人人樂聞。周有光先生卻只雲淡風輕地順其自然,白菜豆腐加肉松,喝茶,也喝星巴克咖啡,每天讀書看報,關注天下大事——今年某日,我隨金玉良女士去探望周先生,介紹寒暄後,周先生開口說,哎呀某某人死了!那天早晨我還沒來得及看報,還不知此事呢。當下心想:老先生消息真靈通啊!何老之有!
金玉良女士是周有光先生的“小友”,她退休前與沈從文夫人張兆和是作協同事、好友,後來與張允和、周有光也熟識起來。金玉良性情溫良,為人謙和,特有老人緣,幾位老人都和她要好,彼此往來密切,了解深入。周先生深厚的學養、豐富的人生閱曆、前瞻的思維和儒雅的談吐深深吸引她,十多年來,不論酷暑嚴寒,每周一次探望周先生,陪老人聊天,聽老人講他的人生經曆、講過往年代。她記下來,如今竟成一本書——《老藤椅慢慢搖——周有光和他的時代》。老先生親自題寫了書名,大有“禦筆欽定”的意思,又可作“防偽標識”,總之是很滿意這本書的。
以往金玉良建議老先生寫自傳,老先生都謙虛說:“我沒什么可寫的,我的生活經曆很簡單。”——讀完金玉良寫的這本書會由衷感歎:哪裏簡單?!周先生今天所達到的人生境界,終歸是他百年人生不斷曆練、修為的結果。即如健康長壽這件事,每個人帶著自己的DNA、家庭的影響,於人世間走自己的人生路,起點有多高,作為有多大,天地有多寬,眼界與胸襟、坎坷與通達……無不相關,又怎是單單問個生活起居、飲食習慣就以為得了健康長壽秘訣那么簡單?
金玉良在前言中雖謙虛地稱這本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周有光傳記,她只是把日常聽到、看到的綴字成文,和喜歡、熱愛周先生的讀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滄桑,但翻開書一頁頁讀下去,周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他所處的時代、社會的面貌,就像懷舊的老電影,浮現眼前,帶著豐富的曆史細節,帶著生動的悲歡。
閑來讀書,不會去讀“中國抗戰時期經濟史”這樣專業圖書,但閑讀周有光這本書,卻能了解到許多當時經濟情況。比如,周先生回憶中講到農本局,我問過學經濟的人,也不甚了了。據周先生解釋,農本局就是特種農業銀行,其資本來源,一半政府分期撥給,另一半為合營資金,由各商業銀行按當時儲蓄存款額的比例攤派。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後,為解決大後方百姓的吃飯、穿衣問題,政府加強農本局的領導。國民政府經濟部次長何廉受蔣介石委派,出任農本局局長。局長下面有兩位協理(即副局長),一位協理負責與金融界的溝通和協調等有關事務;另一位協理蔡承新負責農本局的日常業務。農本局的宗旨是促進農業信用的流通,促進農產品運銷。
當時,由於沉重的地租和苛捐雜稅,農民幾乎達不到溫飽,更談不上積存。在耕種季、收獲季,在青黃不接的時候,在遭遇天災人禍的時候,農民主要從高利貸者、地主和商人等私人手中借貸。上世紀30年代,盡管已經有了銀號(即錢莊)和當鋪這樣中國傳統的信貸機構,但是錢莊通常設在城市、商埠,農民無法利用。當鋪的情況比錢莊好些,在農村有代理店或代理人。當鋪的借款利息,按照法律限制月息是三厘,但實際生效利率往往比三厘高得多,期限也比較短。典當者在期限內如果無力贖回自己的物品,當鋪便將其賣掉並從中牟利。雖然如此,當鋪規定的條件還是比從私人手中借款要好些。然而,大多數農民家徒四壁,兩手空空,他們幾乎沒有可典當的財物。農民需要新的信貸來源,新的基層借貸機構。
在何廉領導下農本局適時地在後方廣大農村,建立以縣為單位的農業合作銀行(即合作金庫);又因陋就簡,盡量利用已有的公共財產,如鄉村的祠堂、關帝廟或觀音廟、集鎮的會館來籌建農業倉庫。有了農業倉庫,農民把收獲的物產儲存在那裏,就不用擔心黴爛、損壞。同時,農民如果需要現金,可以用儲物作為抵押從倉庫借款。農民從合作金庫借款,利率很低,而且也不用物品擔保;只有一個條件:必須是本縣合作社社員。因為合作社連帶有集體責任,合作金庫借出的錢款不必擔心不能歸還。
農本局相繼在四川重慶、湖南長沙、陝西西安、貴州、廣西桂林、湖北西部設立專員辦事處。蔡承新是一同參加救國會的老朋友,周有光經他介紹,在重慶專員辦事處主持日常工作。從1938年到1939年一年的時間裏,重慶專員辦事處先後在三十多個縣,成立了合作金庫和農業倉庫。周先生到省內一個又一個的合作金庫和農業倉庫巡回指導、審查;還嘗試辦家畜保險業務;為了改良柑橘品種,和金陵大學農學院園藝系的教授到江津、綦江等處調查。他跑遍四川各地,對那裏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
他說剛到四川住在旅店裏,他拿兩塊錢請茶房代買柑橘。一會兒,茶房背回一大背簍上好柑橘。他驚訝,怎么買這么多?茶房說,兩塊錢就是這么多。事後他才知道,橘農沒有儲存條件又無法外銷,柑橘大量上市時根本賣不上價錢。農業倉庫建成後,農本局仿照北方夏天窖冰的方法,向橘農推廣如何把柑橘儲存在倉庫裏。柑橘儲藏問題解決了,橘農的收入也提高了。
到處奔波,還要隨時跑警報,躲空襲。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寇連續兩天對重慶市區實施震驚中外的狂轟濫炸。山城變成火和血的海洋,5000多人被炸死,房子大部分燒光了,以至於站在市中心就看到長江和嘉陵江邊了,20萬老百姓無家可歸。周先生回憶5月4日傍晚,他們聽到空襲警報趕快把日常公文收拾就緒搬入地下室。喘息未定,離辦事處不足二三十米的地方突落數彈,門窗全毀。東邊的興隆街首先起火,接著西邊被炸的地方也煙火大作。形勢危急,他們當機立斷只留兩三人看守辦事處,其他人攜帶賬冊連夜繞道送總局寄存。不久,周先生帶著他的辦事處遷往長江上遊宜賓。
周先生說:“人越是在困難的時候越不能消沉。”周先生特別善於在艱苦生活中發現樂趣,一生都是這樣。往返於宜賓、重慶之間,他常常坐一種形似“蜻蜓”的水上小飛機,那是他平生坐過的交通工具中最有趣的。飛機翅膀居然是綢子做的,有兩只船形的木頭腳可以停在水上。當時長江、嘉陵江沿途都有水上小飛機,主要是郵政部門投遞信件用的。飛機上有一名駕駛員、一名助手。後部放東西的邊上,還可以坐一兩個人,他們常常把這座位售出賺點“外快”。飛機停穩後,小船劃到飛機旁邊,接送信件或人員。飛機很小,飛得很低,水中的魚呀、草呀,看得清清楚楚。妙極了!這有趣的飛機還救過張允和的命。一次她患痢疾,大家都認為沒救了。但朋友幫忙在重慶請到一位名醫,一星期兩次坐水上飛機到宜賓診治。奇跡發生了,張允和痊愈了。
周先生在農本局的工作是出色的。何廉曾在文章裏寫道:“在四川省會成立一個大辦事處,管四川的合作金庫和農業倉庫等單位,並派周耀平(周有光當時的名字,筆者注)任主任,周是一個很能幹的人,大學畢業,在上海的銀行裏做過副經理,富有經驗。”
回顧農本局歲月,周先生說:後方的農民保證了抗戰時期的糧食、棉花,解決了吃飯穿衣問題。直到抗戰結束,基本沒有出大問題,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當時政府每一個方面都是向老百姓要錢的,而錢哪裏來呢?追本尋源主要從農民身上來的。只有農本局把錢借給農民,幫助農民發展生產,所以農本局對抗戰是有巨大貢獻的。
抗戰期間,周先生還做了一項艱苦而有意義的工作,就是一九四三年三、四月間,新華銀行等四家銀行組織“西北經濟調查團”,調查陝西、甘肅的經濟情況。這個調查團名義是民間代表團,實際是應政府要求組織的,政府給調查團提供吉普車等交通工具。調查團由五位銀行家組成,周有光是該團負責人。調查團由重慶出發到西安、蘭州、武威、張掖、酒泉,直走到嘉峪關、玉門、安西。
每到一地,他們先去拜訪當地的府衙,結果令人遺憾,官員們對自己轄區的基本情況幾乎茫然無知,連基本的經濟統計都沒有。調查團有人想到了教會,便去天主教堂了解情況。周先生說:“噢,不得了!他們給你講得頭頭是道。”調查團在西北獲取的最有用的資料,幾乎都來自教會。
周先生說,西北的教會主要是西羅馬系統的天主教,神父大多是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這些傳教士文化水平很高,都是大學畢業。到了中國他們要不斷學習中國文化,不但學習國語,還要學習當地方言。他們要深入邊區,深入農村,深入群眾。他們對中國的情況一清二楚,會定時向羅馬教廷報告。所以,說他們是特務也不冤枉。
調查結束,別人都回重慶,周先生興致高,再往前就是敦煌,他要去看千佛洞。路上黃沙漫天,男人要隨時下車鏟沙子。途中,一位用紗巾蒙著頭和臉的摩登女郎帶著孩子搭車,講一口流利的法語,原來是常書鴻夫人,去探望正在那裏幾間破破爛爛的房子裏籌建敦煌藝術研究所的夫君。到敦煌,畫家張大千和考古學家向達也在那裏——他們每個人在抗戰艱苦環境下,都堅持在做自己的本職工作。
抗戰時期,周有光和許許多多中國人一樣,不僅吃苦,而且承受國破人離散的慘劇。抗戰八年,周有光和張允和搬家36次,可愛的女兒小禾不滿六歲,因為生病沒有盤尼西林,死在媽媽懷裏;兒子一日在外被流彈擊中,所幸大難不死。在周先生夫婦心中,那是怎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需要多長的時間、多大的心智去慢慢化解?
抗戰勝利後,周先生供職的新華銀行,派他去美國、英國開拓業務。周先生眼界更開闊了,人也闊了。在美國感受四通八達的鐵路,高檔車廂裏還有浴室;去英國乘豪華遊輪,有遊泳池,晚宴都要穿禮服,張允和單是旗袍就帶了一二十件。周先生頗為風趣地對金玉良說:“那時我有那經濟條件。不像你認識我時,都窮趴地了。”
一時赴觥籌交錯的華宴,一時過“憑票供應”的日子;65歲於“幹校”挑擔插秧,98歲在北戴河下海遊泳……窮過富過,歡喜過悲痛過,春風得意過也坎坷失意過,這就是一個人的一生,一個人的百年史,您以為老壽星是怎樣煉成的?
(本文原刊於《經濟觀察報》觀察家2012年12月 作者:郭娟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審、周有光《老藤椅慢慢搖》責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