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動互聯網的環境下,人們獲得知識越來越容易,包括傳統文化和經典作品,絕大多數也能在網上找到為數眾多的電子本和研究材料。與此同時,讀者甚至是學者,習慣了碎片化地獲取知識,卻也很難有之前埋頭鑽研的心態了。
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傳統文化與經典閱讀,是比以前更好還是更壞?7月1日,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傅傑、複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汪湧豪在思南公館對談,從學者角度分享了他們的看法。

現在網上有各種版本的《論語》注本,要下載到電子版變成了十分便利的事情。
互聯網帶來的好處不言而喻
汪湧豪和傅傑都不算是特別典型的互聯網用戶,但互聯網對傳統文化、學術研究的改變也不可避免地浸透到他們的研究和生活之中。
傅傑認為“互聯網給我們帶來了好處是不言而喻的”。他從學生、學者和普通讀書人三個角度分享了自己體會到的這種好處。
首先,傅傑覺得,互聯網的普及給學生找書提供了極大便利。傅傑在複旦大學有一門開了多年的課程:中文系的必修課《論語精讀》。後來又開了一門選修課:錢鍾書的《管錐編》精讀。
“我剛開始上《論語精讀》的時候得提前半年通知書店,下個學期我要開《論語精讀》了,如果有一百個學生,就讓他們進一百本楊伯峻《論語譯注》。那時候國學不像今天這麼熱,《論語譯注》也不是經常印的,書要買不到,圖書館幾本很快就借完,其他的學生就要抓耳撓腮想各種各樣的辦法。”
《管錐篇》更是如此,精讀課涉及的文本並不多,但《管錐篇》卻是一部一百多萬字的大部頭,要學生每買一本很貴,但不買又無法正常開課。
而現在網上有各種版本的《論語》注本,要下載到電子版變成了十分便利的事情。“現在完全不存在之前的問題,我還要告誡學生,一開始讀《論語》的時候不要目迷五色,盯住一本譯注書就好。”
從學者角度,傅傑更能體會互聯網帶來的查閱資料方面的便利,他戲稱為“從前像騎單車,有了互聯網像坐高鐵”。
他舉了《四庫全書》的例子。這套大型叢書是古典文學研究的必備資料,但多經焚毀散軼,曾有一段時間,能看到《四庫全書》,對學者是難得的研究條件,“著名文獻學家餘嘉錫能寫《四庫提要辯證》,首先是學問好,第二,他是故宮博物院的,能看《四庫全書》,別人有那個學問也沒那個條件做他那個東西。”
但網絡時代,四庫全書已經被電子化,不僅每個人都能輕易看到,甚至有便捷的搜索功能,可以用關鍵字從中查到自己所需內容,這給學術研究帶來了極大便利。
最後,從讀書人的角度,傅傑覺得讀書“可以任意挑選版本了”,“比如你是書法愛好者,練習寫篆字,原來中華書局本子的字很小,現在有了互聯網,版本很多,你還可以隨意放大,看不清的可以反複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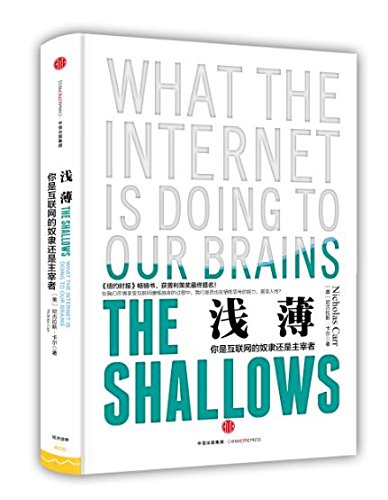
《淺薄》探討了在互聯網高度發展的今天,我們變得更淺薄還是更有深度這個問題。
沒有知識分子,只有知道分子
汪永豪承認互聯網帶給人的好處不言而喻,但從深閱讀的角度,他認為“互聯網這個東西很壞”。
隨著移動互聯網的普及,抱著手機刷屏已經成了年輕人主要的閱讀方式,碎片化閱讀取代嚴肅閱讀成為主流。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公布的2016年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人均讀書量7.86本,比前幾年略有提高。
“但我想,扣除心靈雞湯、營銷文字、成功學,每個人一年讀多少書,大家最清楚。”互聯網發達以後,如今手機閱讀超過60%,數字化閱讀接近70%,而紙面閱讀只剩下40%。汪永豪說,移動閱讀造成泛濫閱讀、輕閱讀的狀況,是每個人都體會到的。汪永豪說。
他特意提出美國記者尼古拉斯·卡爾《淺薄》書中的觀點:互聯網對人毒化是根本性的。
“本來你在內容裏面潛水,你深深地進入到文本當中,你與它共呼吸、同命運,又深深地感動。現在你只是在字面上滑行,根本進不去。互聯網改變了你的記憶程序,改變了你的神經線路,以至於你覺得再看《追憶似水年華》太長,再看《戰爭與和平》太不能接受了。”
汪永豪認為,人在讀書中研究自主獲得的記憶是人腦的“原始硬盤”,但現在大家都不去調動自己的原始硬盤,而是習慣了“內事不決問度娘,外事不決問Google”。這樣獲得的知識大體不錯,但都只是皮毛,都是訊息。
“訊息要經過整理才能成為知識,知識經過反思、解構才能成為思想。互聯網為什麼淺薄,就是因為它至多提供給你一點知識,它毫無思想,所以我們這個時代產生了很多‘知道分子’,卻沒有‘知識分子’。”

錢鍾書在《宋詞選注》裏考證“春風又綠江南岸”,提到唐人早就把“綠”詞做動詞用,並舉了四個例子說明。“但是有人從互聯網一查,輕易挑出十幾個例子,比錢先生要多得多。”
要警惕互聯網帶來的功利性學術思維
任何新興事物的產生都是一把雙刃劍。互聯網這樣對人們現實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事物更是如此。
傅傑也承認,從內心深處來講,互聯網從查閱資料這些工具性的方面,給學者研究帶來的裨益極大,但與此同時,“現在佔據的材料越來越多,但消化的功夫、融會貫通的功夫勢必越來越少。”
“古人是抄書慢慢變成讀書。” 傅傑時常提醒學生,出聲地讀十遍《史記》,和看十遍《史記》,效果完全不同,“有了朗讀基礎,一般標點不會標錯,因為基本的語感就在那裏。我的老師這一輩一再告誡,你得讀,一定得出聲地讀,慢慢我們就變成查,從背、抄到讀、看,但慢慢就是互聯網上查了,現在我們連查都不查了,現在聽了。”
這樣的“輕閱讀”一定程度上也帶動了現在的“國學熱”。但傅傑覺得這樣“大家都談點國學”的狀況是很功利的,很多人並不一定懂《論語》《孟子》,甚至根本沒有看過原著,但談一點似是而非的國學卻很有用,“在飯桌上你就可以談老子怎麼說,孔子怎麼說。”
“這種心態和這種形式上,我覺得互聯網都給我們帶了根本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從一個傳統讀書人的角度來說是萬劫不複的。”
在學術圈,也不乏這種互聯網閱讀帶來的功利性閱讀。錢鍾書在《宋詞選注》裏考證“春風又綠江南岸”,提到唐人早就把“綠”詞做動詞用,並舉了四個例子說明。
“一般我們研究宋詩都沒看那麼多,覺得太佩服了,但是有人從互聯網一查,輕易挑出十幾個例子,比錢先生要多得多。互聯網的好處是這樣的,一是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更豐富的材料,二是甚至可以糾正前人的錯誤,第三個壞處有的時候會帶來現代學者的‘虛教’。”
傅傑感慨,現在已經有人提出,現在的曆史學家,通過互聯網掌握的史料可以是呂思勉、陳寅恪這些曆史學家的一百倍。“問題是這一百倍你做出來東西是什麼樣子的?在這種情況尤其要預防虛教,另外在這種虛教的互聯網帶來的便利之下,學問變得越來越不值錢,因為出書太容易了。”
他舉例說以前的學者如鄧廣銘做辛棄疾研究,用了一輩子時間,先編年譜,再注他的詞,一首一首考證清楚。而現在的年輕學者,選一個比辛棄疾還著名的宋代人集子,比靠著互聯網馬上有注,一注出來以後馬上就出書。
“但鄧先生辛棄疾的注,很多都是我不知道的地方。現在學者注出來我都知道,或者是我查得到的。我不知道的,想知道一下的,他不注,因為他也查不到。”
傅傑覺得,這就是互聯網便利條件下帶來的極大弊端,學者更追求著作傍身,靠互聯網材料的便利堆積出書,而忽略了真正的學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學問越來越不值錢,“推而廣之,關於曆史、文學、哲學的很多論著都存在這個問題,所以書越來越多、越來越厚,但書讀起來的味道越來越差。都是不需要讀的,最值得讀的還有陳寅恪的書、錢穆的書、錢鍾書的書。”
傅傑說,自己和汪永豪還算是從小認真讀書讀上來的一輩人,而互聯網帶來的變化一日千裏,“20年前根本想不到世界會是今天這個樣子”,“我從自己的角度,20年後再發展下去,將會對傳統學術、傳統讀書人的心態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我其實是很悲觀的,甚至不敢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