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9日至8月20日,应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儒学院之邀,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语言文化学院教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为复旦哲学学院FIST课程“宋明理学系列专题研究”作了题为《南宋道学的演变》的讲座。在两天的授课里,田浩澄清了南宋道学的概念、梳理其发展脉络,并阐释了南宋道学的当今意义。以下文字根据课程录音整理而来,经田浩教授审定后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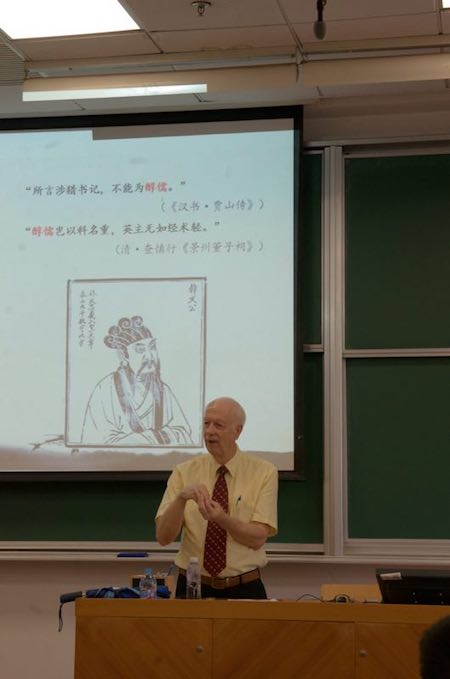
1.道学
在涉及南宋道学的概念时,东西方常用“理学”和Neo-Confucianism这两个词,但在使用时存在争议。中国人通常认为,Neo-Confucianism是“理学”的英译,而有些西方人认为,“新儒学”是中国人对Neo-Confucianism的翻译。例如,谢康伦(Conrad M. Schirokauer)教授认为Neo-Confucianism是一个西方词汇,在中文里并没有本义,它与理学没有关系,不能等同于理学;中国学者知道Neo-Confucianism和理学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发明了一个词“新儒学”来翻译Neo-Confucianism。虽然他的看法有问题,但还是值得我们注意。
理学与Neo-Confucianism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西方学者普遍使用Neo-Confucianism这个词,但在上世纪80年代,我发现他们在使用这个词时,所表达的内容并不相同。比如,冉云华教授在1980年代末写了一篇文章,认为金朝的儒学文化都是Neo-Confucianism,而陈荣捷教授的结论则完全相反,他认为金朝没有Neo-Confucianism。我在1992年Philosophy East and West上发表的“A New Direction in Confucian Scholarship: Approaches to Examin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Neo-Confucianism and Tao-hsueh(道学)”提到这个相反的结论。但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也写为狄培理William Theodore de Bary)教授认为,二者的区别是,陈荣捷考察的是早期的儒学,此时Neo-Confucianism还未完成,而冉云华则是考察儒学发展的成果,两人考察的阶段不同,两者之间并没有冲突。三位前辈学者(包括狄培理)的学问当然比我这个后学好,不过,陈荣捷与冉云华两位教授讨论的时代、范畴和对象都是一样的,结论却有矛盾,是因为他们对Neo-Confucianism的定义完全不同。
在陈荣捷先生看来,Neo-Confucianism(或者说他的“新儒学”)基本上是指从二程到朱熹时代的学说。他认为,宋代其他儒家学派和Neo-Confucianism没有太大的关系。所以,在《中国哲学文献选编》(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里,陈荣捷先生介绍宋代哲学,只讨论北宋五子和朱熹,在朱熹之前只给陆九渊一章稍作介绍,其后即为王阳明,中间没有讨论其他的哲学家,而且朱熹同时代的大儒只有张栻、吕祖谦等值得稍微提一下,所以陈荣捷先生提到的“Neo-Confucianism”范围很窄。但是,冉云华先生的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其意,可以说Neo-Confucianism就是宋学,几乎包括了宋代所有的儒家思想。这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在同一范畴下,讨论的内容却不同,使我们很难深入了解宋代儒家思想的演变,因此,最好用宋人所使用的范畴和术语来考察。我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已经开始讨论道学。道学是宋学里一个特别的派别。在宋代,“道学”比“理学”的使用要多,而且它的内涵与宋代的社会政治有直接关系,假如要了解儒家思想在宋代的巨大演变,最好就使用“道学”这个术语。另一方面,我认为无论使用哪个术语:理学、新儒学或道学,等等,都要阐明其内涵,以及在这些提法下,包括哪些思想家、不包括哪些同时代的哲学家。
陈荣捷先生的说法受到《宋史·道学传》的影响,而这本书则受到朱熹的影响。《宋史·道学传》主要包括从北宋五子——周敦颐、张载、邵雍、二程,到朱熹,以及他们的一些门人,这些人属于道学。其他的宋儒均未被列入。道学具有特别的地位,当然与1241年南宋将朱熹的学说当作教育思想的主导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有关。
朱熹强调“醇儒”。历史上也有过醇儒这个词,但朱熹的用法有他的特色,他以自己的立场阐释儒家传统,要接受朱熹的立场,方为醇儒。比方说,朱熹在和陈亮辩论时,就要求陈亮变成醇儒。朱熹另一个很有名的说法是“道统”,更有说服力。从古代的圣贤,一直到孔孟,传承了一个道统,然后到了北宋,周敦颐和二程接续道统,再传到朱熹。朱熹把自己放在“道”的传续中间,而且变成“道”的标准。“道学”的范畴在朱熹这里有了很大的改变。
在北宋末南宋初,道学家们主要关心社会政治改革方面。一批人具有共同的社会政治目的,所以可以合作,推行更好的政治,这些人都是儒生,但他们的思想观点有所不同,也有一点复杂。他们可以包容或接受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对“心”的解释,但他们更关注社会政治合作。因为社会政治问题更加重要,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一定要通力合作。他们以道学为一个社会政治文化的圈子,但因为搞政治文化,到了吕祖谦、朱熹的时候,他们把道学当作一个政治的党派。但朱熹也有更强的使命感,他甚至有更高的要求,要“醇儒”,要诸儒的思想和他的基本一致。后来到1241年,宋理宗把朱熹、二程等供在孔庙,利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育的标准,把王安石从孔庙驱逐出去。所以,到那个时候,道学的演变更为明显,可以把思想、历史与政治结合起来讨论,强调这一演变。
2.南宋道学演变的第一阶段:胡宏(1105-1161)与湖湘学派、张九成(1092-1159)与浙东学派
胡宏很注重政治和国家的事情,他的一些著作,比如《知言》,就强调天下政治的问题。他在南宋初期,特别是岳麓书院有很大的影响力,而且代表了那个时候道学的特色,即特别关心政治和国家的事情。虽然他们的哲学立场被朱熹和后人严厉批评,但胡宏和张九成无疑是南宋早期最主要的道学思想家。
张九成更注重“心”的问题,更注意发展心学,而且他把“理”和“心”联系起来。他在南宋初期具有重要性,一个主要的依据就是《诸儒鸣道集》。《诸儒鸣道集》是南宋早期的重要著作,它不仅包括张载、周敦颐、二程等人的议论著述,还包括了张九成的,这是最主要的部分。《诸儒鸣道集》大概是张九成的学生编写的,他们将张九成放在最后,意味着道学团体的思想到了张九成这里,可被视为那个时候的代表。《诸儒鸣道集》更强调心学,这和朱熹的立场有很大区别。所以朱熹后来就批评张九成、胡宏,特别是张九成。朱熹认为,张九成的思想和佛教关系太过密切,特别攻击了他的心学。所以朱熹之后,张九成基本上不被放在道学的范畴内,他的著作基本上在佛教材料中保存下来。
3.张栻(1133-1180)、吕祖谦(1137-1181)
胡宏的学生张栻,是四川人,他父亲送他去岳麓书院跟胡宏学习。后来张栻成为了岳麓书院的主要老师,影响很大。他和朱熹、吕祖谦,并列当时最重要的三位思想家,即所谓“江南三贤”,因此,岳麓书院特别强调张栻的贡献。
他们三位在很多方面有共同立场,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讨论胡宏著作时的态度。朱熹要修改胡宏的话语、或者完全抹掉朱熹所选出来的段落。张栻虽然是胡宏的学生,但他被朱熹说服,特别是在讨论“心”的问题上,张栻就未能保留胡宏湖南道学学派的传统。所以有的朱子学者觉得,宋代湖南道学的传统基本上在张栻去世后被朱熹承接。这个说法虽然成立,可是我觉得其中有更复杂的情况。在张栻和朱熹的书信来往中表明,张栻一定有某些地方(例如强调周敦颐)影响到朱熹的思想。另外,朱熹在受到张栻的影响之后,他慢慢地怀疑张栻的立场,也怀疑二程门人的看法,对二程有一些怀疑。
朱熹通过和张栻、吕祖谦的来往,尤其是通过讨论与辩论,使得自己的立场慢慢地明确。我稍微提两个最主要的例子,第一个是《中庸》讨论“中和”的问题,“未发”、“已发”的立场。牟宗三先生写了很多关于这个题目的文章。朱熹的传统比较注重静坐修养的方法,胡宏、张栻的传统则要求在工作的时候修养,不太注重静坐的方法。朱熹到岳麓书院讨论,受到张栻影响后,注重二程的看法,就是未发是性、已发是心。朱熹逐渐觉得张栻的看法有问题,所以写了“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很清楚地强调已发、未发都是心里的。我们可以从朱熹的著作看出他的立场、以及如何改变二程门人和他自己对“中和”的概念。
第二,朱熹、张栻同时讨论《仁说》,他们都很注重“仁”的概念,而且很不满意汉儒以“爱”解释“仁”、二程以“理”解释“仁”。按照朱熹的话,他评价张栻修养好、为人特别好,原因是张栻早期和胡宏修习,讨论仁义之旨,而且写了《希颜录》。同时,朱熹还很关心,包括二程看法在内的传统立场还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所以他觉得,假如我们恢复或者创新一个传统,就必须有一个关于仁的新理解。
在朱熹、张栻的书信来往中,有两个《仁说》,最重要的部分,是以仁为“爱之理、心之德”,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中对仁的最完整定义,影响力很大。有的人,包括陈荣捷先生认为,两个《仁说》都是朱熹写的。但是,朱熹在1184年致信给吕祖谦的弟弟说,“心之德”原本是张栻要利用来改变朱熹的说法,所以“心之德”就是张栻的说法而非朱熹的。朱熹原来反对心之德的说法,可是很有趣的是,朱熹自己后来还是利用了“心之德”给“仁”下了一个新的定义。这是很重要的依据,它让我们看到张栻对朱熹的影响很大,1180年张栻去世,他的家人就请朱熹将张栻的著作编纂成文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朱熹以前强调张栻的著作,但讨论“仁”的著作《希颜录》,朱熹并没有保存下来;张栻给朱熹的某些信中关于“仁”的讨论,朱熹也没有收录在文集之内。朱熹利用编撰张栻文集的机会宣扬自己的立场,这就让读者更接受朱熹的立场,所以后代比较难看出张栻原来的思想、著作。所幸当代学者(尤其是陈来教授)找到了一些张栻的其他著作,例如陈来发现张栻论周敦颐的材料。
我以吕祖谦作为第二发展阶段的主要代表,以此和第三阶段作出大的区别,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因为朱熹、张栻、吕祖谦之间的来往,是很平等的。虽然这两个人比朱熹年轻,通过进士考试的时间也比朱熹要晚,可是朱熹特别尊敬二者,尤其是吕祖谦。朱熹和他们讨论时,他们可以直接批评朱熹做人方面的道德问题,朱熹也承认自己的缺点,比如承认他的脾气很急躁。吕祖谦的修养非常好,与人交往很和气。朱熹承认吕祖谦的贡献,例如,吕祖谦替朱熹撰写了《白鹿洞书院记》, 而且他们合编了《近思录》。虽然有一些传统学者不知道吕祖谦对《近思录》的贡献,可是按照朱熹自己的话,《近思录》最终成型是受了吕祖谦的立场影响,所以吕祖谦很有影响力。
我想稍微介绍德国的学者马愷之(Kai Marchal),现在任台北政治大学哲学系副教授。他有一本专门讨论吕祖谦的著作,(我的《朱熹的思维世界》只有两章讨论吕祖谦),讨论吕祖谦和朱熹政治文化立场中的共同点与相区别的地方。吕祖谦比较肯定王安石的改革,两人都注重孟子,特别是孟子利用五经的一段话说老百姓希望雨先下于“公”之地,而编出来“井田制度”的理想。张载、胡宏、张栻要恢复孟子所提的“井田制度”,因为按照这个理想,每一个农家有足够的田地可以养家。虽然吕祖谦强调井田制度的原则,毕竟他还是历史学家,所以他很清楚宋代的情况,特别是唐末之后土地兼并严重,没有办法完全恢复孟子的复古理想,可是,他仍然希望宋代政府利用井田制的原则来设立某些新的政策,从抑制土地兼并开始。
更重要的是,马恺之举例说明吕祖谦将自我修身与历史中的真实和他所处的社会结合在一起。关于吕祖谦的许多研究,关注探讨自我修身和政治权利之间的关系。为了尽到士大夫的责任进而影响国家统治,他试图说服皇帝来恢复隋唐传统的官僚集团对决策及皇帝行为的制衡。但朱熹试图说服皇帝自我修养之后自愿地限制自己的权力,吕祖谦则认识到通过制度来限制皇权的必要性。皇权倾向于朱熹而非吕祖谦的一大原因,在于与朱熹主张关注皇帝内心道德的转变,与此相比,吕祖谦通过制度来限制皇帝行为的方法看起来不合礼法并具有敌意。因此,“与其他儒者思想家相比,吕祖谦较早地意识到‘道德的内化’的政治结果。”
4.陈亮(1143-1194)、陆九渊(陆象山,1139-1193)
吕祖谦是陈亮的朋友,他也影响到陈亮的思想。朱熹对陈亮不满的一个原因是,吕祖谦死了之后,陈亮强调他自己和吕祖谦的关系,朱熹批评他利用和吕祖谦的关系来提高自己。客观而言,朱熹也有利用吕祖谦来提高自己的权威,比方说在《祭吕伯恭著作文》中,朱熹强调吕祖谦当过道学领导的时候,就趁机提出他自己必须继承吕祖谦的道学领袖地位。在朱熹看来,陈亮受吕祖谦影响,甚至于把吕祖谦强调的经世致用发展到了一个极点,变得更危险。陈亮对“权”这个概念的理解是个尤为明显的例子。“权”字有不同的意思:英文的范围包括situational weighing, moral discretion, and/or expediency。朱熹特别强调“权”和“经”的规定,“经”是完全按照道德标准的看法或行为;在《论语》里,孔子说只有很少的时候有人可以跟着他做“权”,说明在特别的情况时,很难辩出道德或者实行道德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所以这是比较难的道德问题。在这方面,儒家思想比很多西方思想更有趣。西方思想要分清对错、真假等等,分得非常清楚。中国儒家传统的好处就是比较注重较为复杂的道德问题。从孔子开始,讨论一些具体的问题,如孝忠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很值得从中国广阔的历史来讨论“权”和“经”的关系。孔孟很清楚,假如父亲做坏事,你就要保护父亲。后来随着皇权增大,皇帝更需要强调“忠”,有了政府的立场,重视忠更是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假如你不忠,则完全无法尽孝道。关于这个问题,朱熹很清楚他的看法,他强调必须通过“经”的道德标准来做事,只有圣人可以做“权”。按照陈亮的立场,“权”也在道德里面,包括王道、霸道和公、私与义、利,他要想办法将它们结合起来,不是像朱熹那样过于清楚地区别或对立道德。管仲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孔子在《论语》里赞美管仲,认为管仲集合诸侯、抵抗夷狄、保护中华文明。所以孔子这样评说管仲的贡献:“如其仁。”孔子歌颂管仲给后代儒者造成很大的困难,后代儒者对管仲有更严厉的批评,他们不接受管仲有“仁”的看法,而是批评霸道、批评管仲,所以他们觉得孔子肯定不是赞美管仲具有“仁”的道德,这不可能,他们认为孔子的意思是管仲和仁完全没有关系。朱熹批评陈亮的某些类似的概念,把结果和道德混在一起,认为陈亮的焦点就是功利。因此,我觉得要解释陈亮思想的基本概念,我的一本书《功利主义的儒家》就是讨论陈亮向朱熹的挑战。当然陈亮的“功利”是一种儒家的功利,跟西方功利主义有其区别。
最后介绍对陆九渊的一些看法。陈亮和陆九渊对朱熹的作用,来自于他们对朱熹的挑战,也给朱熹不同的机会把自己的立场讲得更清楚。朱熹想办法对抗他们的说法,这就和对待张栻、吕祖谦的情况相反。朱熹利用张栻与吕祖谦的某些看法来树立自己的学说,可是和陈亮、陆九渊的来往则是观点上的对抗,促使他进行哲学系统化。传统的“朱陆一同”观点注重他们的主要区别是:道问学、尊德性,还有心即理、性即理的范畴。但是就朱、陆二人的书信往来看,他们并不辩论那些范畴。相反,他们论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朱熹利用“无极而太极”的概念来与二程的“理”相论,形成系统的哲学。这也是朱熹受张栻影响的例子,因为张栻早期十分强调周敦颐的重要性。陆九渊批评周敦颐的“无极”范畴,也批评朱熹利用周敦颐“无极而太极”,说“无极”是北宋初期陈抟提出的概念,因此“无极而太极”是受到道教影响而形成的。按照陆九渊的说法,周敦颐受到道教的影响,所以朱熹不是醇儒。孔子在《易经》中强调太极,太极足够,不必再放无极在太极上面,这是多余的,这是把道教思想放在儒家思想之上。朱熹说他看过《国史》把周敦颐的话当作“从无极而为太极”。朱熹自己承认,假如“从无极而为太极”是周敦颐的原话,那么陆九渊的立场就是对的:就是说,周敦颐把“无极、太极”分为两个东西,而非一个。但朱熹不接受这本《国史》引用的话。
第二,朱熹平常批评陆九渊不够尊敬儒家经典,而且这个批评影响后代学者对陆九渊的看法,但是朱熹写信给陆九渊的时候,他批判的对象不同。一方面,他批评陆九渊过多提出利用四书五经的话,而且把四书五经的话解释得太肤浅,只解释字面意思,不够了解更深的哲学层次;另一方面,朱熹觉得陆九渊并未就五经探讨他心里面的话。可是陆九渊批评朱熹,问他所谓的“理”是什么?如何知道这不是朱熹自己编出来的、自己的概念而已?可能朱熹的“理”跟现实情况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朱熹自己的意见。从吕祖谦、陆九渊的立场来看,朱熹太理想化,不够客观。关于陆九渊,我认为我们应该讨论、研究、再讨论之后,才有客观的结果。这和一般学者考察陆九渊的方法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最后,我们做一个结论,上述讨论宋代道学的演变,特别是强调与朱熹同时代的人,这样的讨论和我们当代的研究、和你们作为研究生的情况有什么关系?1968年,我第一个星期当哈佛大学研究生的时候,研究院院长告诉我们:“不让别人知道自己独创性的思想概念,这是很笨的办法;最好把想法提出来讨论。概念无论被肯定或否定,都会有进步和发展。所以和大家讨论、合作才能有所进步。”我们也可以说,聪明不只是依靠个人而已,而且创造力也不是一个人自己的天才而已。创造性实在是依靠一群人一起讨论合作而形成的。朱熹的创造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依靠同时代的人们,把他人的概念和结论拿来变成自己的概念,而且他与他们的观点对抗,这也帮助他把自己的概念弄得更清楚。不要太注意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的好处,也希望你们参加对话与讨论,参加一些讨论,你可以有所贡献,把研究结果更推进一步。我们研究古代哲学也可以对我们了解当代的一些具体问题有所帮助。(作者:马雨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