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期由电影引发的讨论空前热闹,多部春节档上映的影片为人们持续、热烈的争论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看电影是一件轻松有趣的事,它让我们告别沉重现实,于生活的夹缝中得到片刻休息。得益于成长背景差异,每个人的观影角度和口味如此不同。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人博在《业余者说》中以电影为契机,探讨了“表达的艺术”以及“反东方主义”,经出版社授权节选刊发,以飨读者。
表达的分寸——面向私己和公众
在阅读您的散文集《孤独的敏感者》时,我产生很多想法,同时也产生很多疑惑;这些想法和疑惑很多都和“表达”这个问题相关。或许,我们可以把电影、音乐、小说和学术都看作某种程度上的“表达方式”,进而把艺术家、小说家和学者都看作“表达者”。如果这种看法基本靠谱的话,我想从“表达”这个话题入手,来向您求教我心中的疑惑。
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前提,恐怕是要讲明自己。你知道,我的专业是法学,谈论法学以外的任何问题从专业角度说都是外行。如果这个集子设定的主题是“听外行咋说”,这些话题是可以聊一聊的。对我而言,聊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之所以“敢”聊,主要是缘于好奇心。
除此之外,作为一个不务正业的“闲逛者”,我对这些东西或多或少也都曾涉猎、思考过,体现的是“业余”的价值。对内行人,我总有一个想法:一个电影人不能只听专业影评家的理论和观点,最好也能听听观众对作品的感受,一部片子为啥“叫好不叫座”,说到底,那是因为观众不买你和专家的账。在观众看来,那样的电影不值得掏钱、花时间。就我所知,观众不会先去读电影理论然后再进电影院。
事实上,影评家越是把一部电影说得天花乱坠,就越会败坏观众观赏的胃口。当然,这并不是说“叫好不叫座”的影片都不是好作品,问题是你拍出的影片总得有人看。电影家可以为自己拍片,但绝不会设定只是自己一人观赏。反过来讲也一样,我不会把电影中涉及的法律问题看成是法学专家的观点或意见,但一部好的电影作品也会给我们这些以法学为业的人以深刻的启发。譬如《烈日灼心》里有关法律的那段台词堪称经典:
“我认为法律是人类发明过的最好的东西。你知道什么是人吗?在我眼里,人是神性和动物性的总和。就是他有你想象不到的好,更有你想象不到的恶。没有对错,这就是人。所以说,法律特别可爱:它不管你好到哪儿,就限制你不能恶到没边儿;它清楚每个人心里都有那么点脏事儿,想想可以,但做出来不行。法律更像人性的低保,是一种强制性的修养;它不像宗教要求你眼高手低,就踏踏实实地告诉你至少应该是什么样;[它]又讲人性,又残酷无情。”
——这几句话胜过一篇出色的专业法学论文,这话并不过分。

曹保平执导,改编自须一瓜的长篇小说《太阳黑子》,2015年上映。
从广义的角度上说,人类的分工主要有两类,即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当然,在中国宪法里还出现了“建设者”这个概念,除去中国特定的政治语境之外,它更接近于“脑力劳动者”:经商者,主要靠脑袋而不是靠腿,“财大气粗”说的是心态而不是身体;企业家,一般不会自己搬运产品,而是一个对搬运者发号施令的人;管理者,运用的是技艺而不是力气。
学者、艺术家说到底都是靠脑子吃饭的人。你总不能把弹钢琴看作是体力活。他们是一类人,面对的是一个共同的对象: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我们的生活本身。小说家喜欢把他的对象看成是一种“故事结构”,通过叙事来解释和表达他对世界和生活的见解。音乐家主要靠的是耳朵,他习惯于把生活和世界想象为“声音”:我们的生活、世界乃至整个宇宙都相互关联,存在着一种隐秘的和谐关系,这种关系会带来动静;把那些在我们看来杂七杂八的声响组合为有规律的音符、旋律、曲调便是他们的工作。电影家擅长的是把生活和世界转换为影像,一个带有色彩、声音、图像、故事的镜像结构。“摄影机”既是电影家探索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生活、生命的工具,又是他表达问题的主要方式,生活、生命的意义通过对胶片的剪辑、拼接而显现出来。学者的任务则主要是运用自己的“理性”在生活与世界里发现原理、规则、规律、公式、模型,推理论证是其依赖的主要路径。
生活与世界既带有空间性,又带有时间性;既有色彩,又有声音;既枯燥无聊,又有趣味。那些被称作“脑力劳动者”的人,其主要使命就是把生活与世界的某个切面作为自己的对象,寻找一种适当的表达方式去揭示其中的秘密和意义,并从中体验这种表达的感受,以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或价值。脑力劳动者,即一群依赖“表达”而生活的人。
中国的“东方主义”表达
我们先从电影说起吧。您似乎系统地关注过张艺谋的电影,尤其是他的早期电影,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这些电影,据说被认为是有力地塑造了“中国”的形象。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张艺谋通过电影这种方式“表达”了中国,哪怕这种“中国”只是他的一家之言。一些文艺批评家认为,张艺谋早期电影其实比较“媚俗”,媚“西方”之“俗”。他采用了西方人的视角,所表达的“中国”其实只是一个“伪中国”。这种看法让我想起萨义德的“东方学”,“东方学”致力于反思和揭示西方人如何想象“东方”这个问题。在您看来,萨义德的“东方学”,对于我们认识“中国”、表达“中国”有什么意义?您又是怎么看待张艺谋电影里的“中国”的?
首先是喜欢看电影。这可能是小时候养成的喜好:那时候农村的生活比较单调乏味,孩子们除了打架斗殴也就盼着看电影。那时的电影是露天的,各个村庄要轮流放映。大的村子场次往往要多一些,如果哪个村子的人与放映员认识也会得到多放的好处。我们的村子小又没名气,所以常常要跑到别的村子,因“占地方”被别村的孩子们揍得鼻青脸肿也是常事,那似乎是“爱好培养”应交付的成本。除此之外,银幕反面对外村的孩子来讲,也是最适合的观看地点和方式。
在农村,放映的片子转来转去也就那几部,所以有些片子看了不下百遍并不是吹牛,有些电影场景成了孩子们戏仿的对象,有些电影台词也像玩具被他们牢牢地攥在手里。
现在仍然喜欢电影。坚持这种为数不多的爱好,既与早年的经历和记忆有关,也与自己的生活态度和理解问题的方式相近。对于一个不喜欢热闹的人而言,其最好的方式就是把自己置于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守着电脑屏幕——用现在的话说,叫“宅”。电影画框里的画面、场景以及在此展开的曲折故事和人生,除了具有询唤(interpellation)功能之外,对观看者的心理也有平复作用。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需要的是想象力,它所倾心的是事物的相似性;学术作为理性形式,关注的则是事物的差异性。在我看来,一种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既需要想象力,也需要判断力,电影无疑是前者的最好训练方式。而关注张艺谋的电影,原因并不复杂。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讲,张艺谋的名气大,是“第五代电影”的代表人物,而他的电影也常常会引起争议,容易受到各方关注。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电影总能引起电影之外的某些思考。他的早期作品似乎在讲述与我们这些法学中人共同的对象和主题。他用镜头表述他的文本,而法学家则用电脑敲出自己的文字,而那个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文本世界则是双方共享的。他的一部《秋菊打官司》会成为中国法学者《送法下乡》的主要“参考书”,“秋菊问题”会形成中国法学的命题之一也就在情理之中,并非意料之外。

《秋菊打官司》海报
我不打算详细评述张艺谋电影。只要搜索相关文献资料,你就会发现张艺谋电影存在于两个地方:它曾被形形色色的人研究和批判,形成了无数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似乎比任何一个中国电影人的都多;在当下中国电影的另一角,张艺谋似乎不再被人问津,观众的热情好像转移到他的家庭。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自己再在此大嘴咧咧,的确不是一个好主意。我选择的策略是,主要对张艺谋电影研究的方法谈点自己的看法;其次,为了“证明”这种看法,也捎带扯上他的电影。当然,话题都得围绕“表达技艺”进行。
在张艺谋电影研究中,“反东方主义”是一种影响较大的方法论。它主要被应用于张艺谋的早期作品中,如《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这也是“媚俗”“伪中国”这些词语的来源。
这里的问题有两个:中国的电影人如何向西方传达自己的电影?西方的同行和观众又如何能接受来自于中国的电影?这是其一;其二,对西方观众所接受的中国电影中的“中国历史与文化”,中国的知识人又如何认知?
有一个事实不会引起太多争议:中国的电影不能只拍给中国人看,应该拥有更多的观众,特别是西方观众。中国电影如何能把西方观众拖进电影院,或者首先为西方的电影人所接受,是问题的焦点。这里的“接受”一词的含义极其简单:他们爱看。那什么样的中国电影西方电影人感兴趣,观众爱看?“爱看”并不是一个暧昧的词。喝倒彩并不是为了把人捧起来,而是要把他摔在地上。看别人出丑,这不是观赏,而是起哄。电影无论带有多少商业气味,它本质上还是一门审美艺术。所以,首先不能用“出丑”来界定西方电影人和观众对中国电影的兴趣。
这里,确实存在一个观看的视角问题。这个“视角”既是审美的,也是文化的。审美视角容易理解,眼睛不同,口味自然不同(当然,审美与文化不能截然分开,文化参与了审美方式的形成也是事实)。文化视角则要复杂得多,特别是在中西之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始终是个既说不完、也不易说清的问题。“先进-落后”二元结构虽然遭到普遍质疑,但它的有效性并未完全丧失。“(西方)先进-(中国)落后”既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基本范式,也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包括电影。事实上,西方不仅发明了电影,而且也创造了电影的诸多艺术流派。它的电影技术被全世界学习和应用。好莱坞电影产业仍是电影工业的典范机制。“美国电影走向世界”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同样一句话,其语义一样而意义却存在极大差异:前者意味着要赚全世界的钱;后者则希望世人(西方)能认识自己。

1993年拍摄电影《活着》时的张艺谋与巩俐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先进-落后”仍未完全失效的范式下,张艺谋电影为西方的电影人(包括西方观众)所接受,其接受的机制是否就是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的?
要知道,东方主义作为一种方法论,就像是个同一型号的筛子,用它筛选不同的非西方国家,符合筛孔的全都漏下去,上面剩下多少,并不是筛选工作所关心的,它只注重筛。反东方主义与其说是一种方法论,莫如说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也是由西方建构,由“东方”书写。它的根本缺陷不在于热心解构,而是有意遗漏了那些原本就存在于不同国家与民族中的文化性。西方电影人和它的观众能够同时接受伊朗和中国电影未必就是出自东方主义的同一种机制,也可能是因为电影映现出的两个国家不同的文化镜像打动了异域的同类,因为人除去差异,仍能剩下类似的情感共鸣。
进而言之,中国观众(包括本人)爱看伊朗电影也并非因为同属于东方主义语境下的受害者,与伊朗人一起抱团取暖——电影可能表达政治问题,但它毕竟不是政治——而是因为伊朗有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马吉德·马基迪、贾法·帕纳西、巴曼法·玛纳拉等杰出的导演以及他们创作的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作品。
另一个例子是日本。日本的电影大家如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是世界公认的著名电影导演,其作品也受西方世界观众的欢迎,如《东京物语》《罗生门》等。如果把作为现代主义副产品的日本电影以及在西方世界的声誉,归结为与中国相同的东方主义语境,那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日本自身已脱离“东方”,成为先进“西方”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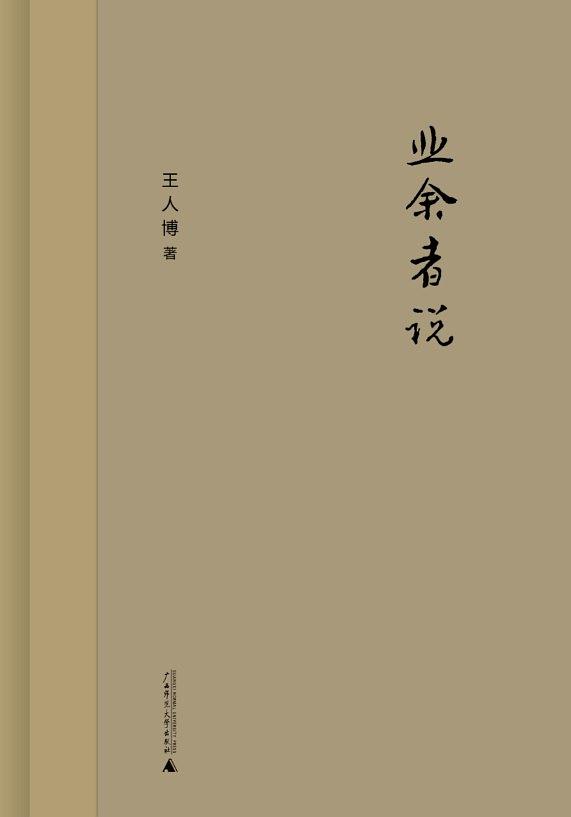
《业余者说》
王人博 著
广西师大出版社·新民说 2018-07
……………………
来源:新民说iHuman
原标题:王人博:中国的电影不能只拍给中国人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