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瑟非常能体现中世纪英雄人物的特点,他们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虚幻与历史之间,早已成了传说中的人物,就像那些历史上真正存在的人物,他们也已经远离历史而成为传说,与意象世界中的虚构英雄结合起来。在这方面,我们将一睹中世纪其中两大英雄人物平行而又交叉的命运演变——介于历史与传说之间的亚瑟和查理曼。
亚瑟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9世纪初编年史家内尼厄斯编写的《不列颠人的历史》(Historia Britonum)一书中。据书中记载,有一位叫亚瑟的人助不列颠国王抵抗入侵大不列颠的撒克逊人。作为战场领袖,他杀死了将近960 个敌人。因此亚瑟主要是作为功勋卓著的战士、不列颠人的保护者走进了历史。在中世纪盛期,凯尔特人的口头文学中就出现了他的影子,尤其是威尔士散文故事集《马比诺吉昂》(Mabinogion)讲述了这位英雄的早期时光。有人曾经将亚瑟和其他文化中的英雄人物相对比,尤其是印欧语族具有三种社会功能的文化、欧洲甚至日耳曼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但是,不管英雄亚瑟的本质是什么,西方中世纪创造、流传给我们的是一位与不列颠民族意识紧密相关的凯尔特英雄。
亚瑟真正诞生于一本据说作者是威尔士的编年史家蒙茅斯的杰弗里的作品中。杰弗里是牛津的一位议事司铎,于1135 到1138 年编撰了《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 Regum Britanniae)一书。杰弗里讲述了自布鲁图斯率领罗马人给不列颠人带来最初的文明之后不列颠诸王的历史。作为罗马人和蛮族人的混血后代,不列颠人自此便被一连串的国王统治着。其中最后一个国王,尤瑟王(尤瑟·潘德拉贡),在法师梅林的魔法的帮助下使他爱慕的女人伊格赖因受孕,她生下一个儿子,这便是亚瑟。
亚瑟15 岁继位为王,在对罗马人以及西欧各民族的战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他杀死圣米歇尔山周围散布的恐怖的巨人之后,征服了整个大不列颠、北部群岛,疆域直达比利牛斯山。他的外甥莫德雷德抢走了他的妻子和王国。亚瑟从战场归来将其杀死,但是自己也受到了致命的一击,随后他被送到威尔士附近的阿瓦隆岛。在那里,他要么是去世了,要么等待着力量恢复,以重新夺回他的王国和统治权。就这样,亚瑟很快成为一系列代表中世纪丰富而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亚瑟王传说”的中心人物。

这一文学形象中的很多基本情节都来自克雷蒂安·德·特鲁瓦于1160 至1185 年创作的故事诗和13世纪上半叶以散文形式流传的亚瑟王传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中世纪文学中创造性的想象在英雄以及奇观的塑造方面发挥了多么关键的作用。意象的历史赋予了中世纪文学在当时的文化、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至关重要的地位,更加赋予了它能够跨越世纪而长存的持久生命力。
亚瑟是我们称之为“不列颠题材”这一广阔的文学领域的中心人物。他带动了很多文学形象的诞生,或者说在他的周围集结了一系列英雄人物,其中最闪亮的是高文、兰斯洛特和珀西瓦尔。他还创建了一个在中世纪西方基督教中不多见的乌托邦式团体,即传说中的圆桌骑士团。这个团体中的成员都是英雄的典范。亚瑟作为一位战争英雄,和法师梅林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后者用他的预言和保护陪伴着亚瑟从出生到死亡的整个人生历程。
梅林是一件奇特的宝物——圣杯的构思来源,我们在本书中不对圣杯做过多的介绍,因为它实际上早已从我们的想象当中消失了。圣杯是一个有魔力的物件,是圣体盒的一种形式,对它的寻找和征服成为基督教骑士尤其是圆桌骑士团的使命。中世纪骑士的基督教化在这个神话中达到顶点。圆桌骑士团这一形象的创造同样也使我们看到英雄和奇观的世界其实隐含着中世纪社会和文化的矛盾,它象征着生活在中世纪等级森严和极不平等的社会中的人民大众对理想的平等世界的向往。

但是,在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当中,也存在着一种在贵族这一较高的社会等级中创建团体和要求举止平等的渴望。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亲吻礼就是一种姿态上的象征。圆桌骑士团除了隐喻宇宙是一个整体,即世界的整体性之外,还象征着对平等世界的憧憬,亚瑟则在其中扮演着担保人的角色,并在贵族世界中寻找其现实的化身。
但是,除了拥有战士与骑士的身份,亚瑟还是中世纪政治社会中卓越首领——国王的虚构化身。这值得我们注意,长久以来,亚瑟真正的名字是“亚瑟王”(Arthurus rex),比如我们可以在意大利南部奥特朗托大教堂(11世纪)的地面镶嵌画上看到的,而且亚瑟在欧洲颇具诗意的想象当中一直是国王的象征,他不以神秘的形式存在,却没有丧失神圣的光环。亚瑟不只是一位真实存在而又传奇的国王,他还是一位千禧年的国王。中世纪的人们普遍梦想着由信仰和美德统治世界的日子降临大地,他们期盼着由一位历史上的国王领导启示录记载的世界末日。这种想法在东方获得了巨大成功,某些“隐士埃米尔”的出现便是一例。
在西方,亚瑟的形象被许多皇帝所采用,比如腓特烈一世(绰号“红胡子”),他认为亚瑟可能并没有死,而是长眠于一个山洞中,在阿瓦隆岛上静待着自己的回归。这就是“过去和未来之王”(Rexquondam, rexque futurus)的主题。

如果说圆桌骑士团这样一个神秘的团体与亚瑟的形象紧密相连,那么有一件伟大的战士或骑士通常所共有的人格化的器物与他的名字联系得更加密切,那就是他的佩剑。亚瑟的佩剑具有魔力,只有他能够挥舞得起来,他用这把剑杀死了不计其数的敌人和怪物,尤其是巨人,最后圣剑被投入湖中也标志着他的生命和权力的终结。这把剑名为“石中剑”(Excalibur),它的消失为亚瑟之死这一段晦暗的情节画上了句号。英国著名导演约翰·保曼还在他的电影《亚瑟王神剑》中让这把剑登上银幕。我们在查理曼和罗兰的手里也能发现这样的人格化的佩剑:咎瓦尤斯、迪朗达尔。它们和石中剑都是了不起的英雄们的最好搭档。
亚瑟首先是中世纪多重价值观念结合的体现。这些观念无疑打上了基督教的深刻烙印,但首要表现的还是世俗的价值观和世俗的英雄形象。亚瑟自身表现了封建价值观两个连续的发展阶段:12 世纪的英雄主义和13 世纪的骑士风度。他是印欧传统中具备三种社会功能的国王:代表第一种功能的神圣之王,代表第二种功能的战争之王,代表第三种功能的教化之王。他为研究中世纪文学的著名的史学家埃里克·科勒所下的一个较为合理的定义做了很好的注解:“封建骑士世界的两大任务:历史的合法化与神话的创造。”
正如所有的英雄,尤其是中世纪的英雄一般,亚瑟的名字与很多地点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地点通常都是出现战役和死亡的地方。其中有重要的战事、征服及胜利发生的区域,凯尔特地区、爱尔兰、威尔士、康沃尔、阿尔莫里卡;有亚瑟诞生的地方,康沃尔地区的廷塔哲;有传说中他的宫殿所在之地,位于康沃尔和威尔士边界的卡美洛;有一些神奇的岛屿,比如阿瓦隆岛;还有位于威尔士边界的英格兰本笃会格拉斯顿伯里修道院,据说1191年在这里发现了亚瑟王和王后圭尼维尔的遗体。
但是,在远离凯尔特地区的东方,也还有一个著名的地方与等待之王——生死不明的亚瑟密切相关,这个地方就是埃特纳火山。根据13 世纪初一位英格兰人蒂尔伯里的杰维斯的一部著名的故事集,亚瑟安静地沉睡于埃特纳火山中,他或是在等待着重回人间,或是等待着升入天堂。因此亚瑟也与我称之为炼狱的诞生这个故事紧密相连,当时的人们在炼狱的入口位于爱尔兰岛还是西西里岛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这位凯尔特国王应该算是基督教国家的教义中入炼狱的第一批人了。
但是,在基督教的欧洲,从来没有全能的英雄和没有阴暗面的奇观,这个特点一直持续到今天。英雄也只是一个人,而人都是有罪的,坏人的背叛必然与封建的忠诚观形成对比。另一方面,如果说君主制的意识形态将国王塑造为一个英雄的形象,那它远没有赋予他绝对主义的特点,而文艺复兴和古典时期则更注重突出这一特点。亚瑟是一个罪人,也曾被背叛过。亚瑟克制不住情欲,与他同母异父的姐姐结合生下了莫德雷德。越是伟大的人物,越是可能犯下天大的罪恶,国王和英雄(查理曼亦如此)通常都有乱伦的行为。至于这次罪行的果实莫德雷德,则是一个叛徒,他的背叛导致亚瑟王最后死亡了。如果说亚瑟知道他的妻子圭尼维尔背叛他并和他的仆从兰斯洛特偷情,那么他自己也多次在不同的场合背叛了圭尼维尔。
蒙茅斯的杰弗里之后,亚瑟的形象不断得到巩固。首先,英格兰金雀花王朝用政策确立了他的地位。英雄形象的政治利用是历史上的常见现象之一,尤其是在中世纪、在欧洲历史中。在英格兰诸王大力宣扬亚瑟的同时,法国人和德意志人也争先恐后地在历史神话中寻找本国的精神支持,两国都不遗余力地谋求垄断查理曼。就这样,欧洲历史中出现了一对具有双重关系的组合——亚瑟王和查理曼,双方时而互补,时而对立。

查理曼,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的奠基人
亚瑟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3世纪初的西多修道会士海斯特尔巴赫的凯撒利乌斯在他的《关于神迹的对话》(Dialogus miraculorum)中写道,有一次修道院院长布道时,底下的修士都在打盹儿,这时他提高了嗓音:“听我说,我的兄弟们,听好了,我要给你们讲一个离奇的新故事:过去曾有一位国王名叫亚瑟。”一听到这句话,修士们都醒了,激动不已,全神贯注地听着。亚瑟甚至在修道院内都成了英雄。在中世纪,亚瑟形象突破贵族阶层的成功之处还体现在“亚瑟”这个名字上。由一个名和一个姓结合在一起的现代人名形式出现在13到14世纪的西方基督教世界,那时我们就已经发现“亚瑟”的存在,尤其是在市民阶层。
米歇尔·帕斯图罗曾着力研究过“亚瑟”和其他圆桌骑士团主要成员的名字的传播情况,他强调一个人的教名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人的“第一个社会记号、首要属性、主要标志”。他曾根据15 世纪末之前的约40000 个带有法国印记的传说,考察过圆桌骑士团的成员的名字出现的频次。他发现“效仿亚瑟王”在那时的城市中已经成为一个不可争辩的事实,对亚瑟的狂热甚至席卷荷兰、意大利这些地区,一直持续到16世纪中期。让我们再回到法国,这次有关亚瑟人名学的人类学考察的胜出者是特里斯坦,共计出现120次;紧接着是兰斯洛特,79次;而亚瑟接近72次,远远超出高文(46次)和珀西瓦尔(44次)。
最后,伴随着浪漫主义的到来,亚瑟迎来了中世纪意象的大规模复兴。他有幸成为当时英国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之一——丁尼生笔下的主人公,他于1842 年出版了《亚瑟王之死》,他生前一直在创作《国王叙事诗》,合集于1885 年面世。大约同时期,亚瑟在一些拉斐尔前派画家的作品中获得了新生,尤其是在丹特·加布里埃尔·罗塞蒂(1828—1882)和爱德华·伯恩- 琼斯(1833—1898)的作品中。音乐领域中,在瓦格纳的影响下,肖松于1886—1895 年间创作了他的唯一一部歌剧《亚瑟王》,而我们将会发现其实瓦格纳也在中世纪的(尤其是日耳曼的)英雄与奇观的复兴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

电影最终使中世纪的英雄亚瑟及他的主要英雄伙伴重新焕发了活力。让·科克托最先将亚瑟王的传说搬到戏剧中——《圆桌骑士》(1937)。二战之后出现了一些电影杰作,也出现了许多扭曲、脱离中世纪意象的电影,比如1953 年由理查德·索普导演的好莱坞电影《圆桌武士》,1967 年由乔舒亚·洛根导演的音乐喜剧《卡美洛》。伟大的作品还有布列松的《湖上骑士》(1974)、埃里克·罗默的《威尔士人珀西瓦尔》(1978)和约翰·保曼的《亚瑟王神剑》(1981)。在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著名电影《夺宝奇兵3:圣战奇兵》(1989)中,导演派哈里森·福特去寻找圣杯。滑稽改编也意味着卖座,对亚瑟的调侃在著名的《巨蟒与圣杯》(1975)和泰·加尼特导演、宾·克罗斯比主演的《误闯阿瑟王宫》(1949)中取得了同样好的效果。
颇为保守的好莱坞电影监制人杰里·布鲁克海默刚刚给安托万·福奎阿的场面豪华壮观的电影《亚瑟王》(Le Roi Arthur,2004)投入了巨额资金。剧中罗马人占领结束之后,亚瑟、圭尼维尔和圆桌骑士团被演绎成为使国家走上发展进步的道路而坚决抗击撒克逊人的英格兰英雄。导演表明:“当罗马人占领大不列颠,当英格兰人民为了完成传播文化的使命而摆脱罗马人的压迫并抗击蛮族入侵,那时的亚瑟和今天的阿富汗与伊拉克的局势有着某种意义上的共鸣。”亚瑟真正是无时无刻不在震撼着我们。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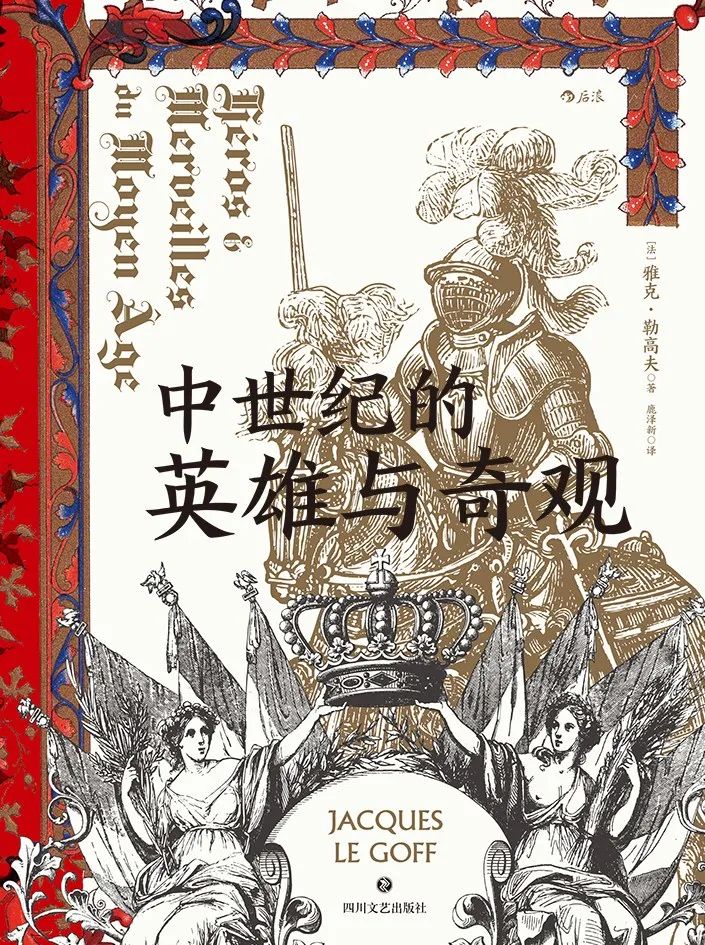
《中世纪的英雄与奇观》
作者: [法] 雅克·勒高夫
出版社: 后浪丨四川文艺出版社
原作名: Héros & Merveilles du Moyen Âge
译者: 鹿泽新
出版年: 202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