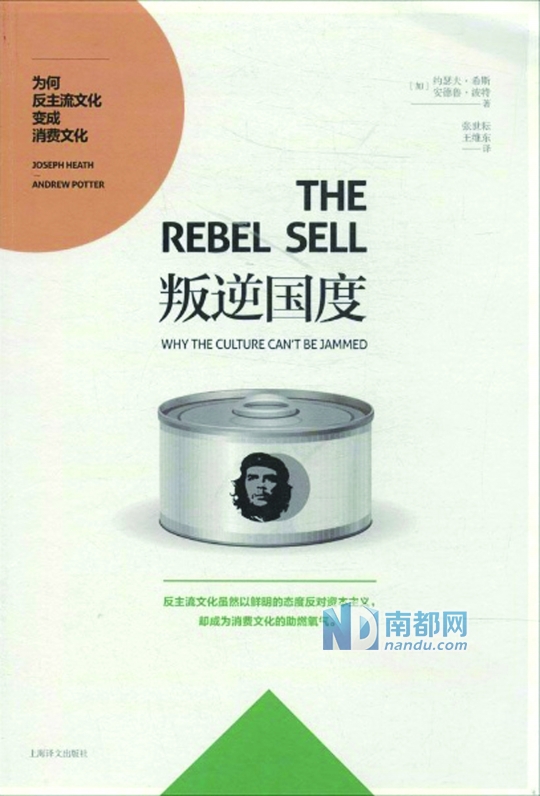
《叛逆国度:为何反主流文化变成消费文化》,(加拿大)约瑟夫·希斯、安德鲁·波特著,张世耘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8月版,58 .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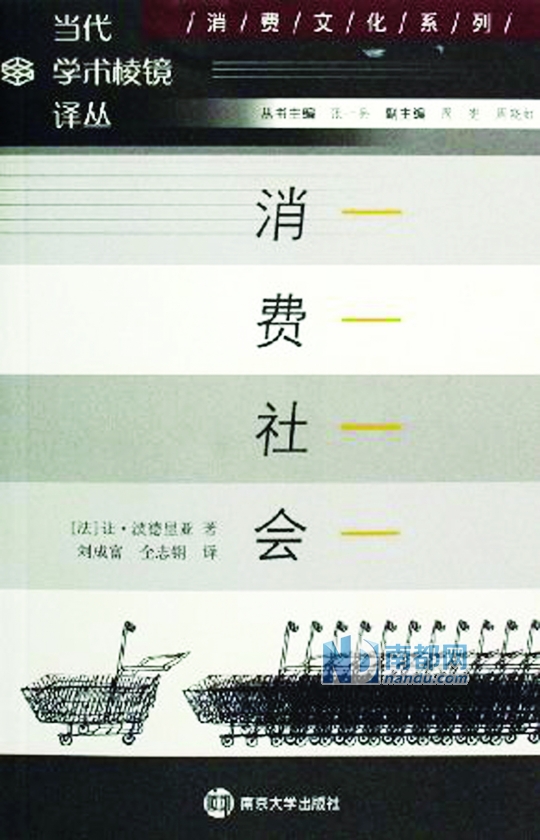
《消费社会》,(法)让·波德里亚著,刘成富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版,28 .00元。
黄夏自由撰稿人,上海
当代反主流文化(以下简称“反文化”)运动发轫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尤其是美国。彼时,物质消费和大众娱乐渐成时代发展的主流,其后,“垮掉的一代”、嬉皮士、反全球化、环保主义、反消费主义等相继接棒且共同汇聚成一股影响深远、且方兴未艾的反文化浪潮。但反文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目前尚没有专书作出全面细致的检讨。好在两位加拿大作家和研究者约瑟夫·希斯、安德鲁·波特撰写的《叛逆国度》,帮助我们从反文化的思想渊源、政治经济机制、反文化与消费主义的关系等方面入手,破除了关于这一思潮的种种迷思。
反文化并非当代事物。柏拉图就曾在《理想国》中探讨过一个叫作“洞穴”幻象的东西,说的是困于洞穴中的人看到洞壁上的影像,仅仅是幻觉,而非真相。日后渐臻启蒙,卢梭引入平等、自由的“高贵的野蛮人”概念,为的是揭露法国专制主义是如“洞穴”幻觉那样虚伪和反常的事物。再后来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鼓励工人阶级参与革命活动,将资本主义说成是束缚他们身心的虚设观念,是由“商品拜物教和异化劳动”所臆造的意识形态。
至20世纪,反文化运动获得了更强大的生命力。纳粹意识通过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进行的技术洗脑和统治,反共时代美国军方对“群体催眠”的兴趣和实验,汉娜·阿伦特《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揭示邪恶来自于正常、理性的普通人类,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表明大众心理的盲从、狂热具有高度传染性,弗洛伊德的精神压抑-升华理论与米歇尔·福柯的规训-惩罚“大囚禁”理论,等等,在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如《一九八四》那样高度极权、巧妙受控和身陷压迫的体制内,只是这个体制打着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旗帜罢了。因而,按照反文化理论,我们要想从体制的意识形态造成的幻觉,和因这个幻觉而导致的压抑、异化和神经症中解脱出来,就必须“拔掉插头”,或推翻、颠覆整个体制,或退入内心,修心养性,剔除植于头脑中的“芯片”。
《叛逆国度》的中心题旨,就在于揭示这种推翻、颠覆和心灵改造理论的无效、偏激乃至虚伪。作者通过比较20世纪前后的反文化运动,说明无论是卢梭还是马克思,他们的理论都旨在局部修正和调整游戏规则(无论是政治抑或经济),而不是彻底将之取消、删除。他们也有明确的目标和纲领,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也知道为了实现目标,争取大众的理解和支持,乃是题中之义,也就是说,他们与大众利益是一致的(至于真的是否一致,则另当别论)。而20世纪以来的反文化运动,其主导理论则既提不出取消、删除规则后应当重建的游戏规则(或者虽经提出,却系无技术支持可能的乌托邦),又把大众视为需要摆脱、反对的庸人,大众发起的任何用以改善自身状况的措施,皆被其斥为治标不治本的肤浅举动。因而,反文化运动在提高人类福祉和幸福水平的问题上,不仅无任何助益,反倒是处处碍手碍脚。
那么,规则本身,是否真是压迫的象征呢?稍稍有点阅历的人,都知道规则在现代社会中,给予我们的好处要远远多过坏处。比如排队,我们固然会因浪费时间而抱怨不已,但试想有人擅自插队而不受惩罚,人人争先恐后,乱作一团,那么浪费的时间就会更多。因而,作者认为,“完全自由、平等的个人关系经常乐于接受强制执行的行为规范,以此规范他们之间的交往。因此,一个社会存在强制并不总是标志着支配关系,或是意味着有必要控制邪恶,或是把一个群体的意志强加给另一个群体。”很大程度上,设立规则的目的就是为了消除集体行动无法协调的困境。
当然,规则也并非毫无漏洞。那么,对于有漏洞的规则,我们是如何反对的呢?对此,作者提出了“不同意见”和“背离规范”两种反对方式。“不同意见就像是公民不服从行为,这是指人们原则上愿意按规则行事,但是对部分通行规则的具体内容抱有真实、诚恳的反对意见。而背离规范则是指人们为了自利的原因而不服从规则……(问题在于)许多采取背离规则的人认为,他们正在以某种形式表达不同意见。”后者经常与前者混淆不清,也因此,许多叛逆行为,如犯罪、吸毒和暴力行为,被赋予争取自由和解放的英勇光环。那么,如何将两者区分开来呢?作者引用马丁·路德·金话说:“我绝对不鼓励回避和反抗法律,这将会导致无政府主义……我认为,当一个人违反一个他的良知认为不正义的法律时,并愿意接受惩罚而在狱中服刑,以唤醒公众良知对不正义的反思,那么,这实际上是对法律的最大尊重。”(《伯明翰市监狱的来信》,1963)。
大众文化的另一个迷思,就在于它是否与消费主义存在因果关系。按照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的看法,大众的需求是消费社会为自身运转制造出来的幻觉,是一个系统符号;系统向大众灌输虚假需求,使他们成为消费大军,目的是配合生产的要求,消化大量生产造成的过剩商品。但鲍德里亚恰恰没有看到市场调整机制远比想象的要复杂,解决萧条问题,并不是要向大众灌输需求,而是投入更多的货币进入经济循环,至于如何投入,则与工资福利、社会保障等公共政策息息相关,而这又是反文化运动所不屑一顾的。
并且,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反文化运动还推动了消费主义的大潮。反文化既然反大众,那么势必要将自己从千篇一律中“区分”开来,追求另类和时尚,而时尚的周期则不断加快(昨天的另类成了今天的大众),投入其中的金钱更是推高了消费主义。归根结底,“身份区分”实际上就是阶级区分,“人们愿意多花钱,这和他们愿意多花钱获得某种形式的社会地位毫无两样”,这和反文化口口声声要消灭资本主义简直南辕北辙。而在阶级构成上,反文化所倡导的个性、自由、叛逆,更是符合资本主义求新变的内在精神,反倒是恪守新教传统的旧式资产阶级,成了资本主义自身力量的清除对象。因而可以这么说,反文化就是资本主义本身。
反文化的心态值得我们咂摸,它源自对国家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高度不信任,照理说可供我们作社会批判之用,但它又没有提出我们可以信赖的、具建设意义的理论工具。它是启蒙时代和20世纪留给我们的思想遗产,但注定让我们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深受它的蛊惑和困扰。《叛逆国度》定义了一个信息爆炸而人们越来越无所适从的时代,而理论家们为理解这个时代所发起的反文化运动,说到底仍是那个如魅影一般的“柏拉图洞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