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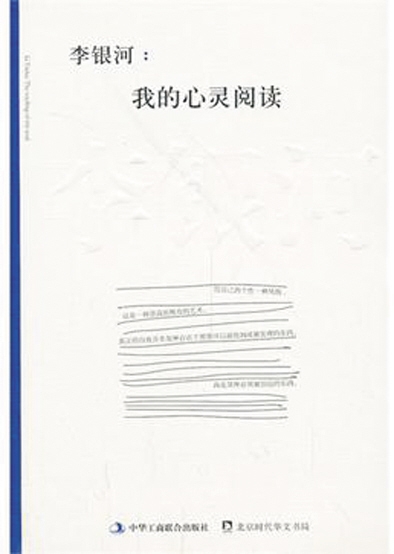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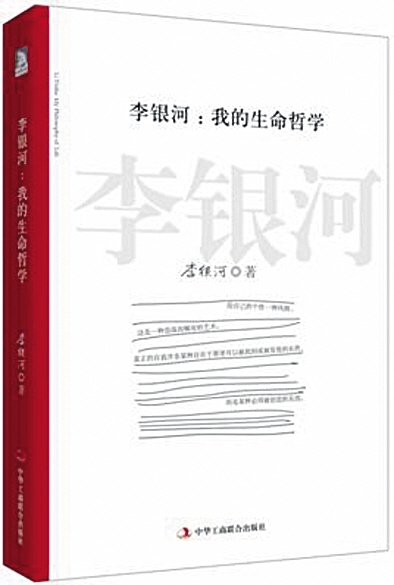
蓝色,是自由的颜色。而李银河所做的,就是争取这样一种被制度和习俗剥夺过多的“人的自由”,无论这种自由,是关于性,或是其他。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和王小波轰轰烈烈谈恋爱的“文艺女青年”,到在学术圈被誉为“中国波伏娃”的观念前卫的性学家,再到网络时代在性别话题上饱受争议的公共知识分子,李银河经历了公众眼中一次又一次的身份转换。年长一些的读者大概更熟悉的是作为王小波遗孀的李银河;性少数群体把李银河奉为英雄和“带给人间温暖与光明”的普罗米修斯;但在社会主流性观念和道德观念面前,李银河更是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知识分子。公共领域对学者出身的李银河来说就像一个荒岛,她所习得的“常识”一直在“挑衅”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而她就像个孤军奋战的斗士,被非议、被攻击,但仍然心平气和地守护着她的战地,期待社会观念的进步,期待被更多人所理解。
性权利
注定被指手画脚的研究
“性学家”是李银河在学术界最主要的身份。她早年在美国取得社会学博士,归国后师从费孝通,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文科博士后,此后便开始了她在中国研究“性别”、“婚姻”、“同性恋”之路。费孝通先生对她的学术生涯影响非常大,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就步上费孝通先生开创的“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方法研究社会学”道路。她在实地调查中分析了大量个案、描述了形形色色的个体经验,展现出了这一群体在中国社会的文化身份。
这部1998年出版的研究著作也开启了中国学界把同性恋群体作为文化研究的先河,为之后近二十年中国同性恋群体争取权益开辟出了大量空间。在李银河、潘绥铭、张北川等性学家的推动下,社会对这个性少数群体的宽容度越来越高,同性恋在这个时代可以更骄傲地走进公众视野,至少是年轻人的视野。中国是一个过度性压抑的社会,“性”这件事在中国社会中以各种各样的姿态,承担着不同程度的污名。李银河一直没有停止为我们被制度和习俗剥夺过多的“性权利”疾呼,她经常引用自己的精神偶像福柯的观点,“多元人际关系模式是未来的趋势”,并感叹,“我们社会中的人际模式是多么可怜呐!”
网络时代又把这位学者拉到了更为广泛的公共视域之中,李银河跳出学术圈,在博客里的通俗化写作使她的观念和言论更有效地散播了出去,但也更大范围更有力度地冲击了公众的价值观。习俗就像一个痼疾,它不止伤害着被无形剥夺性权利的人们,也一直伤害着这个性权利斗士。最令人难过的是,她难以得到那些她为之疾呼的人们的理解。多年来,李银河对此最沮丧也最激烈的一次在博文中的表达,也不过像一句抱怨,“好心被当成驴肝肺!”
公领域和私领域
呼唤包容性,坚守浪漫爱
很多人质疑,在与王小波的爱情故事里有着浪漫天性、专一而又深情的李银河,怎么会支持“一夜情”、“多边恋”呢?李银河的解释是,这是私领域和公领域的区别。
在八十年代,李银河和王小波是特别前卫的文艺青年,他们一起疯狂地看电影、读小说,环游欧洲。结婚后,王小波已经有了侄子和侄女,李银河也有了侄子侄女,两人商量着,“咱俩都不能给各自家里添新品种了,别生了”,“对,不生了”。就这样,他们选择了“丁克”——在那个年代前卫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生活方式。可惜,这样自由浪漫的生活只延续了二十年,王小波辞世后,李银河的一篇《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悼小波》,曾让无数读者声泪俱下。后来的十几年里,也经常能在李银河的博客中看到王小波的名字,不论生离死别,王小波早已是李银河漫长生命中的一部分了。
而当李银河近年来一再在博客上主张“卖淫非罪化”,当她公然为因参与“集体换偶事件”而获“聚众淫乱罪”的某副教授维权时,人们又追忆起了她和王小波被世人传诵的刻骨铭心的爱情。这让一些公众面对她对性自由的观念“痛心疾首”,甚至问出“李银河对得起王小波吗”这样的问题。李银河对这样的问题总是哭笑不得,她曾经回应说,“王小波如果活到现在,立场肯定和我一样,只不过他表达的方式会更幽默。”
混淆公领域和私领域,似乎是很多公众的逻辑。在公共领域内,李银河在种种性话题上“惊世骇俗”的发声,事实上只指向了两个字:权利。捍卫不同群体或个体做某件事的权利,推动一个更包容的、能接受多元关系与不同价值的社会,一直被李银河视为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责任。她认为自己有责任为不相干的人发声,为发不出声音的人发声。
但这一切的倡导,并不代表着她本人在私人空间里也是那样做的。事实上,李银河在私领域中,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爱情坚守者。她一再在博客里赞颂“超凡脱俗的精神之爱”,她在博文中写“生命是多么短暂,我想让自由和美丽把它充满。”
退休生活
开启“不严肃小说”的创作
李银河在退休后出版了三本学术著作以外的杂文集,《我的生命哲学》、《我的社会观察》和《我的心灵阅读》。这三本文集大量收录了她多年来在博客上的文章,《我的生命哲学》卖得尤其好,里面大多在讨论关于存在、衰老、死亡孤独这些沉重、却又随时裹挟着我们生命的问题。同时,三本书的名字也在很大程度上总结了李银河退休后的生活状态——她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思考生命,用来阅读,以及继续参与到公共话题中。
除此以外,这位女士在年过六十的年纪,竟心血来潮地开始尝试小说的创作。2013年底的一天,李银河在博客上发下了一个“宣言”,“由于本人和众多同性恋平权运动积极分子的努力,同性恋在中国已经基本被正名了。我把下一个目标确定为在中国为虐恋正名。作为性研究者,我责无旁贷。”在这之后的日子里,她就开始陆续在博客上发她写的“虐恋主题”的短篇小说。
由于主题都是“虐恋”,小说无法在内地出版,李银河原本在香港签了出版商,但后来出于种种压力,还是违约了。最大的压力在于,她很多亲友劝阻她,如果小说出版了,在公共领域又会大量减少支持者。虽然李银河一再强调探讨“虐恋”的意义,可要彻底解放人们的性观念,破除人们对任何形式的“性”的偏见,在中国社会中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
只要“性”这个话语在这个社会还在被诟病,只要还有人因为“性”而受到歧视,公共领域对李银河来说就仍是一座“荒岛”,她拿着唯一的武器——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守卫在这里,迎接黎明。
“当我们感觉到不自由的时候,实际上仅仅是由于我们屈从于习俗,我们完全可以不这样做,而去选择一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的生活。”
采写/新京报记者伍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