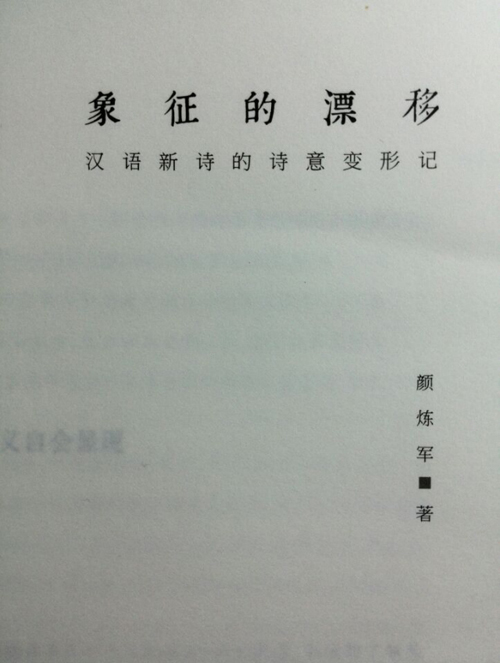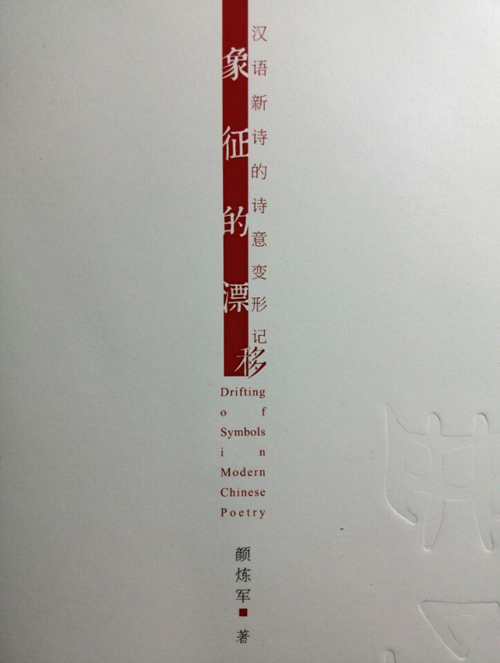
我在北京求学期间,因参与处理张枣老师后事,与诗人赵野先生有过数次缘分相见,只是未及细谈和请教。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意外地收到了赵野先生的微信,他对发表在《诗建设》上的本书第一章给予了过高的评价,并希望能够读到本书全稿。粗陋习作得到长辈的鼓励,自然令人倍受鼓舞。文情难鉴,诗人与批评家之间,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所说的,更多是“东向而望,不见西墙”。赵野先生慷慨答应为本书作序,显现了他的长者风范和沉博绝丽的诗人之心。感谢赵野先生,更要感谢因诗人和诗歌而来的缘分。 ——颜炼军
1
我还记得读到《祖先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时的欣喜,我读到了触及到汉语诗歌秘密的文字。那是去年秋天,一个与那篇文章的意蕴和表述相契的季节,我正在思考“兴”与中国当代绘画之间,能否找到一种联系,之前我已相信,“兴”是中国诗歌甚至中国文化里,最迷人也最本质的一个概念。文章发表在泉子编的《诗建设》第10期,作者是颜炼军。窗外天空高远,落叶悠然,我在心思往返中,记下了这些对我深有启发的语句:
“兴”通过所命名或指涉之物,来完成人与神之间的往来,亲证了世界“看不见”的部分。“兴”是事物、语言和经验之间的相互唤醒,三者的叠加、回响,呈现的是一种内在的自由。汉语新诗必须建立起自己描写新的经验和事物的自由传统和词语魔术,建立起新的“写物”之辞,与新的物外之“意”契合,以新的、敞开的形式来安排事物和经验的秩序。“兴”在脱离了神话和宗教意义后,……依然作为一种“野性的思维”……,不断促成物我之间充满惊讶的遭遇和共鸣。这是一种心与物之间的自由回响,是一种想象的自由,也就是诗意的自由,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对人神共处的自由状态的永不疲倦的模仿。
2 敬文东兄为人为师,皆有民国风范。数年前就向我多次提起他的几个学生,颜炼军,张光昕,曹梦琰,说是为中国诗歌找到了几颗好苗子,深感自豪。炼军好像早早去杭州了,几次私下酒局,文东带着光昕和梦琰前来,我和他们已熟悉。后来我曾代《艺术时代》杂志,约光昕写了一系列诗学文章,梦琰则受师命,写过一篇我的评论,他们二人的才情、见识及文字,不负乃师夸誉。文化本是一种传承,需要一代代薪火相传。 我和炼军后来在公共活动中,打过一两次照面,北京的匆忙熙攘,不会让人在这种照面里,对谁有较深的印象。张枣仙逝后,我知道炼军花了很多功夫,编辑出版他的诗集和随笔集,其诚昭昭,其心眷眷。我和枣兄相识二十多年,一直认为他是这一百年里最大的语言天才,其对汉语诗歌及汉语本身的贡献,应该成为当代文化极为珍贵的部分。炼军倾心于此,想来除了报师恩,也是持有同样的价值判断。 去岁末在上海见到何言宏兄,向他提起炼军的这篇文章,他说这只是炼军博士论文的一章,我遂满怀期待,向炼军要来这份全稿《象征的漂移》。短信沟通中,知道他生在大理乡下,长于苍山洱海间,就更多了一份亲切。大理啊,那是中国我最喜欢的地方,我和好多朋友的终老之地。 3 波德莱尔定义的现代性,一半是瞬时、即兴、变化,而另一半是永恒。尼采说上帝已死后,西方古典主义诗歌丧失了神性的基础,诗人们独自面对巨大的虚无,成为现代社会的外人。最好的现代主义诗人,波德莱尔、马拉美、里尔克、艾略特、叶芝、庞德、奥登一脉,则通过重新激活古典神性资源,建立新的现代抒情神话,书写新的崇高性,将现代社会的各种危机和消极性,转化为有效的抒情,从而证明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诗意能力。 汉语古典诗歌,有着更悠久的传统、丰富性和成就。古典诗歌世界具备坚实的形而上学基础:“原道”,对不可企及的世界本质的遵循;“征圣”,对圣贤高士理想人格的追慕;“宗经”,修辞立诚,不逾距。两千年来,语言与事物之间,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精致的、几近穷尽的诗意,源源不断为古典中国的日常生活输出崇高感和美感。当天下体系崩塌,古典诗歌的形而上学基础随之解体,诗人面临诗意的巨大空白。 本书一开篇,即以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为参照,优美表述了汉语诗歌的根本性特征,和遭遇的现代性困境,并高蹈指出现代汉语诗歌,应该化解和分担这场浩大无边的生存危机,写出存在中的难言之隐,把生活、历史乃至世界的一切,内化为诗的崇高,彰显现代中国人存在本质的诗意性。“没有诗意进取,现实便不能独自成立”,这个断言有着古希腊的自信和明确,难道这就是我们要建立的新的形而上学基础? 在今天,一个成熟诗人一定要能回应这些价值观,让世界的梦想,存在于一首诗中。 4 1946年,隐匿在浙东乡野的胡兰成,以逃亡之身,不忘天下志,开始著述《山河岁月》,在中国文化中,独挑出一个“兴”字,来展开他的历史抒情。胡兰成认为礼与乐是中国文明的基础,而“兴”正代表了乐的精神。在胡兰成那里,“兴”是万物的自然呈现,“大自然的意志之动为兴,大自然的意志赋予万物,故万物亦皆可有兴。诗人言山川有嘉气,望气者言东南有王气,此即是兴。” 胡兰成的历史抒情,有些似是而非,大而无当,用在审美范畴,却很精妙。诗人具备一种古今同在、当下永恒的能力,“兴”正是抵达的要隘。明了“兴”,即能明了汉语独有的那份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本真自然。“兴”的奥秘与滋味,不独属于中国古典诗歌,而是属于汉语和汉语文明。新诗要在一种新的经验下,赋予事物以新的感觉和情欲,重建与世界的亲密关系,“兴”无疑是再生的一个原点。它可以唤醒我们业已迟钝的对物的通感,把倍受现代性与意识形态双重蹂躏的语言,集合成美的冲锋队。 炼军在书中对“兴”的辨析,完全契合了我多年所思。当代语言晦暗不明,“兴”是幽微之处一道被遮蔽的光。汉语需要它的探路者和突进者,我们也许应该集体前行。 5 二十多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说现代汉语还不成熟,后来我又多次陈述过同样的观点。在世界文明史里,现代汉语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关系,与古英语和现代英语的关系,一定有根本的差异。古汉语的书写语言,是独特的文言文系统,和日常说话全然不同。明清的白话写作,几近口语,当时不是主流。“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语言上完全废弃了文言文,采用白话写作。白话文应被看作一种新的语言,其句法、节奏、气息,都是口语的,它的词汇构成,却来源于日常用语、翻译语言和文言文。后者其实是基础与核心的部分,能带出整个汉语文明与历史,让现代汉语诗歌写作充满可能性。当时,翻译文体压倒性覆盖了新诗的写作,我很少看到这种敏感、认识与成果。 《风雨如晦》一章,即我最初读到的《祖先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最能见出作者的见识,及对汉语的微妙把握,触角伸到了很深的地方。汉字的象形性,赋予汉语丰富、多义的质地,汉语诗歌中人、神、物之间的象征和呼应,充满各种契合点,彼此在召唤和暗示,而这一切的实现,正是通过“兴”。这正是汉语的诱惑所在,我不知道今天的诗人,有多少能领悟到这点。 我以前写过一段话,可与炼军互证:汉语是有思想的语言,我们现在使用的每一个字,在起源上都和世界万物有着某种特定的关系。中国文字一开始,就有丰富的隐喻性。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即是说,诗中有世间的秩序和万物的象征,我们读懂了诗,就能知晓山的静默,水的流动,以及鸟兽草木的鸣叫生长,对我们命运的影响和暗示。迹象即征兆,一切皆有深意。汉语诗歌的秘密,或迷人之处,就在于呈现物与物,或象与象之间的内在关系。 6 如果相信一句老话,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似乎可以说,西方各大语种的诗人,已经穷尽了他们的一切可能,如史蒂文斯所说,“天堂与地狱的伟大诗篇都已写下”。当代中国诗人因为现代汉语的独特性,和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处境。我们还未涉及天堂,未涉及地狱,只是纠缠在尘世里,也没有留下几个经典的文本。还有太多的经验没有处理,命名没有完成,命运没有呈现。自信如张枣,尽管认为汉语已“可以说出整个世界,可以说出历史和当代”,也承认这还是一种表面上的成熟,“它更深的成熟应该跟那些说不出的事物勾连起来,这才会使现代汉语成为一门真正的文化帝国的语言。” 现代汉语的三个来源,日常用语源源不断有鲜活感,却边界有限;翻译文体让我们感知别的文明里伟大的经验、思想与感受力,但诗歌终究要有本民族的文化属性,和母语的节奏与气息;古汉语背后有整个汉语文明与历史,想到这点就令人动心不已。炼军洞见如是:古典诗歌中物与志,或者说象与意之间原本固化的对应,被白话文学革命解除后,词与物在现代汉语中获得了完全自由,使我们可以重返世界原初的无限与澄明。“每一个时代的诗歌,所要发明的,正是对称于这个时代的词与物的关系。”问题是我们作好准备了吗? 这样终于回到了传统问题,我现在相信,对一个当代汉语诗人来说,对自己的传统认识多少,了悟多少并最终转化多少,可能最后决定他能达到的高度。 7 接下来作者梳理了新诗中的写物形态,祖国隐喻,天鹅形象,抒情主体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部分中规中矩,标准的体制下论文。印象较深的,是张枣诗中鹤与燕子的美妙分析,至于天鹅在汉语中,我一直有种怪怪的感觉。就文本而言,我对中国现代诗歌评价不高,尽管年轻时受惠过他们。按艾略特的说法,这是语言和时代的不成熟,与人无关。才情、修养与学识,那批诗人个个大家,我们望尘莫及。 在这本书最后,我看到了炼军的忧心,一个诗歌的使徒,站在危岩边警示来者:比西方现代诗歌晚了近一百年,当代汉语诗歌也完全进入它的虚无主义时代,古典社会中那个侵染着汉语诗歌精神,指引世间万物的彼岸世界已然远去。诗人的象征性发明日益困难,诗歌如何写下不可企及、心向往之的崇高性?或者说,新的言路如何创建? 这是一个相当宏大的命题,而且是批评者的立场,每个诗人会有自己的回应。在网上读到黄灿然对张枣的访谈,张枣说诗歌写作的三个阶段像悟禅:开先的时候词是词,物是物,两者难以融合;后来词物相交,浑然一体,写诗变成纯粹的语言运作;真正难的是第三阶段,这时词与物又分开了,主体也重新出现,三者对峙着构成关系,这时主体最大的不同是他已达到某种空以纳物的状态,居不择地,内心充满着激情理解和爱。彼时我心中暗叫:枣哥,天才啊,我们还在追求词即物,你已经到了更高一层境界。归根结底,诗歌写作是语言的事,诗人的一切梦想皆取决于此。其实我真正要表达的是,语言如果成立,意义自会显现。 近日与友人谈中国何以是中国,历史与文化俨然两极。历史无道凶残,万物为刍狗,文化却一次次重生,坚韧如是。我以为天下观、士的传统以及乡村社会结构,是中国文明数千年来终能万劫如花的根本,今天这三者都被连根拔起,我们可否寄望诗歌承负这个使命。 8 在我全然不顾自己的能力,答应为这本书作序时,一定是它有深深触动我的东西。作为一个当代诗歌写作者,通过语言来构建一个完全自足的世界,呈现中国文化审美和精神特质,是我多年的愿望。我希望我的诗歌里,有一个生动的汉语文明心灵,如草木在阳光下。我不能确定我在这本书里看到的,就是作者本来的意思,也许我完全单向化甚至误读了他的诗学。如果真是这样,正好证明了汉语含混的魅力。现实要求一种明晰,而美总是漂移的,如同世界的本质。 现在我想说,这是一本懂诗的人写的非常内行的书,对汉语诗歌作了全面深入的思考,抵达了一些问题的内核,有着真正的发现。当然诗人不一定要搞清楚这些才写作,诗歌需要更深邃的天赋。 我还想说,这本书视野开阔,富有启示的说法和极具灵感的论述比比皆是。相比于它已突破的部分,另外一些篇章略显平凡,它的文字也还可以更简洁紧凑,至少离一种理想文体还有距离。如果严格一点,它还可以继续打磨,包括对作为范例的诗歌的选择,和对它们的阐述,都有低于作者能力的时候,有些解析落入了俗套。我当然知道批评和创作完全是两回事。诗人更在乎语言质感,和特别微妙的地方,所以会对那些无关本质的批评不以为然。 在这个时代,也许我们不应该要求更多。事实上这本书已经很好了,已经足以值得我们关注和尊重。 《象征的漂移》 内容简介 每一个时代的诗歌,所要发明的,正是对称于这个时代的词与物的关系。 白话文学革命解除了古典诗歌中的物与志,或者说象与意之间原本固化的对应,使现代汉语中的词与物获得了完全自由,诗人因之重返世界原初的无限与澄明,但象征性发明的困难也因之产生。 本书探讨和呈现了百年来不同时期汉语新诗言说或命名崇高性的基本状况,为读者呈现了古典诗歌整体退场之后,汉语新诗不断寻找诗意发明依存的基础、迎向诗意“空白”的跌宕之旅。 作者简介 颜炼军,一九八零年生,祖籍云南丽江,生于大理。文学学者,散文随笔作者。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现任教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另编选有《张枣的诗》,《张枣随笔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