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接到信,你就知道我还平安,不要焦急。
这是一家靠海的旅馆;我的窗面对着黑暗的海口,稀稀疏疏的渔火看起来特别寂寞——还是我自己的心情呢?
结婚三年以来,这是第一次给你写信,而居然是在我“离家出走”的情况下。
你当兵那年,我们一天一封信地缠绵与甜蜜,倒像是不可思议的梦境。
今天晚上,孤独地在一个陌生的小镇上,窗外飘来欲雨的空气,我真有点不知自己是谁的恍惚。
早上的事情实在并没什么大不了,你一定觉得我怎么突然小题大做起来;或者,以为我用出走来要挟你或责备婆婆。
不,亲爱的,我一点没有要挟的意思。我只是走到了一条路的尽头,发现了一条岔路,现在,我得决定是往回走呢,或者,换个方向,往那几乎没有足迹的岔路上走去。
昨天一回家,婆婆就说:“阿坤的衬衫领子有一圈肮脏,洗衣机洗不清净,你暗时用手搓吧!”
我说“好”,其实丢下书只想回房蒙头大睡;白天有教学观摩,连续站了好几个小时,觉得小腿都站肿了,晚饭也不想吃。但是一家几口等着我烧饭,你贪爱的黄鱼中午就拿了出来解冻,晚上非煎不可。
小叔回来了,三下两下脱掉脏透湿透的球衣,随手扔在餐桌上:“阿嫂,要洗!”
电视声开得很大,婆婆唯一的嗜好是那几场歌仔戏。
抽油烟机坏了,爆葱的时候,火热的烟气冒得我一头一脸。炒菠菜一定得有七八颗大蒜,不然婆婆不吃;可是上菜的时候,大蒜一定要剔掉,因为你见不得大蒜。酱油又快用光了,再多炒一个菜就不够了。我找不到辣椒,大概中午婆婆用过,她常把东西放到她喜欢的地方去。
你的话很少,尤其吃饭的时候,说话本来不容易,婆婆重听,一面吃饭,一面听电视,声音开得更大。
我说:“待会儿陪我到河边走走好不好?”
你好像没听见;或许你也累了。几个人淹在歌仔戏的哭调里,草草吃完,你甚至没有发觉我做的是黄鱼。小叔丢下碗筷,关进房里去给女朋友打电话,婆婆回到电视前,你喝着我泡的热茶,半躺着看晚报,我站在水槽边洗碗碟。
回房间的时间,婆婆大声问了一句:“这么快就洗好了?别忘了那些衬衫领子——用手洗。”
躺在床上,有虚脱的感觉。是教课累着了吗?还是做菜站得太久?还是那些油腻的碗筷?还是,因为你没陪我到河边走走?
今天刚好教李后主的《浪淘沙》,课堂上念着念着就想起我们读中文系的那段时光,每逢春雨,就自以为很洒脱诗意地到雨里去晃,手牵着手,一人一句地唱“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然后全身湿透地回家,觉得透心的冰凉、痛快。
我把脚搁在枕头上,减轻胀的感觉,然后开始看李若男给我的书——你知道,若男从美国回来,变了很多,尤其看不惯我做“保守妇女”的模样,一直鼓动我看有关女权的书。
不愿意辜负从小一块长大的情分,更何况,我们在一起时,永远只有我听的份,我倒真用心读了几本她介绍的书。
可是我还不太了解那些观念。这些书都强调女人和男人一样有智慧与能力,所以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做一样重要的事情。所举的例子,不是女企业家,就是女博士、女主管、女部长;总而言之,“女强人”!
而所有的“女强人”都长一个模样:短发、大眼镜、米色的西装,手里拿支笔,一副很严肃、很精干、很重要的神情。这些书强调女人的潜力,好像每个女人都应该从“家”那个窝囊的洞里出来和男人瓜分天下。
或许我太保守,我总觉得:我不是“女强人”,我喜欢“家”里的厨房与卧房,我不喜欢短头发、大眼镜、米色的西装,我喜欢依靠在丈夫的怀里,让他拥着我叫我“小女人”,我不喜欢争强斗胜,不管是和男人或女人……
可是,这本新书里有一张很吸引人的画片:一个女人站在一片葱绿的原野上,眺望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在云海的会合处有几只淡淡的海鸥。很简单的画面,但是呈现出很宽很广、无穷无尽的视野。照片下有简单的一行字:
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
我心动了一下,但是理不出什么头绪来。
婆婆把头探进来两次,我没作声;我太累了,而且,我还在想那一行似通不通的句子。有时候真希望能够把房门反锁了,没经过允许,谁也不能进来打扰,可以假装不在。
小时候,每和爸妈斗气,照例躲进大衣橱里睡一下午,觉得安全又自由。但是我们的房门上没有锁,一结婚,婆婆不喜欢,就把锁打掉了,表示我们是亲密的一家人。
你进房的时候,大概很晚了。我睡得朦朦胧胧的,你也倒头就睡,背对着我。
没想到早上婆婆生那么大的气。
稀饭确实煮得太硬,不过,平常不也就吃了吗?我要加水再熬,她把锅抢过去,一把翻过来,就把饭倒在馊水桶里,大声说:“这款饭给猪吃还差不多。不爱做事就免做!阿坤儿,你今天自己去买几件干净的衬衫来穿,不要让别人讲笑!”
你抓了份早报,走进浴室,很不耐烦地回头说:“查某人,吵死!透早就吵!”(编注:查某人,闽南语词汇,指女孩子)
“砰”一声,把门关上。
婆婆重新淘米,锅盘撞击得特别刺耳。你大概坐在马桶上,一边看武侠连载。小叔揉着睡眼出来,问我昨天的球衣洗了没有,他今天要穿。
我压住翻腾的情绪,走到后院,隔壁阿庆的妻挺着很大的肚子,正在晾衣服。
不,我并没有生气,真的不生气。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阿庆的妻很艰难地弯腰取衣,那一刻,我突然意外清楚地,从远方看着自己这个“查某人”——
三年来,清早第一件事是为你泡一杯热茶,放在床头,让你醒过来。你穿衣服的时候,我去做早点,顺便把小叔叫醒。伺候你们吃完早餐,你骑机车到镇公所上班,我走路到学校。放学回来,做晚饭,听歌仔戏,洗碗筷,改作业,洗衣服,拖地板,然后上床,熄灯,睡觉,等第二个清晨为你泡杯热茶、叫醒小叔、做早饭……
然后你坐在马桶上,很不胜其烦地说:“查某人,吵死!透早就吵!”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就是这么回事吗?
我不是若男,也没有兴趣作女强人;可是,亲爱的,我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我觉得这么空虚?好像声嘶力竭地扮演一个角色,而台下一片嘘声;好像做任何事情,都是我分内的责任,这个“分”,就是妻子、媳妇、大嫂,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女人”的分。我,就是一个女人;女人,就该做这些事,过这样的日子。这是命!
我很迷惑。你上了一天班回来,筋疲力尽,觉得做丈夫的有权利享受一下妻子的伺候;但是,别忘了做妻子的我也上了一天课,也觉得筋疲力尽,为什么就必须挑起另一个全天候的、“分内”的工作?为什么我就永远没有“下班”的时候?
并不是我不情愿服侍你,我非常情愿。可是,亲爱的,你知不知道,我并不是因为要履行女人命定的义务才为你泡一杯香茶,实在是因为我爱你——爱你熟睡时如婴儿的眉眼,爱当年吟诗淋雨的浪漫,爱你是我将白头共老的人——所以服侍你。
如果你把我当作一个和你平等的、纯粹而完整的“人”看待,你或许会满怀珍爱地接过那杯浮着绿萍的茶,感谢我的殷勤。
可是,你把我当“查某人”看,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分”内的事。结了婚,戴上“女人”这个模子之后,连看书、淋雨、念诗、到河边散步、幻想,都变成“分”外的事了。
我变成一只蜗牛,身上锁着一个巨大的壳,怎么钻都钻不出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难道作为女人的同时,我不能也是一个自尊自主的“人”?难道一定要与男人争强斗胜,——比男人更“男人”,才能得到尊重与自由?我可不可能一方面以女性的温柔爱你,一方面,你又了解我对你的爱并不是“查某人”分内的事,因此而珍惜我的种种情意?
说得更明白一点,亲爱的,你能不能了解,我为你所做的一切——烧饭、洗衣、拿拖鞋——都不是我身为女人的“义务”,而是身为爱人的“权利”?一切都只为了爱?!
比做“女人”更重要的,是做一个纯粹而完整的“人”——你懂吗?愿意懂吗?
连海口的渔火都灭了。我已经走到一条路的尽头,只盼望你愿意陪我转到那条足迹较稀的岔路上去。回头,是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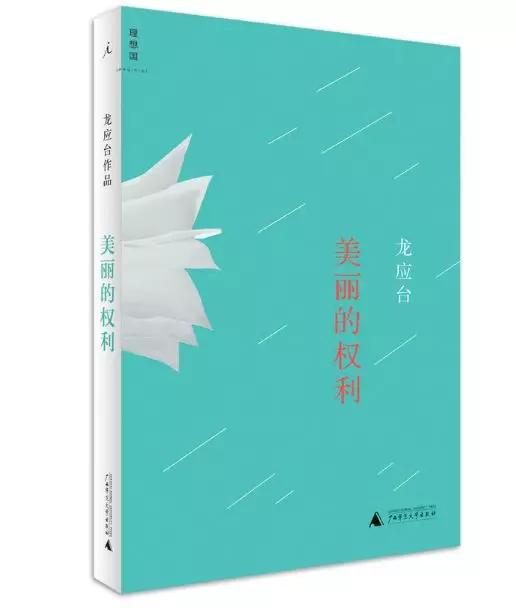
本文摘自龙应台《美丽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