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为人父母居然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真是太可怕了。”日本作家伊坂幸太郎的这句话曾经引起热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作为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在日常相处中,到底该保持怎样的距离,又要如何进行交流?
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美国作家琼·狄迪恩的《蓝夜》。在这本书中,她讲述了自己在痛失唯一的女儿金塔纳之后的心路历程,从孩童时期的陪伴到目送她踏入婚姻的殿堂,当回忆突然袭来,悔恨和痛苦重新浮现,对于爱的认知终于日渐清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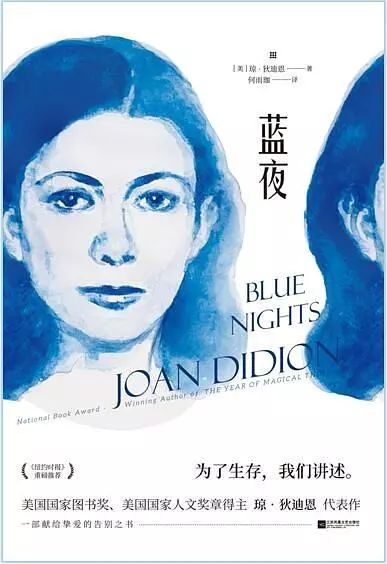
《蓝夜》
[美] 琼·狄迪恩著
何雨珈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蓝夜》节选
我不知道多少人会自认是成功的父母。自觉成功的人一般会举出那些象征着(他们自己)社会地位的东西:斯坦福的学位、哈佛的MBA、常春藤联盟大学毕业生聚集的律师事务所的暑期实习。而不怎么愿意自夸做父母的技巧的人(也就是大多数人),会像念经一样重复我们的失败、疏忽、不负责任和各种托词。“成功父母”的定义经历了非常明显的变化:从前我们认为,成功的父母能够鼓励孩子进入独立的(成人)生活,“提升”他们,放手让孩子去飞。如果孩子想要骑着单车冲下陡坡,父母可能会象征性地提醒一下,冲下这个陡坡就会进入一个四岔路口。但归根结底,最想培养的还是孩子的独立精神,所以父母也就不唠叨,不过多地提醒了。如果孩子想去做一项结局可能很糟糕的活动,父母可能会提醒一句,但只提一次,不会再说第二次。

我在二战期间的孩提时代便是如此。在战争中长大,就意味着我需要比在和平时代更强的独立性。父亲是空军的财政官,战争刚开始那几年,母亲、哥哥和我就跟着他。日子过得并不算艰难,但想想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三年期间,生活在美国军事设施附近的那种异常拥挤、混乱不堪的状况,我的童年也绝不是安居无忧。在科泉市,我们第一次有了真正的房子,那是精神病医院附近的平房,有四间屋。但我们没有打开包袱收拾行李,妈妈说没有必要,因为随时都可能接到“命令”(“命令”对我来说是个神秘的概念,不容置疑)。
每到一个地方,大人们就希望哥哥和我能适应,能凑合,能在建立生活的同时也接受眼前的事实,那就是无论我们建立怎样的生活,都会因为“命令”的突然到来而终止,被推翻。我从来都不清楚到底是谁下的命令。但就算我觉得不合理,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世界正在大战。战争不可能因为孩子们的愿望有任何缓和或转移。孩子们容忍了这令人不快的事实,得到的回报就是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生活。这些孩子的父母面临的最好选择,就是任由孩子们自由野蛮地生长,而这背后隐含的影响,却无人去深究。

战争结束了,我们又回到萨克拉门托的家。但家庭教育的主题依然是放任自流。我还记得十五岁半拿到实习驾照时,就觉得可以吃完晚饭从萨克拉门托开车到太浩湖了。要沿着蜿蜒起伏的山间高速公路开两三个小时,到达之后,我们又立刻转头开回去,因为车里的饮品都带齐了,再沿着来路开两三个小时回家。我开车消失在内华达的高山之中,而且还算是彻夜醉驾,结果爸妈一句都没有说我。我还记得,大概也是十五岁的时候,在萨克拉门托北边的美利坚河漂流,结果被大水冲进一个分水坝,然后拖着漂流艇来到上游,又玩了一次。对于我这样的行为,爸妈仍然一句话也没有说。
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现在实在是无法想象了。
为人父母的行程表上,已经没有时间让你去容忍孩子这样大胆放肆的消遣了。
尽管这种良性的忽略让自己受益,轮到我们当了父母,对成功的判断标准,却是我们能对孩子进行多么严格的监控,恨不得把他们紧紧拴在身边。巴纳德学院院长夏竹丽建议父母多给孩子一点信任,不要对他们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大包大揽。她提到有位父亲,专门休假一年来指导女儿的大学申请准备工作。她提到有位母亲,亲自陪着女儿去见系主任,讨论一个研究项目。她又提到另一位母亲,说因为自己付了学费,要求校方把女儿的成绩单直接寄给她。

几年前,波士顿东北大学的卢因女士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写了大学校园里代沟变小的问题。不仅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家长们的问题,也指出了学生自己的问题。其中有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一个月和家人的手机通话时间远超三千分钟。她似乎把自己家看作一个很有用的学术资料库。“我可能会给爸爸打电话,问他‘土耳其的库尔德人是怎么回事?’这比自己去查找资料容易多了。他什么都知道。我爸爸说什么我基本都会信。”另一个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学生被问,有没有觉得和父母太亲近了,她一脸茫然不解:“那是我们的父母啊,他们本来就应该帮我们。这本来就是他们的职责所在啊。”
我们越来越觉得,这样深入参与到孩子的生活中是特别正当的行为,对他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我们把他们的号码设为快捷拨号,通过聊天软件注视他们,追踪他们的去向。我们认为打过去的每个电话他们都要接,只要他们计划有变就要向我们报告。我们总是胡思乱想,觉得一离开我们的视线,他们就会遇到前所未有的新危险。我们会把“恐怖主义”挂在嘴边,彼此警告“世道不同了”“和以前不一样了”“不能放任他们干我们以前干的事了”。

然而孩子总是要面临危险的。
女儿金塔纳出生之后,我没有一刻不在担惊受怕。
我怕游泳池,怕高压线,怕水槽下面的碱水,怕药橱里的阿司匹林,怕“破碎男”本人。我怕响尾蛇,怕湍急的水流,怕泥石流,怕出现在家门口的陌生人,怕没由来的发烧,怕没有操作员的电梯,怕空荡荡的酒店走廊。恐惧的原因显而易见:这些东西可能会伤害她。问个问题:如果我们和孩子能清楚地了解彼此,这恐惧会消失吗?是我们俩的恐惧都会消失,还是只有我的恐惧会消失?
成年后的我们,便渐渐淡忘了童年时的沉重与恐惧。
金塔纳说,有个人总是出现在她的噩梦中,被她称为“破碎男”的一个神经不正常的人。她时时提起这个人,事无巨细地向我描述,让我经常忍不住去她二楼窗外的阳台上看这个男人是不是真的存在。“他穿着一件蓝色工装衫,像修理工,”她不断对我重复这个形象,“短袖的。衬衫上总是写着他的名字,就在右手边。他名叫大卫、比尔、史蒂夫,反正就是那种很大众化的名字。我猜这个人大概在五十到五十九岁之间。戴着一顶棒球帽,就是道奇队那种帽子,海军蓝的,上面有‘GULF’的字样。棕色皮带、海军蓝的裤子,黑皮鞋擦得亮闪闪的。他对我说话,声音非常深沉:你好,金塔纳。我要把你锁在车库里。五岁以后我就再也没梦到过他了。”
她说“我猜这个人大概在五十到五十九岁之间”时,我意识到,自己对这个“破碎男”的恐惧,毫无疑问和她一样。

说到恐惧这个问题。
起初动笔写这些文字时,我本以为主题会是孩子,我们拥有的孩子,我们希望自己拥有的孩子;我们依赖孩子依赖我们的感觉;我们鼓励他们永远都是孩子,不要长大;我们对他们的了解,似乎比他们那些最淡漠的点头之交还要更浅;而我们对他们来说,也是同样难以读懂。
我们总是全情投入地为彼此付出,所以永远看不清彼此。
我们或者他们,只是想一想彼此的死亡、疾病,甚至只是老去,都难以忍受。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令金塔纳饱受折磨的恐惧之一,就是怕父亲约翰去世,世界上只剩下她一个人来照顾我。
她怎么可能会觉得不是我来照顾她呢?我从前总是问这个问题。
现在我反过来问:她怎么可能会觉得我能照顾她呢?
她见证过我特别需要照顾的样子。
她见证过我无比孱弱的样子。
这种焦虑属于她,还是属于我?
我了解到这种恐惧,是她暂时撤了呼吸机的时候,反正是在某个重症监护室,我也记不得是哪一个了。
恐惧的并非失去的东西。
恐惧的是,即将失去的东西。
内容简介
本书是琼·狄迪恩的代表作,为了纪念逝去的女儿,她写就此书。
狄迪恩在书中探寻生与死、情感与自我之间的关联:是否我们从根本上无法互相了解,甚至对彼此一无所知?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同,使我对你的痛苦甚至离去的预兆置若罔闻?是否即便没有生死的阻隔,我们也不曾真正亲密? 关于失去,关于悲伤,关于幸与不幸,关于婚姻、孩子和记忆,关于人们愿意或不愿意面对的一切……
她说,我们需要学会接受失去,就像接受偶尔的急流旋涡和每日的潮起潮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