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
朱利安·巴恩斯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与马丁·艾米斯、伊恩·麦克尤恩并称英国"文坛三巨头",曾四度获得布克奖提名,并在2011年摘得。他的妻子帕特·凯伐纳是著名的文学经纪人,是他创作生涯的见证者,也是他所有作品的促成者。然而,这对相依相伴、同悲共戚的爱侣却随着2008年凯伐纳的去世而失散了。伤痛中的巴恩斯用文字书写下对共同生活了三十年的爱妻的纪念,同时也在死亡与分别中重新咀嚼那些有关人生的复杂命题。
欧茨评价这本《生命的层级》是"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一个人的离世,以个体事件阐释失去、痛楚、悼念以及巴恩斯称为'孤独'问题的普遍意义。"本文节选自书中第三部分"深度之失",催人泪下,又引人深思。

巴恩斯与凯伐纳
在人生早期,世人被粗略地分为两大类:有过性生活者和尚无性生活者。后来,划分为尝过爱的滋味者和未尝过爱的滋味者。再后来——至少,如果我们够幸运(或者,不妨说,很倒霉)——划分为已忍受悲痛者和尚未忍受悲痛者。这些划分是绝对的,就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
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年。我们相遇时,我三十二岁;她去世时,我六十二岁。这三十年,她是我的生之所在,心之所向。她讨厌衰老。年方二十,她就认为自己活不过四十。我却满心憧憬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看时光变慢,我们一起追忆往事。我能想象自己无微不至照顾她,我甚至能够——但其实没有——想象自己像纳达尔(注:19世纪法国摄影先驱)那样,学着温柔护士的模样,轻抚她鬓角的白霜(她憎恶这种依赖,于我而言却无关紧要)。
恰恰相反,从夏至秋,从确诊到她离世,在这短短三十七天中,伴随我的是焦虑、惊慌、担忧与恐惧。我尽力不回避,始终直面这一切。结果呢,我既癫狂又清醒。多少个夜晚,当我离开医院,我发现自己在幽怨地凝视着公交车上归家的上班族。他们怎么可以如此懒懒散散、无知无觉地坐在那儿,一个个摆出一副无动于衷的神情,而这世界即将改变了呀?!
死亡,一件既平庸又独特的事情,我们都不擅长应对。我们已不再能够赋予它更多的内涵。正如E.M.福斯特所言,"一场死亡也许可以说明自身,但并不能阐释另一个人的死亡"。因此,哀痛转而变得难以想象:不仅是它的时长和深度,还有它的色调和纹理,它的幻象和谵妄,它的屡屡发威。还有它起初的震荡:你突然跌落冰冷的北海,浑身却只有一件滑稽的软木浮力夹克助你求生。
而你一旦被卷入这一新现实,就根本无法未雨绸缪。我就认识一个人,她心想——或希冀——她可以做到。她的丈夫罹患癌症已久,几近奄奄一息;她很务实,提前就要了一份书单,收集了有关亲人亡故的所有经典文章。但是,当那一刻真正来临时,一切准备都功亏一篑。"那一刻":你感觉已熬过了漫漫数月,但经查验证明,原来不过才寥寥几天。
很多年,不经意间,我会忆起一位女作家在比她年长的丈夫去世后写下的文字。在经历悲痛的过程中,她承认,灵魂深处有个声音在隐隐地向她透露真相:"我自由了。"当轮到我时,我清楚记得这一点,我害怕那提词者的低声细语听起来像是一种辜负。但是,此音,此语,都没有听到。一份悲伤并不能启迪另一份悲伤。
悲痛,犹如死亡,既平庸又独特。这一比喻也是挺平庸的。当你换了车子的牌子时,你突然注意到马路上还有很多同样牌子的车辆。它们之前被视若无物,此刻,它们受到了关注。当你失去伴侣时,你突然注意到世间所有的孀妇和鳏夫都在向你奔袭而来。以前,他们或多或少是隐而不见的,而现在,其他驾车者和非丧偶者依然对他们视而不见。
如所预料,我们悲痛哀戚。那好像也是很显然的,可是,在我们这一时代,没有任何东西显得或者感觉是一目了然的。一位朋友去世了,撇下妻子和一双儿女。他们会有何反应呢?妻子着手重新装饰房子;儿子走进父亲的书房,直到读完父亲生前留下的每条信息、每份文件和每一物证才走了出来;女儿制作了几盏纸灯笼,她要让它们漂浮在将要撒下父亲骨灰的湖泊上。
另一个朋友在国外的机场,因为行李传送带引发的事故,突然失去了生命。事情发生时,他的妻子走开去取小推车。回来发现一群人挤在一起,围着什么东西。她以为大概一件行李突然打开了。然而事实是,"打开的行李"正是她的丈夫,已经没了呼吸。一两年后,我的妻子去世时,曾写信给我:"人生来就斤斤计较,一个人对你有多重要,就能对你造成多大的伤害。因此,我认为,在一定程度上痛苦值得细细品味。"她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很长时间里,我一直将她的信件留在书桌上。说实话,我并不相信有朝一日我会享受伤痛,但那时,我还在苦难的入口处。

我早已明白只有陈词滥调才能表达古已有之的情感——死亡,伤痛,悲怆,伤心,心碎。即便在当今,它们也是无法推脱逃避,或是有药可医的。悲痛是人的一种天性,而不是一种医疗状态。也许有良药可以帮助我们忘记伤痛,忘记一切,但是,任何药物都无法治愈伤痛。悲痛中的人并不是伤心欲绝的,他们伤心得恰如其分,一分不多,一分不少,只是根据那件事物在心中的重要程度选择了同样程度的伤心。
"走了"是我特别不愿意使用的一个委婉性动词。"听到你妻子走了,我很忧伤。"尽管"死"这个词可能已经被你说滥,但你实在不必将它强加于人。不过,"死"有另一种折中的说辞。在我和她通常会一同出席的一场社交活动中,一位熟人走上前来,对我说:"她没来,我很想念她。"我觉得,这儿,missing这个词就用得很恰当,它既表示缺席,又表示想念。
伤痛形形色色,并不能互相解释,但有可能互相重叠。因此,在伤痛的人群中间会形成"伤痛气场"。你的内心世界,只有你自己清楚——尽管你也知道不同的事物。你的身子穿过一面镜子,就像在某部科克多电影中一样,发现自己身处一个被逻辑和模式包围的异次元。举个小例子。我妻子去世的三年前,我的挚友,诗人克里斯托弗·里德失去了伴侣。他写了很多诗歌,都是关于妻子离世以及这带给他的创伤。在其中一首诗里,他描述了生者拒绝已逝者的情形:
可是我也遭遇了宗族的清规戒律,
而且举止粗鲁,
在餐桌闲谈中唤起我死去的妻子。
一阵沉默之音,
一阵心照不宣的恐惧和惊愕,飘然而至。
初读这几行诗,我不禁感慨诗人结交的朋友多么奇怪。我也在想:诗人大概一点儿都不认为自己表现粗鲁,对吧?后来,我的妻子去世了,我才一下子明白过来。我过早下了断言(或者,准确地说,我混乱的脑袋为我下了这个断言)。我决定在任何"我想要"或"我需要"的时刻毫不避讳地提起我的妻子。
聊起有关她的往事不过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尽管"正常"这个词本身听起来就很别扭。我很快明白,伤痛如何将悲痛的人区分开,如何重组他们,明白朋友是怎么经受考验的,为什么有些人及格了,有些人却没有。因为经历过同样的伤痛,老朋友之间的情谊可能会加深,也可能刹那间显得无足轻重。淡化伤痛,这一点年轻人做得比中年人好,女人做得比男人好。这一事实,既是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毕竟,我们通常认为性别相同、年龄相仿、婚姻状况接近的人更能理解对方。多么幼稚啊。
我记得,曾与三个年龄相近的已婚朋友在一家餐馆"共进晚餐,边吃边聊"。他们与我的妻子相识多年——也许加起来恐怕有八九十年。而且,如果别人问到我的妻子,他们个个都会说他们很爱她。在饭桌上,我提到了她的名字,却没有一个人接过我的话。后来,我再一次提及她的名字,同样徒劳无功。第三次,我甚至故意刺激他们。我很生气,也很惊讶,他们这根本不是礼貌,而是怯懦,他们甚至不敢提她的名字,连续三次漠视她的名字,他们这样做太让我失望了。
……
你无从得知,在别人眼中,你是怎样的人。你的自我感觉与你的实际情况也许相同,也许不同。那么,你的自我感觉是什么呢?试想你从几百英尺的高度坠落时一直保持清醒,着陆时,你的双脚落在了玫瑰丛中,接着整个身体跪倒在地。这样巨大的冲击使得体内的器官穿孔破裂,从体内崩裂而出。这是我们的感觉,为什么它看起来却截然不同?难怪有些人意欲转向一个更"安全"的话题。他们并不是逃避死亡,也不是逃避死去的她,而是在逃避活着的你。
我不相信我在有生之年还会见到她。不再相见,不再倾诉,不再抚摸,不再相拥,不再倾听,不再欢笑。也不再等待她的脚步声,在敞开的门后微笑着,将她拥入怀抱。我也不相信待我死后还会与她相遇。我坚信死了就是死了。

有人说悲痛是另一种形式的暴力,前提是自怜是无可非议的。有人说,悲痛仅仅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思考。还有人说,他们为生者忧伤,因为他们才是要经历彻骨悲痛的当事人,而逝者却无需承受这份伤痛。这些方法试图将悲痛最小化,从而走出悲痛。面对死亡,方法还是这样。
我承认,有些悲痛是自作自受——瞧,我已失去挚爱,瞧,我的生命已何等消逝——但从一开头,这悲痛更多的是洒向了她:既然她已失去了生命,就该寻根问底,看看她失去的到底是什么。她的肉体,她的灵魂,她对生命的强烈好奇。常常,我会有这样的错觉,仿佛生命本身才是最大输家,它才真切感受到丧亲之痛,因为它不再拥有她对生命本身的强烈好奇。
别人对事实、对真相、对逝者名字的逃避害怕,往往会激怒正处于悲痛之中的人。可是,悲痛之人他们自己又会说出几多真相呢?他们自己不就常常共谋逃避吗?因为,他们跌入的真相漩涡,不仅淹没了他们的膝盖,还蒙蔽了他们的心灵和头脑。这些真相有时无法辨识,有时即使能够辨识,也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记得有一个朋友在做完胆结石的切除手术后,说那是他这辈子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他是一名记者,惯于描情状物。我问他能否描述这份痛苦。他盯着我,回忆涌上心头,眼泪也浸湿眼眶,而他,一直沉默着。他词穷了,找不到描述这种痛苦的最佳词汇。而我们的谈话也陷入了沉默。正当我悲痛欲绝时,一位熟人在众人面前问我:"呃,你好吗?"我连连摇头,暗示他这不是适宜的场合(当时正在吃午餐,闹哄哄的)。他不依不饶,好像在一味地提炼问题:"不,你一个人过得怎样?"我手一挥,示意他滚开。再说啦,那会儿我真觉得自己一个人过得不好,完全不在状态。我大可以说一句,譬如,"有点时好时坏吧",让这个难缠的问题过去。那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英国式答案。只不过呢,悲痛之人难得感知到它的循规蹈矩,甚而英式风范。
你自问,在这纷乱的思念中,你对她有多思念?对携手走过的岁月有多思念?对她使我之为我的品质有多思念?对单纯的陪伴有多思念?或是对不那么简单的爱情有多思念?你自问,幸福记忆里面的幸福是什么?既然幸福是由某些共享的东西构成,那么这到底是怎么起作用的呢?独自幸福——这听上去措辞矛盾,就像是天方夜谭。
……
我对她的哀悼,简单而绝对。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刚开始,有些念头会顿时涌入脑海:"无论动与静,我都在思念她。"日复一日,我不断重复这句话,以此证明我是何许人,我身处何方。驱车回家时,我会大声呐喊:"我要回家了,就一个人回家,回到一个人的家。"失意降临、物品破碎或随意搁置时,我就安慰自己:"比起失去她,这一切根本不算什么。"我几乎没有想过这种悲痛中生出的唯我论有何层次与不同,直到一位女性朋友跟我说她嫉妒我的悲痛。"这究竟是为什么?""因为,如果X(她的丈夫)去世了,我的情况会更加复杂。"她没有细说,实际上,她也没有必要细说。与她一番对话后,我有了新的想法:也许,在一定程度上,我在从容地面对妻子的离去。

第一次与她分别的时间超过两天,是我去乡下采风写作。我发觉,除去所有意料之中的思念,我在道德上也存有深深的相思之情。这让我颇感惊讶,但其实并没什么好惊讶的。爱也许不会将我们引向心中的彼岸,但是,无论结果如何,爱应该是肃穆与真相的召唤。如果爱不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它没有这样一种道德效应——那么,爱不过是一种矫揉造作的欢愉。然而,悲痛——爱的对立面——在道德空间却无立足之地。为了求生,我们被迫采取守势,蜷居一隅,而我们因此变得更加自私自利。那里绝不是"一览众山小",仅仅是"一叶障目"。在那里,你甚至听不到自己的呼吸。
以前,看到报纸的讣告,我会百无聊赖地计算我与死者的年龄差:想着多了X岁(或者是少了X岁)。现在,看到讣告,我会转而研究死者的婚龄。我会嫉妒婚龄比我长的。我很少想到:在多出来的每一年,他们的婚姻生活也许夹杂着腻烦或束缚。而我对那种婚姻毫无兴致;我只想赏赐给他们幸福的岁月。再后来,我开始计算别人守寡的时间。譬如,尤金·波利,生于1915年,卒于2012年,电视遥控器的发明者。在他讣告的最后,是这样说的:"波利之妻卒于1976年,他们携手走过三十四个春秋。"天哪!虽然他婚龄比我长,但他竟寡居了三十六年。三十六年的苦中作乐?
……
起初,出于惯性、爱以及对模式的需求,你继续重复做着你和她一起做过的事情。很快,你意识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你独独一人重复着之前两个人共同做过的事情,但没有了她你就思念她;或者,你开始做新的事情,之前你从没跟她一起做过的事情,而你却以不同的方式思念她。你强烈感受到已失却了两人共同的词汇,失却了比喻、逗弄、伤人话、圈内笑话、傻话、娇嗔和恋人絮语——所有这些晦涩的所指深植于记忆中,但一旦向局外人解释就毫无价值。
天下所有夫妻,即使是最放纵不羁的,都会在共同的人生中建立起模式,而这些模式是有年轮的。于是,第一年就像你业已习惯的岁月的一幅底片像。这一年,不同于事件迭出的往年,你无所事事,百无聊赖:圣诞节,你自己的生日,她的生日,相识纪念日,结婚纪念日。而这一切与新的纪念日相交重叠:恐惧降临的日子,她摔倒的日子,她住院的日子,她出院的日子,她去世的日子,她出殡的日子。
熬过第一年,你以为第二年不会比第一年更糟糕,也以为自己已为来年做好了准备。你以为你已经与所有的苦痛相遇,在这之后,生活只剩下这些苦痛的重复上演。可是,凭什么苦痛的重复就意味着苦痛的减少呢?起初的一次次苦痛的反复,促使你思忖未来年岁中所有的重复。悲痛是一幅爱的底片像。倘若爱会在岁月的流逝中积累沉淀,为什么悲痛就不可以呢?

……
过了几个月,我鼓足勇气,开始出入公众场合,去看戏观歌剧听音乐会。可我发现我对剧场门厅有了恐惧之心。恐惧的倒不是门厅的空间,而是门厅里聚集的人群:激动难抑、满心憧憬地期盼着享受美妙时光的"正常人"。我无法忍受嘈杂的噪声和宁静如常的神情:一辆又一辆满载乘客的巴士对我妻子的离世无动于衷。我得劳驾朋友们在戏院门外等候我,他们像领孩子那样将我引到座席上。一进戏院,我就感到安全了;灯光暗下,我感到更安全了。
……
最初的时候,我不可能相信(但那些可能性去哪儿了呢?)梦境比记忆更加可靠,更加安全。在梦里,她的一颦一笑都更像她自己。我一向知道,这就是她——她冷静而有趣,快乐而性感,因而,我也这样。这一梦境,很快便演变成了一种常规模式。我们在一起,她显然身体康健,因此我想——或者确切地说,由于这是一场梦,我知道——要么她是被误诊了,要么奇迹般地康复了,要么(最起码)不知何故死亡被推延了几年,我们可以继续一起生活。这一幻想持续了一段时间。可是,我随后想——或者确切地说,由于这是一个梦,我知道——我一定是在做梦,因为,事实上,她已经死了。我醒了过来,感到非常快乐,因为我曾怀有这一幻想,但同时又嗒然若丧:真相终结了幻想。于是,此后我再也不想重入这一梦境。
某几个夜晚,熄灯之后,我提醒她最近她都没有出现在我的梦里,于是她就常常向我奔来,以此回应我(确切地说,"她"出现在梦里,以此"回应"我——我每时每刻无不认为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而已)。有时候,在梦里我们亲吻;这样的场景总有一种轻松笑意。她从不指摘或责怪我,也不会让我觉到愧疚或失职(不过,由于我把这些梦视为一厢情愿,所以我也必须将它们视为谋求私利,甚至自鸣得意)。或许,之所以有这些梦,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已有够多的惆怅和自责。然而,它们永远是慰藉的源泉。
因为,每当我试图从回忆中探寻的时候,我总是以失败告终。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无法回忆她死亡前那一年的场景。我能忆起的只是一月到十月:三个星期待在智利和阿根廷,在智利的南美杉树林里度过了我的第六十二个生日,与我做伴的是树林里那些欢呼雀跃的阿根廷啄木鸟。然后回归正常生活,之后是在西西里岛徒步度假,以及一些我们最后的共同回忆:巨大的茴香和满山遍野的野花,安托内罗的一幅画作和一头制成标本的豪猪,世界维斯帕周末一个满是高尔夫球名流的渔村。但此后,在我们归来的路上,恐惧加剧,崩溃突如其来。我记得她渐渐衰弱的每一个细节,她在医院里的时光,回到家、死去、安葬的时时刻刻。
但是,我的回忆无法退回到一个月以前;我的记忆似乎已灰飞烟灭。她的一位丧偶的同事安慰我,说这很正常,说我的记忆定会回来,可是,我的生命里鲜有可让我确信的事,没有任何固定的模式可循,因此,我心存疑虑。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我很想知道这一切究竟为什么会发生?这让我觉得她再一次从我身边悄然溜走:我先是在当下失去她,然后又在过往里失去她。记忆——脑海里的影像档案馆——瞬间崩塌。

……
尽管如此,我还是清楚地记得最后的事。她读的最后一本书。我们一起去看的最后一场戏(电影、演唱会、歌剧、艺术展等)。她喝下的最后一杯红酒。她买的最后一件衣服。最后一个周末。我们最后睡过的不是我们自己的床。最后一个这个,最后一个那个。我写下的最后一篇让她大笑的文章。她描述自己的最后的文字。她最后一次签自己的名字。她回家时我最后一次为她弹奏的曲子。她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她说的最后一个字。
……
事实上,一个人死了可能只意味着他不再活着,但并不表示他已不复存在。
于是我不断地跟她说话。我觉得这既必要又顺理成章。我跟她讲我正在做的事情(或者我一天中的所作所为);我一边开车一边向她指出一路的景致;我说出她的种种回应。我让我们的喁喁私语保持活力。我取笑她,她转而取笑我;我们背诵台词。她的声音让我平静并给我勇气。我越过桌面,看着一帧小小的照片,照片中的她一副稍稍揶揄的神情,我回答她的揶揄,不管她揶揄什么。简短的讨论后,平庸的家庭事务也顿时灼灼生辉:她认定浴室地垫实在丢人现眼,该一扔了之。
外人也许会觉得这是个古怪或"病态",抑或自欺欺人的习惯;然而,顾名思义,所谓外人乃是未曾尝过悲恸滋味之人也。我自然而然地很容易将她外化,因为迄今我已将她内化了。这是悲恸的悖论:如果说这四年没有她我也好好地活了下来,那恰恰是因为她陪伴了我四年。她还那么活跃,证明了我先前的悲观论断毫无道理。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悲恸可能只是一重道义空间。
尽管我和她交谈时她总是有问必答,但我的口技是有限的。我还记得——抑或可以想象——对以前发生的或目前被不断重复的事情她会说些什么。但我说不出她对新近的事情的反应。在她走后的第五个年头的开初之时,我们密友的儿子自杀了,小时候他是个温柔、聪明的男孩,后来成为一个文雅而忧心忡忡的男人。虽然深陷在悲痛中,我发现自己困惑不已,数日来无法完全回应这突如其来的死讯。后来我才明白个中缘由:那是因为我无法向她讲述,无法听到她的回复,无法重现和比对我们共同的记忆。失去了她,我也就失去了各种伴侣,在所有其他种种伴侣中,现在又添上了一员:一位可以同悲共戚的人。

……
你期待何时可以"度过悲伤"?悲痛者自己是无从得知的,这是因为,现在,时间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度量了。四年后,有人对我说:"你看上去开心点了"——比"好些了"更胜一筹。更有胆大者说:"你再找了一个?"仿佛那显然是唯一的出路。对有些局外人来说,确实是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尽然。某些好心人想要帮你"解决";而其他人仍然认定那对夫妇,即使他们已不再存在,而对那些人而言,"再找一个"是唐突无礼的。"那感觉就像是你爸再婚一样。"我的一位年轻朋友说。可是,我妻子的一位美国老朋友在她去世几星期后跟我说,按数据统计,婚姻幸福的人往往比那些不幸福的人更快地另觅新欢:通常不出六个月。她这样说是有意为之,颇含鼓励之意,但这一事实——如果是事实的话(或许它只适用于美国,在这个国家,情绪乐观是基本义务)——让我震惊不已。那显得既完全符合逻辑又完全不合逻辑。
四年后,同样是这位朋友,说:"她已成为过去的一部分,我痛恨这一事实。"如果对我来说这不是真的,那么,语法,就像其他东西一样,已然开始变了:她其实并不存在于现在时,也不完全存在于过去时,而是存在于某一居中时态,即过去-现在时。或许,这就是为何我喜欢听到哪怕一丁点儿关于她的新消息:一段过去未曾报道的记忆,一条她多年前给的忠告,一段日常动画中她的闪回。如果她频频出现在别人的梦境里,我会替她感到高兴——她的行为举止,她的衣着打扮,她的饮食习惯,现在的她与从前的她是何等接近;还有,我是否就在她身旁。这些稍纵即逝的时刻令我兴奋,因为它们匆匆地将她重新固定在现在时态,将她从过去-现在时态中拯救出来,稍稍推延那一不可避免的遁入过去的历史中。
……
差不多在三十年前,在一部小说中,我竭力想象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成为鳏夫后的情形。我写道:
她死的时候,你并不吃惊。爱的一部分已经准备死去。她死了,你就更加确定了对她的爱。你没弄错。这只是全部事情的一部分。
随之而来的是疯狂。接着是孤独:并非是你所预想的那种浩渺的孤寂,也不是丧妻后耐人寻味的悲恸,就只是孤独而已。你期待着某种几近地质般的东西——身处倾斜的大峡谷中的眩晕感——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只是感受到一份彻痛,如同工作一般稀松平常……(人们说)你一定会从悲伤中走出来……没错,你确实走了出来。但并不是像火车驶出隧道那样,呼啸着穿过山丘,再次沐浴在阳光里,随后又伴着轰隆声驶入英吉利海峡;你从悲痛中走出来,就像一只海鸥从海面的浮油中逃离;你终生无法摆脱身上的沥青,而那脏了的羽毛也将与你永久相伴。
我在妻子的葬礼上读了这段话,十月的白雪覆盖着大地,我的左手触摸她的棺木,右手捧着一本摊开的书(这本书是献给她的)。我小说中的鳏夫过着另外一种生活——怀着另一种情爱——一种与我截然不同的鳏居生活。但是我太过悲伤,以至于只能断断续续地用几个词表达一句话的意思,同时惊讶于自己选词的精准。只是到了后来,我才开始小说家式的自我怀疑:或许,与其说那是为我小说中的角色虚构一份正当的悲痛,不如说是在预测自己将来会有的感受——而这就简单多了。
三年多来,我一直以同样的方式,按照同样的情节梦见她。然后,我做了一个千秋大梦,它仿佛为我的这一夜间辛劳做了一个了断。但是,正如所有美好结局一样,我并没有看到它实现。在梦里,我们还在一起,在某个开阔的地方一起做事,那样开心——所有的一切都是我曾经习以为常的——突然,她意识到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必定只是一场梦而已,因为那时她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本文节选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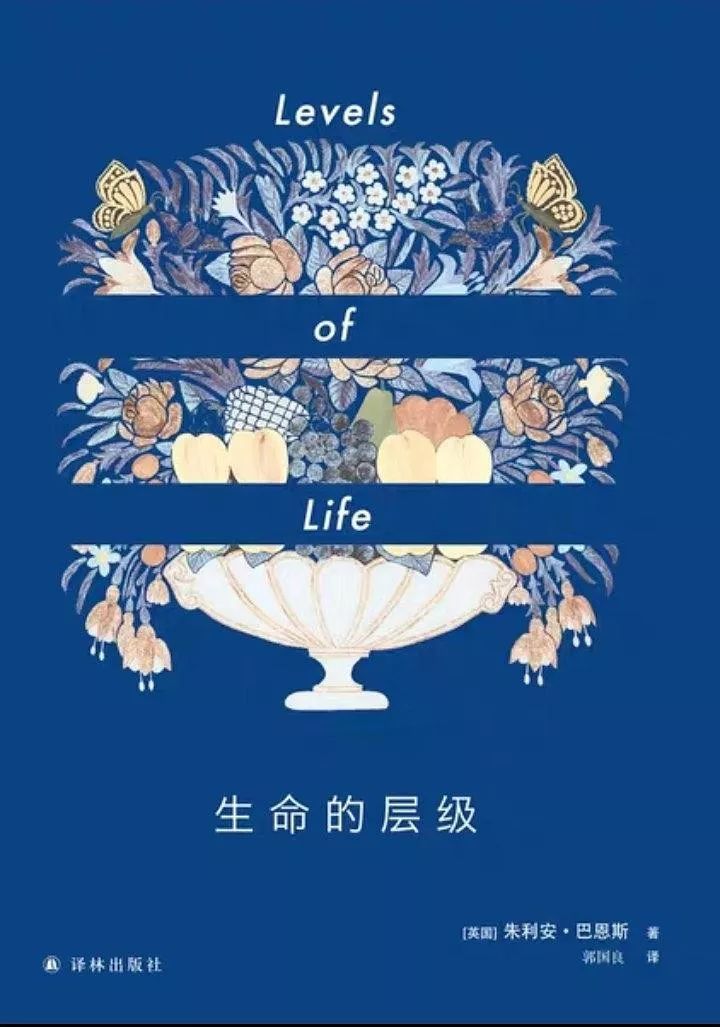
生命的层级
作者: [英]朱利安·巴恩斯
译者: 郭国良
译林出版社201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