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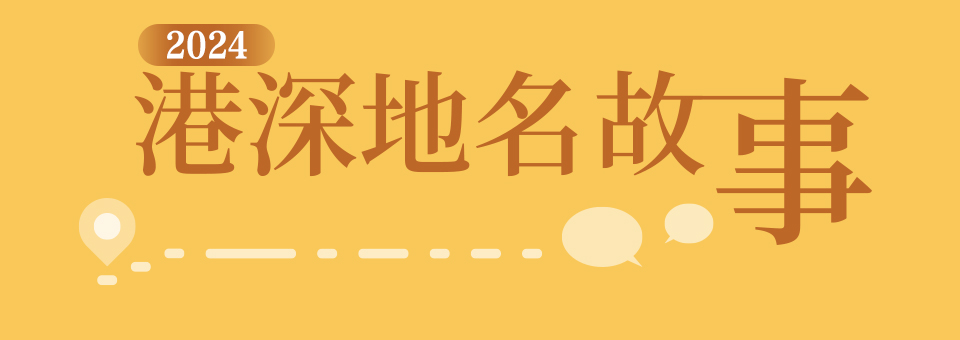
作者:尹昌龍
要講改革開放以來深圳村莊的變化,最神奇的莫過於漁民村了,從苦難的打魚人到全國最早的一批萬元戶村,從「洗腳上岸」到「洗腳進城」,漁民村人身份變化巨大,而這個變化背後藏着的是一個城市、一個時代的奇跡。
從水上向岸上漂移
漁民村位於深圳市羅湖區的西南部,地處羅湖火車站以西,深圳河以南,西臨布吉河口,北靠春風路高架橋,村子面積不大,只有0.25平方公里。這是今天的漁民村,而回到過去,漁民村在岸上恐怕只算是立錐之地。講深圳的原住民,都要講到廣府系或客家系,這是主流人群,其實還有一個小小的族群,不經意間就會被遺忘,那就是疍家人。疍家人完全生活在水上,船即是家,生計的主要來源就是打魚,屬於漁民。今天從事非遺工作的人很想恢復疍家人水上婚禮的生活場景,以喚起對往日生活的回憶。非遺工作者的想法無疑是想在疍家人以往的日子中找到浪漫,而遺憾的是,在實際生活中,從漁民村走過的歷史來看,只有「苦難」二字。即使到了今天,老一輩的漁民村人總是把自己這群人叫「水流柴」,意思是水裏流過的樹枝,在水上飄飄蕩蕩,完全是無所歸依的樣子。很重要的原因在於,他們幾乎無法上岸,無法過上穩定的生活。他們面對的人生不平等超乎想象,如上岸不准穿鞋,喜慶不准張燈結綵,更不得與陸上人通婚。非遺工作者說的水上婚禮,即使在舊時代恐怕也非光芒四射。還有一條是文化權利的缺失,就是不能參加科舉考試,這比現在不能參加高考還要殘酷,疍家人幾乎沒有上升通道了。當然,這一條據說後來廢止了,疍家人好歹打開了人生的一扇窗。印度盛行種姓制度,處在社會最底層的就是賤民,也許疍家人當年就是這樣一群「賤民」。

20世紀50年代的漁民村村民舊居。 資料圖片
要找這群「賤民」的根,恐怕還要找到東莞企石河畔的州寮村了。當年州寮村的人打魚為生,後因颱風和魚霸,有的村民就順着東江而下,經虎門入珠江口,一路漂泊到深圳羅湖一帶,見深圳河魚群豐富,便成了深圳河上的「水流柴」了。一開始是落在深圳河上的「犁頭尖」,這塊新大陸四面環水,像個島嶼,後來再靠近陸地,用水草、竹竿搭建寮棚,這就是他們最初的居所了。新中國成立後,漁民村在深圳河邊又建起了簡易的碼頭。從犁頭尖開始,漁民村人也一步步向岸上遷移。1953年,漁民村用150萬從蔡屋圍村買了兩塊約30畝的魚塘,同時在魚塘南邊開墾了一塊約60畝的荒地,買地的契約現在都還保存着。其實到今天,漁民村人仍然感謝蔡屋圍村出手相助,不然他們可能還在愁着怎麼上岸呢。漁民村人在他們的博物館中,展覽着當年一家子蝸居的小船,想起「煮魚當糧那識米,船頭蹲唱鹹水歌」,想起「世上最苦黃連樹,世間最苦水上人」,漁民村人對改革開放帶來的新生活永遠有一種感念。

20世紀80年代初的深圳漁民村。
中國首個萬元戶村
講起漁民村人最大的榮耀,恐怕在於三位黨和國家領導人都親自到漁民村視察,這在深圳所有村落和社區中都絕無僅有。1984年1月25日,鄧小平視察漁民村;2010年9月5日,胡錦濤視察漁民村;2012年12月8日,習近平視察漁民村,這恐怕是漁民村人永遠值得驕傲的往事了。而漁民村也是媒體和社會關注的焦點,不僅接待了一批又一批的參觀者,而且上央視這樣的主流媒體也是屢見不鮮。
漁民村能引起如此廣泛的關注,最重要的恐怕還是源於其經濟變遷和生活的變化。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第一個萬元戶村就是漁民村。1981年,漁民村集體收入6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全村35戶,160口人,人均2571元,每戶平均1.06萬元,在全國率先成為萬元戶村。1984年,鄧小平考察漁民村,當聽說漁民村村民月收入400多元到500元,曾經開玩笑說,這收入比我的工資還高。

第四屆中國設計大展的中國元素——漁民村。 資料圖片
講漁民村的變化,當然首先是經濟的發展、收入的提高。能成為萬元戶村,這也得益於開放的市場和漁民村人的經商頭腦。也許是窮則思變的道理,漁民村求新求變的首先就是生產方式和經營方式。漁民村的經營大體分幾個階段。早期買了大船出海捕魚,從河到海,魚獲大大增量,當然,這還是在上世紀60年代。再後來是捕魚養魚的結合,蔡屋圍人出魚塘,漁民村人出技能,雙方開展合作。再後來,進入改革開放年代,漁民村首先集資買了推土機,自己開辦魚塘,開始大規模養魚。當時包括香港在內,市場需求量大,漁民村人賺得盆滿缽滿。然而漁民村最大的商機則來自於建築市場,當年的深圳經濟特區就是一個大工地,漁民村人或者買泥頭車跑運輸,或者從深圳河裏採沙解決建築材料所需。這其中,國貿大廈、深圳體育館等的建設都用過漁民村人供應的沙子。當時沙子市場需求強勁,漁民村人想不賺錢都難。村民不僅收入提高了,後來還住進了自建的別墅,添置了冰箱、彩電、音響等現代家電。這是當時內地家庭可能想都不敢想的。

如今的漁民村文化廣場,幼兒園的孩子們正在訓練武術。 資料圖片
當然,漁民村的幸福還不止經濟收入增加,村裏建起了幼兒園、文化廣場、村史館。當年連科舉考試都參加不了的疍家人,如今有了自己的大學生、碩士和博士。當年有人從漁民村逃港,而現在不少香港人在漁民村安居下來,差不多佔到了總人口的1/10。鄧小平當年說,這樣的生活,內地農村可能得要100年吧。而胡錦濤希望,漁民村人過得更富裕、更文明、更安寧。習近平視察漁民村時指出,漁民村的生活是一個巨大的跨越,他希望漁民村人靠自己勤勞的雙手過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特別要說到的村史館,漁民村人細致地梳理了村子的發展和變化,並作了生動的展示,有圖文、有場景、有視頻,系統性和直觀性非常強。村史館2014年建成開館,到了2020年又進行了整體改造與提升。展覽分為四個部分:「當家作主—深圳解放漁民上岸」「共同富裕—全國首個萬元戶村」「和諧社區—舊村改造成功典範」「先行示範—新時代新羅湖新漁村」,把漁民村的歷史全盤講清楚講生動了。
舊改背後的新體制
講漁民村的變化,不止是村民的收入,還有村子的建設。當年村集體經濟飛速發展,形成了豐厚的積累後,村裏在1982年就建起了33套獨立別墅,全是兩層小洋樓。以前是一家子住在1.5米寬、5米長的小船上,水邊臨時搭起的也都是水草寮棚。而如今住進了別墅,漁民村人最感謝的還是改革開放。
但變化還不止於此,隨着房屋出租帶來的收入越來越多,村民們開始了亂搭建,原本是兩層樓,搭建下來就變成了四五層樓高,漁民村成了名副其實的「握手樓」天下。隨之而來的是嚴重的安全問題,亂搭電線、地基超載,安全成了最頭疼的事。不僅是「握手樓」,還出現了「比薩斜塔」,樓體傾斜、牆體開裂,似有搖搖欲墜之勢。實際上,深圳的城中村在急劇膨脹的外來人口衝擊下,幾乎都避免不了亂搭建的現象,但漁民村人解決問題的決心和行動,到現在都值得學習。村裏經過研究,決定將這些亂搭建的別墅全部推倒,進行大規模的舊改。本來可以收取可觀的租金,而現在的改造則需要從銀行貸款,但這些困難都被一一克服。2004年,漁民村新村落成,盛大的慶典上擺出了188道大盆菜,有2000多名嘉賓參與分享,可謂盛況空前。

漁民村與香港隔河相望。 資料圖片
從「握手樓」到花園式小區,如此大規模舊改,需要的是強大、統一的意志,否則,各自為政、各為其利,舊改也將無從談起。更進一步講,新村實行的是統一出租、統一管理,更規範、更專業、更科學,同時也保證了村民的合理收益。沒有對一戶一幢這種傳統村居模式的革命,就不可能有大規模高起點的規劃與建設。對於村民來說,有統一的意志,恐怕也是得益於該村股份公司,從挨家挨戶的入股到股權的內部流轉,從「按人所有」到「按份所有」,以股權為紐帶,村股份公司實現了集中統一的利益增長與管控。村股份公司在實現農村城市化以後城中村和城市社區的管理中,功不可沒,否則,像這樣的集中改造,無論如何也無法實現。村民對漁民村股份公司充滿感情,當初公司要用「裕豐」的名字,但最終還是用回了「漁豐」兩字。雖然漁民村人的身份早已發生變化,但這份記憶揮之不去。
當然,已經不是漁民的漁民村人說起往事,也不是沒有遺憾,至少有兩條:一是不用再打魚了,而村民單靠出租房屋就可以過上小康的日子,這總覺得有些不踏實,應該有打魚那樣的實業支撐;二是當年的深圳河,他們可以自由地漂行水上,而如今由於邊境鐵絲網的阻隔,無法再往河上走,河還在那裏,但離村民卻更遠了。
現實生活與昔日記憶仍藕斷絲連。
作者簡介
尹昌龍,北京大學文學博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專家。現任深圳市政協文化文史委主任、深圳市決策諮詢委員會專家委員。曾任深圳市閱讀聯合會創會會長,深圳市文化局特區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文體旅遊局(新聞出版局)副局長,深圳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主要著作有:《1985:延伸與轉折》《重返自身的文學》《別處的家園》《全球化的煙花》等,主編《深圳全民閱讀發展報告 2016、2017、2018、2019、2020、2021》,編著《文化深圳從閱讀開始》《以書築城以城築夢:深圳書城模式研究》等,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優秀出版人物、全國新聞出版行業領軍人才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