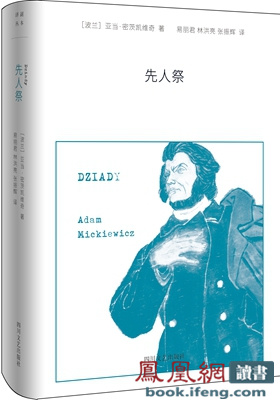1968年1月,波蘭人民共和國,冰霜覆蓋首都華沙。市中心的廣場上,華沙民族劇院,正在上演波蘭戲劇史上的經典之作《先人祭》。這部波蘭最偉大的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的代表作,一經公映,讓整個華沙為止震動,場場爆滿。華沙大學的中國女留學生易麗君也在觀眾席里。她還記得,台上的演員激昂地朗誦着台詞(詩篇),台下觀眾跟着一起朗誦。舞台上下連成一片,演員觀眾心意相通。
2015年7月29日,北京,人藝劇院,81歲的易麗君老人以詩劇《先人祭》中文版譯者的身份,在新書發布會上回憶四十多年前在華沙劇院里看此劇的見聞感受。和她一起出席發布會的,還有《先人祭》中文全譯本兩另外位譯者林洪亮、張振輝,來自波蘭戲劇界的藝術家,和新書出版方。發布會的主題,以碳色筆跡呈現在背景板上——“密茨凱維奇回到中國”。
易麗君在發布會上動情地復刻那個讓她終生難忘的演出場景:台上的演員,台下的觀眾,慷慨齊聲地發問:到處都是沉默,到處都是黑暗。怎麼辦?怎麼辦?
這句台詞,易麗君用波蘭語和中文,各朗誦了一遍。
“鐵幕時代”讓蘇聯大使觀看途中退場的波蘭戲劇
《先人祭》是波蘭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的代表作。這位十九世紀最偉大的詩人,是浪漫主義代表性戲劇家,亦是散文家、翻譯家、文學教授和政治活動家。他1798年生于立陶宛,進入大學後組織並領導學社爭取波蘭的民族解放,之後經歷了逮捕、監禁、五年的流放和二十六年的流亡,1855年因染瘟疫卒于土耳其 。在歐洲和波蘭,他被視為與拜倫歌德並駕齊驅的人物,其影響力超越文學,覆蓋文化和政治。早在1907年,魯迅先生在《摩羅詩力說》中,評價其為“叛逆者”,認為他“是在異族壓迫之下的時代的詩人,所鼓吹的是復仇,所希求的是解放”。
密茨凱維奇作品的靈魂,本質上是叛逆的。在《先人祭》中,密茨凱維奇用浪漫熾熱的抒情,通過古老民間祭祀儀式,反映了農民對惡霸地主的復集中反映了沙俄當局的暴戾恣睢和詩人對民族叛徒的極端蔑視。這部戲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民族神聖戲劇。
易麗君回憶,1968年《先人祭》波蘭某場上映時,蘇聯大使和夫人列席觀看,途中忽然離席。隨後,《先人祭》被“人民波蘭”政府禁演。以華沙大學學生為首的學生們發起了保衛《先人祭》演出的示威游行,軍警鎮壓,從而引發出一場震動波蘭、深受世界關注的政治事件。
那是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下,波蘭的“鐵幕”時代。
但更具體的背景是,20世紀20年代中期,波蘭政治開始“解凍”。共有的戰時經歷和戰後波蘭政治的松動,讓波蘭的藝術家們聯結在一起。他們在有限的言論自由、意識形態和經濟壓力下想法設法擴大自由度,批判獨裁政權以幽秘的方式侵蝕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礎:波蘭“1956年十月解凍”的中旗帜風潮“波蘭電影學派”在這時期誕生;1957年電影《下水道》獲得戛納電影節評委會大獎;1968年的“道德焦慮電影”、“團結工會電影”、“戒嚴時期電影”都在此間發軔……
《先人祭》在華沙的演出,就進行在這樣的時代浪潮中。這是波蘭政治歷史特定的時期,波蘭戲劇藝術家們,藉着這部誕生于19世紀的詩句,用自己的藝術方式與觀眾進行着詩學的交流,並以此向時代發問。
2015年8月3日話劇《先人祭》登上北京人藝舞台
被周恩來點名的“文革”期間發行的第一本外國譯著
《先人祭》在華沙的震動,也被同屬社會主義陣營里的中國感知。文革期間,在一次各駐外使節參加的外事工作會議上,周恩來問在場的外交官們,有誰讀過引起巨大反響《先人祭》?在座無人應答。周恩來當即表示此書應有中文版。
沒多久,人民文學出版社外國文學出版主管、著名翻譯家孫繩武先生托人找到易麗君,希望她能將《先人祭》譯成中文。幾番風險估量後,易麗君鄭重接下任務,並決定從《先人祭》四部中,選取政治風險最小、也是整本戲劇核心與靈魂的第三部先着手進行翻譯。
就這樣,白天的易麗君進行着斗、批、改“主課”,種菜、養豬、種稻、挑磚建房、教授“工農兵學員”的“副課”,晚上開始翻譯。幾經周折,終于成稿。為了規避風險,易麗君將新稿的譯者署名為“韓逸”,既指“漢譯”之意,又取“易”之音。
1976年初冬,中文版《先人祭》付梓。它成為“文革”期間第一本發行的外國譯著。時任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所長的何其芳讀後發出感慨:“這是一只報春的燕子,是一朵報春花!”
竟是如此巧合,在波蘭,《先人祭》用自己的深度和廣度,激起自己民族同胞的精神震蕩,而在同一陣營的東方,《先人祭》也同樣成為春江水暖鴨先知的報春燕。有人說,戲劇,尤其是經典戲劇,是對一個時期人們的公共精神狀況的測量與勘察。被魯迅稱之為“復仇者”的《先人祭》,成為兩個國家時代前夜里探測的路徑。
2015年7月31日《先人祭》中文版新書發布會現場
如今,時隔四十多年,《先人祭》老去的、白發蒼蒼的三位譯者,重新將作品的第一、二、四部翻譯完整。《先人祭》中文全譯本面世,也給中國當代的藝術創作者如何回應當代境遇,提供出一份歷史參照樣本。
在政治性寓言逐漸褪去對觀眾的吸引力之後,因抗爭現象產生的文學傳播現象,在當代已逐漸被社會發展進程和某一類美學潮流所遮蔽。那些和我們的命運曾息息相關的、已經發生或者還將發生的沖突,漸成高台上的一紙遺囑。《先人祭》中文全本的出版,詩人的聲音因此再次復活。誰曾是故事中那個抗爭者?那些被我們視為對抗性的詩篇、話語和行為,是當代歷史政治直接或者間接催生的產物,還是源于一個更幽遠並難以馴化的精神傳統?
也許我們能從密茨凱維奇的詩中,發現這個傳統的縱深維度。
“語言欺騙聲音,聲音卻欺騙思想;
思想從心理中飛出,卻在語言里死亡。
語言吞噬了思想,在思想之上發抖,
如同大地在看不見的地下激流上顫抖。
難道人們會從土地的顫抖探測出水流的深度?
有誰會想到這股激流正奔往何處?
——亞當·密茨凱維奇《先人祭·第三部》,易麗君譯,四川文藝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