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覺得,加繆可能是到了一定年齡才能夠喜歡上的人。年輕時代不太能夠理解他近乎冷酷的澄澈,也不太能夠想象他所定義的行動與荒誕之間的關系,更以為他和薩特相比,缺少傳奇和能夠忽悠人的“體系”——盡管薩特的哲學體系一直也不那么成功,但至少還算是有了一個時代的喧嘩和熱鬧。而在左岸邊咖啡館里,薩特與簽訂下共同生活契約、卻沒有結婚的波伏娃的并肩寫作,接受青年人近乎朝拜的擁戴,這幅畫面似乎也足以承載我們對于法國文學乃至哲學的浪漫想象。

阿爾貝·加繆(Albert Camus,1913年11月7日-1960年1月4日),法國小說家、哲學家、戲劇家、評論家,出生于阿爾及利亞的蒙多維城。曾于195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加繆不屬于我們對法國文學的這一類想象。貧窮在他的身上——包括寫作——留下了鮮明的印記。他日后曾經記述過對于貧窮的記憶,是到了高中以后,他“因家庭和貧窮而感到羞愧”。我們甚至不知道在阿爾及利亞的陽光、海灘和貧窮中度過童年、少年和青年時代的加繆,是否像《局外人》中的默爾索那樣對巴黎沒什么感覺,也認為巴黎“很臟。有鴿子,有黑乎乎的院子。人的皮膚是白的。”縱然他也有些吸引人的傳奇,例如能寫能導能演,例如憑借帥氣也能吸引不少女人,再例如喜歡踢球——后來和羅蘭·巴特一樣得了肺結核,才沒有把精力全部浪費到踢球上,最后,還有將他帶向死亡的那場離奇車禍,也是說什么的都有,但是加繆的文字實在是過于冷靜,非常有趣地與他這些私人生活之間清清楚楚劃了道分界線。
但我們也不能高估出身的作用。加繆以《局外人》的巨大成功為序曲的文學一生,其實是在法國文學——或者,更確切地說,是法語文學——的歷史里。他的荒誕、顛覆、抵抗,甚至包括羅蘭·巴特定義的“零度寫作”,都在法語文學的歷史里。都在試圖回答,在那個時代,在與法國文化有著密切關聯的地域里——歐洲或者北非,文學能夠做些什么,它自身的出路又在哪里。《局外人》是在伽里瑪出版的,它的遭遇要比法國文學史上的很多作品都要好,因為作為審稿人,同樣執著于人類狀況的馬爾羅很快就發現了它的價值。法語文學來到了20世紀,加繆和另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一起,保證了法語文學在當時繼續影響世界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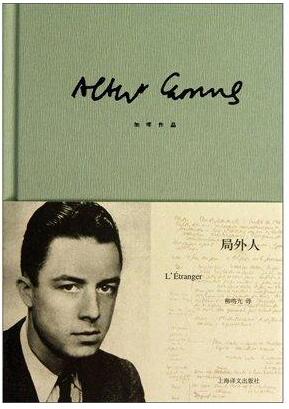
那么我們今天要怎樣來談論加繆呢?僅僅因為大多中規中矩的書單里,倘若選到20世紀的小說,《局外人》大約都會榜上有名?盡管到今天為止,真正讀懂那句“今天,媽媽死了。或許是昨天,我不知道”的人大約也還在少數。
《局外人》一出版,就是被當作“荒誕組曲”來看待的,和塞利納的《茫茫黑夜漫游》、薩特的《惡心》一起。塞利納直接寫戰爭中的士兵,薩特直接將他的哲學思考移植在不知名學者羅岡丹的身上,而加繆描繪的是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而且并沒有完全斬斷與傳統小說的聯系。小說有起始、發展與高潮,從母親去世,默爾索在母親的葬禮上沒哭開始埋下伏筆,到默爾索莫名其妙地殺人越貨,直至最后在法庭上以一人之冷眼抵抗全世界,加繆詮釋了荒誕的核心要義:命運之偶然以及需要知道自身存在意義的人,執著地向沉默的世界要一個答案的決心,縱然不是什么歷史的弄潮兒,也不是被戰爭逼迫著失去理智的人,只是和大多數人一樣,是在失去了上帝的世紀里的一個普通人,他也有權利向自己當時身處的那個沉默世界要一個答案。
加繆筆下的人物仿佛唯一的共同點是在這里:看上去木訥,茫然,隨波逐流,但到事件的最后,總會成為唯一清醒的人。加繆自己稱呼他們是“荒誕之人”。默爾索是這樣,他最后在心甘情愿地接受死刑之前,已經明白自己與周遭格格不入的原因在哪里。但是,與我們想象的正相反,預審推事,檢察官,律師卻都不知道真正的原因,他們只是沉浸在世界早已為他們規定好的意義里。默爾索甚至明白,一個人在母親的葬禮上沒有哭,他就可能要被判死刑,但是他仍然選擇“不超過自己的感受”的言說。在后來的《鼠疫》中,里厄醫生也是如此。里厄不是人道主義英雄,面對鼠疫,他的選擇是做一個醫生該做的日常事務。周圍的人,有的選擇接受,有的選擇宗教,有的選擇逃離,卻無一例外死于鼠疫,而從與鼠疫斗爭的一年中活下來的里厄也失去了一切——親人和朋友,孑然一身。里厄的勝利也同樣不是境遇的改變,或是成為抵抗鼠疫——大家都知道,鼠疫影射的是當時已經在歐洲肆虐的納粹——的英雄,而是他的清醒,他成了那個唯一洞悉鼠疫能夠帶來的所有罪惡的那個人。
或許,如果真正理解了什么是說得“不超過自己的感受”,就會突然間覺得加繆原來是自己心里的一個聲音,一個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例如道德、崇高、倫理,甚至是語言本身——被遮蔽了的一個聲音。需要借助加繆有些殘酷的層層剝離,我們才敢正視,才敢傾聽。
當然我們依然可以選擇不正視,不傾聽。畢竟不是所有人都有加繆的勇氣。何況加繆知道自己并不是沒有風險。因為《局外人》再成功,卻也只是呈現了荒誕的事實,而作為典型“荒誕人物”的默爾索,雖然他在法庭的一幕也把自己和自己身處的沉默世界的對峙推到了極致,可是接下來該怎么辦呢?荒誕的概念從誕生之日起就并不作為解決的辦法存在。這是加繆真正的殘忍之處。
塞利納在《茫茫黑夜漫游》之后就備受爭議,人們可以在依然習慣的道德、倫理框架內暫且假裝出對他的漠視和厭惡。薩特在《惡心》之后的文學選擇似乎更專注于自傳作品或是哲學體系的構建,依然被無數青年膜拜與追隨。荒誕作家們為各自找尋的出路讓我們趨向于相信,思考與行動的一致或許根本無法達成。但是加繆選擇繼續。選擇繼續探尋人類狀況。既作為小說家、劇作家、思想家,為我們虛構人類各種可能的,極致的處境;也作為行動的個體,在每一個危難時刻,并不選擇逃避,而是繼續他的西西弗斯之旅。
加繆是在這個意義上與薩特迅速地區分開來的。例如在每一場戰爭中的立場。從父親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到親身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到作為貧窮的白人家庭身陷殖民后的陷阱,也許再也沒有比加繆更具代表性的戰爭受害者。但是同樣將戰爭當作一種極致的,如同鼠疫般的人類狀況來對待,加繆給出的回答是拒絕一切暴力,無論這暴力是以什么樣的理由。據說1957年12月,在斯德哥爾摩接受諾貝爾文學獎時,他為瑞典的大學生做演講,被問及阿爾及利亞的局勢時,他并沒有隱藏自己的態度。他說:“我拒斥一切意義的恐怖,也包括如今阿爾及利亞街頭發生的盲目的恐怖襲擊,說不定有一天,恐怖襲擊就會波及我的母親和我的家庭。我相信正義,但是在選擇正義之前,我首先選擇保衛我的母親。”
歷史的不幸或許在于,盡管半個多世紀以前,對于這一類的問題,加繆就已經給出了理性的回答,但是半個世紀之后,在世界范圍內,恐怖襲擊卻以空前的速度在蔓延,極端和仇恨依然是人們最懶惰,同時也是最為輕易的選擇。這也許就是西西弗斯的宿命吧,也是在上一個世紀,像加繆這樣的人的悲劇性選擇。阿多諾問,奧斯維辛之后我們還能寫詩嗎?如果加繆泉下有知,一定會跳出來說:必須寫。這是怎樣一個充滿勇氣和真實的悖論啊。(文/袁筱一 翻譯家、華東師范大學外語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