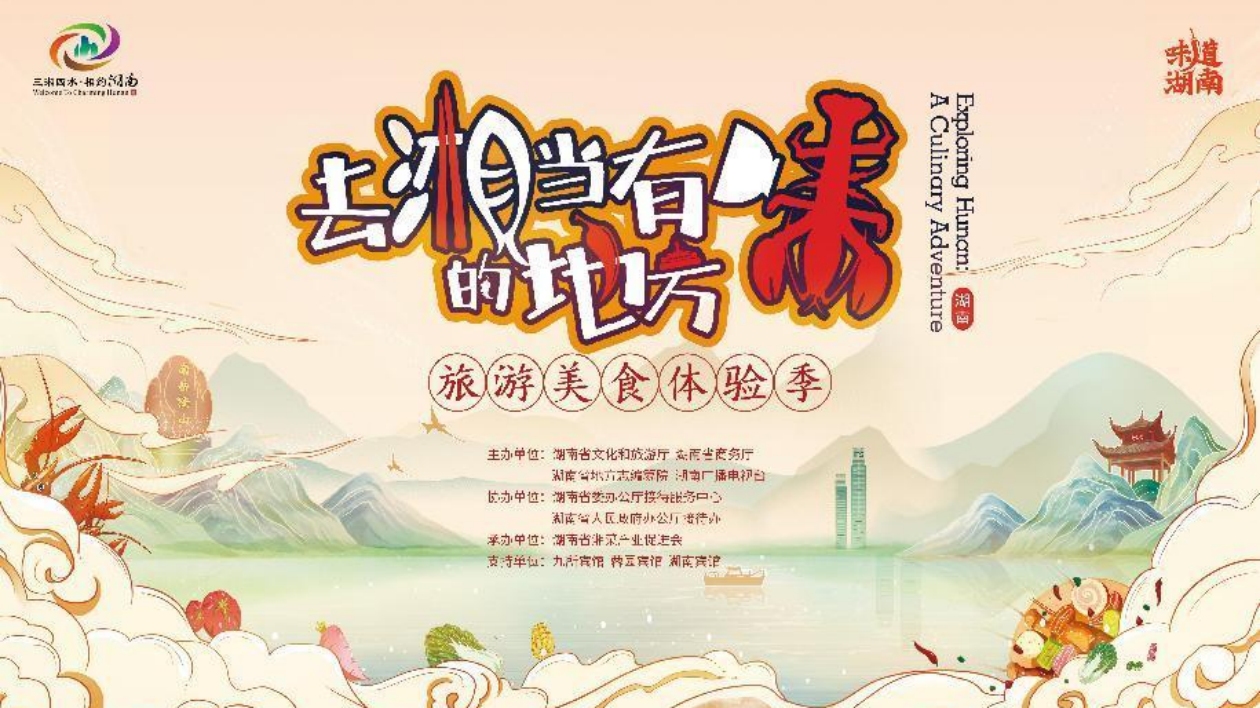許多在文學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偉大作家,即使他離開很久很久,如果有機會,我都想去他們曾經走過住過的地方看看,期盼在那裏捕捉到些許人生美好的神跡和人性光影。
時值穀雨,我來到了長沙市望城區。在下榻的酒店打開一本書,讀到杜甫當年曾在望城寫的《銅官渚守風》。他的這首詩被稱為杜甫的湘江絕唱。
唐大曆四年(公元769年)春,也是穀雨時節,漂泊一生的杜甫來到湖湘大地,從喬口溯流而上長沙。來到銅官山,江面突颳大風,行船停下,便在銅官街一戶人家借住避風。傍晚,他看到譚家坡山上火光沖天,把天空照得如同白晝。杜甫以為這是為春耕而燒山,房東告訴他,那不是燒山,而是銅官的龍窯正在用木柴燒制彩瓷。
這是我第一次從杜詩裏知道銅官是一個燒制陶瓷的地方。
也在這本書上,我看到一篇文章,說的是1998年,在印度尼西亞勿里洞島海域的一塊大礁岩附近,當地漁民下海打撈海參時發現一艘沉船,船身上寫着「黑石號」。「黑石號」沉船的發現,當時震驚了世界。這艘船經由東南亞駛向西亞和北非,船上滿載的都是中國貨物,僅瓷器就近七萬件,不乏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長沙窯彩繪瓷、白釉綠彩器等唐代南北方著名窯場的精品,其中以長沙窯器皿最多。在這些瓷器外包裝刻有「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字樣,「黑石號」沉沒的時間大約是唐代中晚時期。而船上的「長沙窯彩繪瓷」,正是杜詩中銅官一帶燒制的彩瓷。

「黑石號」沉沒地點

新華聯銅官窯仿製「黑石號」
我喜歡陶瓷。因為我出生在廣西欽州的欽江之濱。欽州坭興陶與江蘇宜興陶、雲南建水陶、重慶榮昌陶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被國家級機構命名為「四大名陶」。欽州坭興陶利用坭興陶土的細膩綿密、堅而不脆的特質,把刻、鏤、雕、填等工藝發揮得淋漓盡致。而欽江兩岸陶土經特定的配比和窯煉,又經打磨和研洗,陶土高溫窯變後會呈現「陶褐」與「陶彩」,煥發出凝重內斂的光華,深藏着不事雕琢的絢爛。早在1915年參加首屆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時,坭興陶就以這種含蓄古拙之美榮獲博覽會金獎。自小家裏就一直用着各種細膩柔滑的坭興陶器具,母親總不時在嚴肅提醒我們,用這些器具要輕拿輕放,生怕一不小心就把它打碎了。那時候開始,就感覺陶瓷是漂亮而有神韻的好東西。因為喜歡,便關注相關陶瓷地理,比如四大瓷鄉、五大名窯、六大瓷系,又比如陶與瓷的區別等等,當然只是一些皮毛的知識,所以對於長沙窯彩瓷出自銅官,實在有點孤陋寡聞。
我要去銅官,去杜甫詩中的銅官。
在銅官街一家叫「泥人劉」的陶瓷作坊,我遇見了「泥人劉」的後人劉先生。剛進門,劉先生就給我遞上一杯滾燙滾燙清香可口的「豆子芝麻茶」,據說這是望城一帶主人待客的見面禮節。「泥人劉」客廳的四壁,皆以櫥櫃和展台環繞。櫥櫃裏琳琅展示的,果然都是銅官窯陶瓷器具,展品質地細密,圓潤拙樸,瑩瑩如泛金石之光,沉沉似藏漢唐之韻。據劉先生自述,這裏共收藏銅官窯珍品千餘件,許多器物蘊含着銅官的歷史信息。他陪着我一起邊走邊欣賞。劉先生儒雅彬彬,身上自帶名士遺味,他的目光落到每一件藏品上,眼裏都露出柔情,透着自信和欣悅。他欣悅和自信是因為他長久與泥土、水火共生的親密經歷。他說話柔聲細語,我懷疑他的家族一定是銅官的大戶人家,但我並不懷疑他是一位真正的藝術家。我相信他有過祖傳的藝術訓練,更知道他也經歷過民間精神的洗禮,甚至知道他為銅官窯這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而整天不遺餘力地與泥土親密接觸。我只是驚訝他比我想像的更平常平易,就和銅官窯製品一樣,平易中飽含着神氣和清透。他對銅官窯彩瓷的來路曲直,娓娓道來,如數家珍,談興無盡。在他的眼裏,銅官瓷就是湘江兩岸泥土在跳躍的烈焰中「涅槃重生」,相對於其他名窯,銅官窯是為工匠們施藝、藝術家生發靈感,提供絕佳的物質載體。有通靈的智慧,方能體悟自然之精微,透窺造化之奧秘,於是便有包羅萬象的藝術境界。後來,我在長沙銅官窯博物館裏,看到沉睡海底一千多年,打撈出水後歷經周折才能回歸的那些彩瓷器,在柔和的燈光下比肩陳放。這些跨越歷史而來的每一件作品,都以銅官人從容自信的姿態,渲染着藝術世界的絢爛無極和自我本色。它們的誕生,是銅官人心血的凝結,賦予了生命。一件件作品,技藝之精湛,特色之鮮明,遺世獨立。這些在人類歷史上的文明成就,無不得益於像劉先生以及銅官的祖祖輩輩富於想像力的文化創造。
劉先生說,其實銅官的先輩早在唐代以前就懂得用泥土生產生活用具,在古潭州周邊遺留有大量的陶瓷碎片,距今有更遙遠的歷史。只是到了唐朝,由於社會安定和繁盛,人們生活水平得到迅速的提高,文化藝術比較開放,開放的社會帶來觀念的改變,因此在陶瓷上表現詩畫藝術方面更為突出,陶瓷製作技術發展更加趨向成熟。說到唐朝,陶瓷不得不提馳名中外的唐三彩。這種色彩亮麗並以黃、綠、青三色為基色的陶瓷之魅力至今仍歷久不衰。因此,深受影響的十里湘江,百處窯場,極盛時生產時間長、產量大、品質高、釉色美。銅官窯產品堪稱與洛陽、西安同代,生長在南方的一枝奇葩,它又不以高高在上的藝術性區隔於普羅大眾,而因價格略低深受海外客戶的歡迎。
瓷之美,半在釉彩。銅官窯彩瓷集百家釉色之大成,工匠們上承技藝,銳於新發別創,精研揣摩,砥礪嘗試,創造出獨具一格的制釉工藝。上釉的瓷胎經過龍窯烈火鍛冶,在自然造化的冥冥助力下,玄變出的色彩,華如霓衣,有一種金黃的色調,像一塊晶瑩剔透的琥珀,光滑細膩,沒有雜質,燦然光華,諸彩皆備,至妙至炫。劉先生說,毫無疑問,「黑石號」沉船上的彩瓷器皿就是那時候的產品,其中很多碗具在碗口都有幾處不規則的褐色斑塊,這類器物在中國本土是少見的,這便是為西亞地區阿拉伯客戶特意定製的產品,因此在設計上多有異域的元素,比如描繪一些胡人頭像或阿拉伯圖案等等。
人們可以在後人編纂的史志中,讀到長沙經濟地理對外開放的身份,也許想像不到銅官對外開放的意識在很久很久之前就發生了。
於是,我想起兩千多年前,漢武帝一生幾乎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如何消除來自北方匈奴的威脅。在厲兵秣馬的同時,漢武帝派出使者張騫前往西域,試圖打開國門和匈奴另一側的西域諸國結成同盟。
張騫當年到了今天阿富汗境內阿姆河的大夏國,驚奇地發現有漢朝的布疋比他更早到達西域。返回長安後,張騫把在大夏國的所見所聞呈報漢武帝。漢武帝驚喜之下,一條打通西出陽關的陸上絲綢之路應運而生。
公元前120年,長安已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在來自各地的貢品中,有一頭大象引起關注,負責運送貢品的官員說,這頭大象是南邊沿海城市用陶瓷從海外換來的。
南邊一定還有一條從海上到達身毒國再抵西域的路,否則中國商品何以避開匈奴源源不斷抵達西域?於是,公元前111年起,揚州、寧波、泉州、廣州、合浦等南方沿江海地區便慢慢形成了港口,逐漸成了中國與東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進行海外貿易的最早商港。一艘艘滿載絲綢和陶瓷的帆船,從各個港口駛出,揚帆東南亞,再轉至其他國度。一些國家的使臣通過這條海上通道,踏進中國。
這就是具有兩千多年歷史的海上絲綢之路。
一千年過去,到了唐代中晚期,海上絲綢之路已經非常繁華繁忙了。於是,銅官人毗鄰湘江右岸而居,天時地利人和,每天都可以看到裝載着銅官窯彩瓷產品的中外貨船在潭州港競發,順着滔滔江水北去,百舸爭流,匯入長江,到達揚州港,然後沿着南方海上絲綢之路,穿越太平洋、印度洋,走向紅海、波斯灣,走進世界千家萬戶。銅官,在中外文明的互相交流中,承載着不可忽視的作用,銅官,無疑是海上絲綢之路內河始發港之一。
談吐之間,我發現劉先生和許多望城人一樣,對銅官窯情深意切,並為家鄉的彩瓷早年就走出國門深感自豪。我想,其實今人和古人一樣,都要跟隨自己的內心,一輩子專心做某件事,並做精做美某件事,這就是工匠精神吧!
當我走進譚家坡一號龍窯遺址,撫摸着那些沉睡千年陶瓷生產的每一個工藝流程的平台,深深地呼吸着山間濕潤的空氣,仿佛感覺到了那個朝代的氣象,仿佛感覺到了龍窯的爐火仍在生生不息。前人的絕活至今仍在薪火相傳,今天的銅官窯在劉先生等眾多傳承人的指導下,在眾多藝術工匠的參與下,正在光大着這一人類文明的文化遺存。
春火在燃燒。當然,杜甫筆下「春火更燒山」的場景已不會再現,電氣化代替了木柴燒,彩瓷的生產設備完全不一樣了。世間一切事物都有萌生和發展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銅官創造了歷史並留下了輝煌的見證。變與相對不變把空間軸線上的人和事、歷史與今天連接起來……人間煙火味,最撫人心,有愛,有溫度,穿越歷史的火光和煙塵,依舊在人世間風靡,一直照亮一條從古老通往今天,從銅官通往世界、通向未來的璀璨之路。
於我而言,我讀過了杜甫的詩,走了他走過的一條路,聽到了他聽到兩隻白鶴在叫……我見到了銅官,也見到了「黑石號」上的物,宛若同在,便感受到了一種情懷,以及在內心生長出了對銅官窯的親切。(馮藝)
頂圖:長沙市望城區新華聯銅官窯景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