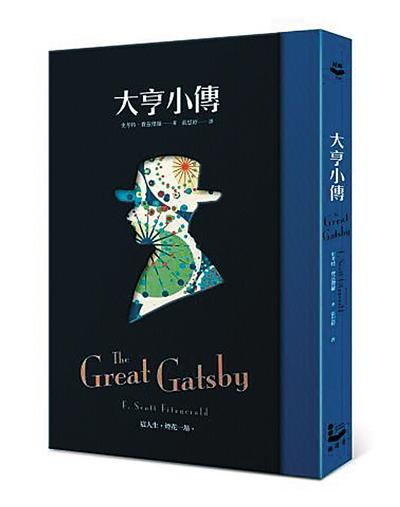
一年前,梁文道在凤凰卫视主持的《开卷8分钟》停播,引来无数唏嘘。不久前,《一千零一夜》一上线,立即在朋友圈引爆。这位都市说书人,试图用自己的方式“为中国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关于说书人——
“我不是在读书,我在说书,就像在天桥说书一样。”
北青报:《一千零一夜》的第一期为什么选择了《大亨小传》(《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本书?
梁文道:这个节目我的选书,开始定了一个规则:尽量选取人类文明史上的经典。这些经典范围可以很广阔,从《大亨小传》到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的一本名著《冲突的战略》。接下来准备要讲的内容里有哲学的,包括笛卡尔;也有很经典的不知道如何归类的蒙田的散文集;有《荷马史诗》、《源氏物语》……
把《大亨小传》放在第一集,是希望和今天中国的现实社会有一种呼应。我一直希望我们的节目更多针对年轻人,想透过三集《大亨小传》和年轻人对话,希望他们去看这本书,透过书看自己生存的时代。大家都说今天的中国进入盛世阶段,经济总体量可能在二三十年后超过美国。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冷静,看清楚是否有潜在的隐患和问题。
很多人在抱怨“今天的年轻人没有梦想,没有理想”,我倒不觉得,还是碰到过很多有高远理想的年轻人的。只不过我们要思考,我们有没有形成让年轻人追逐梦想的空间和机会?梦想的实质内容到底是什么?像比尔·盖茨那样今天看来很成功的人,他们最早在做事业的时候,可能没想到成为世界首富,他们想的是要世界有点不一样。今天看到盖茨觉得他发财是因为他做了微软,但是没想到因果关系是倒转的——他做了微软,成为了世界首富。
强调这个倒转是什么意思?就像我在第一集里提到当年在南方某大学演讲遇到的小孩,他要我记住他的名字和长相,说将来我会在财富榜上看到他。我问他如何实现,他说不出来。我们可以有梦想,可以梦想发财致富,但也请想想:我们要做点什么?
当年乔布斯那些人,在自己家的车库里鼓捣电脑,不是想发财,是觉得好玩、有热情,觉得可能会改变些什么。如果今天有更多年轻人,带着热情和好奇心去做一件事,就像当年硅谷那帮人在车库创业,也许那个东西将来是改变世界的。中国如果真的要变成一个在世界上有长远影响力的大国,需要更多这样的年轻人。发财是意外,不是目标。这样做出来的东西也许是可以改变世界的。
北青报:《一千零一夜》的拍摄场景如何选取?
梁文道: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节目成品是一个妥协的产物。原来想做的是每一集是一个旅程,开头上一辆公交或地铁,在上面讲,结束时下车。我常常看到读书风气盛的国家,很多人在地铁读书。在中国很多人搭公交坐地铁的过程中看视频,我想让观众感觉我和他在同一个环境里做节目给他看。
北青报:这种陪伴在身边的感觉更接地气?
梁文道:接地气有很多种方式,这种好玩,可根本没法实现,地铁和公交不让进去拍。目前变成在路上,节目开头是从公交上下来,结尾上一辆车。这样也有好处,发现另一种趣味,更像在街头说书了。
很多人会说:你为什么不静静地在书房读书呢?我是坚持在街上的。第一,为什么做一个读书节目就得在室内安静地扯?第二,我想提醒一个事情:到底什么叫说书?世界各地的说书人都是在公共场合说的,我不是在读书,我在说书,就像在天桥说书一样。
北青报:说书的形式有些复古,又用现代剧场版打通古今。
梁文道:这种背景环境是有趣的,你会慢慢发现现场环境和书的内容有时候会有很奇怪的变化发生。我在国贸那种最繁华的环境讲醉生梦死年代的《大亨小传》,是相关的。我会跟导演沟通,你不要特别去“配”书的环境,不要因为讲《人间词话》,你就给我带去当年王国维自沉的地方,可以在大马路上,产生反差。这样,背景环境就构成了对这本书诠释的一部分。虽然我是策划人,可每个导演都是独立的艺术家和创作者,要给他们空间去发挥。
传统上把文化谈话节目看作是一个有文化的人坐在那儿说的节目,往往忽略了视觉呈现的重要。我希望整个“看理想”系列在视觉上是有追求、有想法的节目。现在推出的三档节目已经可以看得到,但还不是很明显,希望接下来策划的节目有更大突破和追求,到时候大家就看到了。
关于文艺青年——
“文艺青年为什么不该站出来?为什么要躲起来?你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你不需要认错。”
北青报:在今天,“文艺”、“文艺青年”、“作家”这些词,被很多人和“穷酸”、“矫情”联系在一起。您在做这档全新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主要出于什么考虑?是情怀使然吗?
梁文道:《一千零一夜》是我开始发动起来的,我是策划人。我跟刘瑞林说,一起做点事。从头开始,就是想把它做出来,成为一个可以持续下去的品牌。“看理想”系列节目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把出版物变成视频节目和电视节目,就算做视频,也要探索做和目前我们看到的视频不太一样的东西。你可以说这里面必然有情怀。
这种东西大家今天看是不是会很可笑?我觉得会的。我们本来就很可笑,人家觉得你很穷酸,也许真的穷酸。但我的看法是——文艺青年就该站出来。我常常讲,文艺青年为什么不该站出来?为什么要躲起来?你喜欢你喜欢的东西,你不需要认错。
我觉得最近几年中国有些“反精英”情结,你看我们流行的字眼,比如“屌丝”,比如称赞一个人就说这个人“接地气”,骂一个人就说他是“精英”。反精英的倾向中国过去就有,现在又回来了,而且变得更加严重。
我不是批评这个现象,我完全理解,今天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包含了很重要的社会问题。比如今天的中国,出现了很严重的财富分配的差距,所以大家会有这种情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算是一个屌丝,假如他是一个考不上大学的普通小孩,他中学毕业后工作是打扫卫生,那他就不能文艺吗?对精英的想象,对屌丝的想象,都太类型化。其实完全有可能一个建筑工人喜欢古典音乐。但是在中国,坦白讲,文化,尤其是所谓的高雅文化,的确可能被某些有财富的人垄断。很多古典音乐会、歌剧演出,门票卖那么贵,不是一般老百姓能负担的。我们应该把那堵墙推倒——所谓高档文化的东西,跟社会上有财富、地位的精英画等号,我们应该把这种想象打破。
平常喜欢看书、喜欢音乐的年轻人我知道很多,他们并不都有钱,大部分是穷光蛋,但我知道他们的兴趣在那里,爱好是那样,那有什么问题?他们有什么东西是见不得人的?如果说我今天要做节目给他们看,我有什么对不住大家的?没有。
北青报:您过去说跟新媒体、跟海量信息要保持距离,现在做《一千零一夜》是想通过新媒体让更多喜欢文艺的人看到吗?
梁文道:大家可能都听过“长尾效应”这个说法,比如亚马逊有超过一半的销量来自那些非热销商品。正是有了网络销售,才使得某种所谓的长尾产品出现。
互联网视频跟电视最大的区别是,电视某个时段播出的节目,没法准确掌握受众是谁,总是想办法像榨汁一样把每个时段最大的潜在利益榨出来,追求最大多数人都能看得懂,并且喜爱的东西。但互联网视频能做分众的东西,不追求大众,能在一个机会里接触到全国有相近品位、爱好的人,这些人数量加起来也不少。所以我觉得,互联网视频做这样的尝试,应该可以试试看的。
北青报:《一千零一夜》之前,一直感觉您好像对网络上发言发声比较排斥。2011年有人问您为什么不开微博时,您表示:把每天吃了什么、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都放到网络上,很可怕,会暴露太多隐私。
梁文道:我到现在也没开实名认证的微博,那里包含某种鼓励一个人自我放大的诱惑。一个人为什么那么会想把自己的东西放上网被人看到?这里包含的是一种一个人觉得自己太重要的感觉,觉得自己太漂亮了,太了不起了,应该是宇宙的核心。潜意识里会有这个东西,会刺激一个人的自我。我觉得自己已经算是自我很膨胀的人,不想再被这种东西诱惑、放大自我。
北青报:您自我膨胀吗?在公众场合见到您感觉很谦和。
梁文道:不,那是你不知道而已。我一定是一个很自傲很自大的人,需要很多地检视自己。
北青报:您不用微信?
梁文道:我不用微信,只是在微博有一个马甲,我专门上去看。微博是很重要的政治讨论圈。我需要知道人们在关心什么。但我从来不发言,只看东西。也没有固定关注谁,就是看事。
首先,我发现人们关注的东西少了,你看看“热搜榜”上,时事已经不多见了,有很多娱乐新闻娱乐明星。全国人民每天最关心的是和娱乐明星相关的信息,所以我慢慢开始不怎么关心微博上的事件了。
北青报:目前看,“看理想”推出您谈书、陈丹青谈画、马世芳谈音乐的三档文化节目,点击量都相当不错。这个在你们的意料之内吗?
梁文道:陈丹青的节目最令人惊喜,一天过了两百万点击量。据我所知,这已经打破了所有同类型谈话视频节目的首天上线点击量。但我是一个比较冷静的人,我会觉得可能还得再多一个月去看稳定的观众数据才知道。也许有人一开始没看,后来慢慢加入,也许有人不是不看,是存了一段时间一起看。所以真的得用一个更长的时间单位来结算稳定的收视人群、数量和观看模式。
关于中国的问题——
“一个社会和民族,如果整体的文化感性或者审美能力够高、够丰富,这个民族不会太糟糕。”
北青报:从写时评到做视频,这转变意味着什么?
梁文道:过去我写很多时评,也做时评节目。今天回头看,很悲哀的是有些东西到今天还存在。我希望它“过时”,谈的东西今天已经不再是问题,已经改善了,但没有。当然很有可能指出问题的方式是错的,或者你认为的问题不是问题。写时评让我有乏力感,这几年一直有这种感觉。在今天的社会氛围,让我觉得自己做的事不是要针对刚发生的事,探讨成因,思考解决,而是要往更深层的地方摸。那是日常生活的习惯、习惯背后的文化的感性。
我觉得今天的中国有点情绪不对劲。比如说,前一阵子一个男司机在公路上暴打女司机,讨论后来就变成“女司机该打不该打”。这种讨论方式很古怪,问题应该在于“能不能打人”。为什么那么快就打开了打人的开关?文化感性还有另一面,为什么城市面貌这么不好看,为什么新的公共建筑会和生活格格不入,以及国人在国外的形象不好。这种文化感性让我越来越觉得,我要做的不是一个传统的写时评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是应该做更深层的东西。
我说一句很夸张的大话:我们要为中国再来一次文艺复兴。
北青报:这种“文艺复兴”的方式是怎样的?
梁文道:你眼界要远,做事要踏实,一步步做,不再谈这个社会出什么问题。
我相信一点,一个社会和民族,如果整体的文化感性或者审美能力够高、够丰富,这个民族不会太糟糕。有些东西在我看来不是道德问题,是审美的问题。表面上看我在给你介绍一本巨著、一首音乐、一幅画如何欣赏,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更重要的东西。
一个富豪炫富,不谈论道德与否,可以用一个最古老的、文明人的方法来判断:没样子、不体面。这种审美是感性的东西。我相信一个国家在感性上有层次,很多坏事做不出来,反而会做些好事。如果我们的电影、音乐、艺术、写作,能把层次拉得更深,我们对世界、对身边人的感受不一样,会比以前更敏感于其他人的存在,于是就懂得其他人,不会对他人粗暴、不礼貌。一个社会上有地位的人走出来,不会随便乱说话,因为他要讲体面。
北青报:不体面有人性的贪婪,特别急,急于成功,急于索取。
梁文道:急不来,急也不一定有用,还不如让自己冷静一点,说不定会做出比较正确的判断和选择。
北青报:很多生活中接触的人是不体面的,该如何保持自己的体面?
梁文道:文化感性对人的熏陶就是扩大对身边人的感受,包括理解和同情。很多人做事不合适,我会同情地理解他们那么做事的背景和理由。而且,看人应该是丰富的,也许我不是很接受一个富有的人对为他工作的人颐指气使。也会遇到在公共场合剔牙的人,我知道看人有比看这些行为更重要的标准:诚实、善良,比是否会当街吐痰重要多了。
我不太敢对人下判断,因此对很多事总是有所保留。说不出“我鄙视你”、“你是脑残”这种话,所谓的文化教养是使我们慢慢对所有人多一分体贴。不会那么轻易地对你当前这一刻的品位知识所接受不了的事情那么快去臧否。
北青报:这算一种妥协吗?
梁文道:这跟妥协没关系。比如我和一个人辩论,我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保留一个余地:也许我还没完全理解透你的观点,也许我还没注意到自己观点的缺陷。你总要保留一个空间,更不会因此说对方是白痴。本版文/张晓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