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英國著名藝術批評家、作家、畫家約翰·伯格(John Berger)2017年1月2日在法國病逝,享年90歲。作為當今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蘇珊·桑塔格也曾表達過對約翰·伯格的尊崇並熱愛——“在當代英語作家中,我奉他為翹楚……他是一位傑出的藝術家與思想者。”約翰·伯格在視覺藝術欣賞領域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改變了一代人觀看藝術的方式。評論人馬小鹽認為,伯格是繼本雅明、巴爾特、桑塔格之後,又一位對影像藝術如癡如醉的批評家。而在其關於“看”的著作中,名氣最大的《觀看之道》並非最好的,《另一種講述的方式》《看》《畢加索的成敗》《約定》都要更為厚重與深邃。同時,在藝術批評的光芒下,伯格還是一位擁有巨大才華的小說家,嚴謹的理性思維一點也不曾傷害到他柔軟的感性經驗,稍縱即逝的感性經驗亦一點也不曾抵觸過理性的嚴謹。無論影像理論,還是小說藝術,伯格都深受本雅明的影響。他的離去,對這個世界而言,某種程度上也是文化塌陷的一種隱喻。

伯格,一位著述豐盈,批評、繪畫、小說領域皆有超俗表現的文化大師,元旦剛過,便匆匆離世。相較2016年(2016年2月,埃柯離世),伯格的離世,似乎預示著2017年的文化氣候,將會更為寒冷。文化巨擘的消逝,對這個世界而言,往往是文化塌陷的隱喻。我們身處塌陷之地,唯有目送那些曾在我們的靈魂裏留下深深文字印記的前輩就此遠去。
我讀伯格,是在2010年左右,當時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伯格的一套叢書。這套叢書裏,令我驚喜的反而不是他的理論文集,而是他的小說集《我們在此相遇》。這本小說集,按傳統的文體分類,似乎不屬於小說,而是一本卓絕的隨筆集。實際上這本集子是典型的跨文體寫作:整部作品間於真實與虛幻、小說與隨筆、當下與追憶之間。以個人經驗為底色的半回憶錄小說,在世界范圍內寫得如此詩意優美的並不多見。在我看來,這本小說結構上的地志學寫作可與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相媲美,編織語言絲線的記憶術則可與納博科夫的《說吧,記憶》一比高低,只是納博科夫用循環往複的長句編織著他的記憶神毯,伯格則是長短句兼而有之。

《我們在此相遇》,是一本追憶逝者之書,也是一本追憶自身消逝時光之書。整部小說在書寫消逝而去的人物與安放人物所處的空間意象之間,處處匠心獨具。伯格將他記憶裏的每一位值得追憶的逝者,安放在一個與逝者精神氣質完全吻合的城市之中。這是一種令人吃驚的地志學寫作方式。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所有的人物與城市都是虛構的,伯格這本小說中的所有城市與人物卻是真實的存在。這種真假參半的敘事方式,比起純虛構更有挑戰性。這顯然是一位藝術批評家給予自身小說文本特意制造的一道難題,也只有批評家才會以一種美學的分類法來書寫小說。整本小說,語言輕盈,情感哀傷,虛構奇麗,一些段落讀起來宛若在閱讀不曾分行的詩歌。讀完合上書籍的刹那,令人震驚的同時悵然若失。伯格的這本小說,對我而言,是秘而不宣的珍寶。今天,他已遠消逝,讓我再次複述當初閱讀它時給予我難以解釋的閱讀經驗,唯有一個詞:震驚。
在我看來,國內關於伯格文本的翻譯,由於偏重其藝術批評家的光芒,遮蓋了其作為小說家的巨大才華。到目前為止,關於伯格的小說翻譯,我只讀到《我們在此相遇》這一本書。事實上,伯格是一個非常會講故事的人。這一點,他深受本雅明《講故事的人》一文的影響。本雅明把講故事的人分為兩類,一類是定居者,一類是旅行者。早年生活在英國,中年之後移居至法國阿爾比斯山下的一個小村莊的伯格,定居者和旅行者的身份皆而有之。在那個小村莊裏,他既是一個前來定居的人,也是一個異鄉人來的“講故事的人”。我期待在國內,早點看到伯格其他小說的漢譯本書籍。
伯格的《觀看之道》,是在世界范圍有著巨大影響的文論集。事實上,這本文集是伯格與他人合著(共五人)的一本影響范圍很廣的關於“看”之理論的文集。它原本是伯格為BBC策劃的一系列關於“看”之藝術的電視節目,後因節目播出後廣受歡迎,從而特意擴充整理而成的一部集子。在我看來,僅就影像理論而言,《觀看之道》並非伯格最好的著作,這本書之所以知名度高,是因當時搭乘了電視媒介的飛揚之翼。事實上,伯格所著的《另一種講述的方式》《看》《畢加索的成敗》《約定》比《觀看之道》更為厚重與深邃。前兩本著作伯格側重於對攝影的闡釋,後兩本的重心則傾向於繪畫藝術,《畢加索的成敗》一看標題便知,是一本專門論述畢加索畫作的批評文集。我想,伯格的這四本書,是每一位負責任的藝術批評家的必讀之書。當然,那些在中國藝術批評界渾水摸魚的藝術批評家,顯然不在此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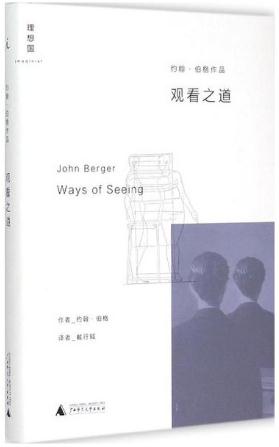
伯格是繼本雅明、巴爾特、桑塔格之後,又一位對影像藝術如癡如醉的批評家。他一生的批評文本,都在強調“被看到”,在強調“看”的獨特經驗,在強調“看”之表象本身。這種對“看”的癡迷,最初源於他對繪畫藝術的熱愛。伯格不但是一位對色彩敏感的畫家,還是一位繪畫教師。在22歲到29歲的青年時期,長達七年之久,他的主要職業便是給學生講授如何繪畫。他對“看”的敏感,應該源於早年的人生經曆。26歲左右,伯格在給學生教授繪畫的同時,開始給倫敦激進的左派雜志《NEW STATESMAN 》(新政治家)撰稿,並迅速崛起,成為英國當時最有影響力的批評家。在流行一時的共產主義思潮的影響下,伯格成為一位秉持左派信念的公共知識分子,他為農民與工人鼓與呼,他信仰共產主義,他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徒。
無論影像理論,還是小說藝術,本雅明對伯格的影響,宛若父於子的血脈相承。同樣是本雅明文本的傳承者與闡釋者,比起阿甘本哲學理論的晦澀,伯格的批評文本更為明晰與清澈。這也是伯格在國外,深受大眾歡迎的重要原因之一。當然,伯格的批評文本,對我國大眾而言,似乎已經無比晦澀,因今天他去世的消息,很少看到普通讀者慣性的點蠟燭。這種現象,一方面顯示出民眾正在學習著不盲目跟從,另一方面則說明,伯格這個名字,比起桑塔格,對中國很多讀者而言,顯然無比突兀與陌生。
伯格一生,左手理論,右手小說,嚴謹的理性思維一點也不曾傷害到柔軟的感性經驗,稍縱即逝的感性經驗亦一點也不曾抵觸過理性的嚴謹。感性與理性,在伯格的筆下彼此互補、完美互融。比起桑塔格被理性嚴重殤飭的頗顯固化的小說文本,伯格的小說文本更為柔軟、優美與詩意。伯格曾言:大多數故事以死亡為開端,從這個意義上講,講故事的人是死亡的秘書(大意如此)。在我看來,伯格本人,便是一位將批評文本與小說藝術完美結合的死亡秘書。我相信,作為一名死亡的秘書,即若在公眾的視野消逝,亦從未真的死去。他會在很多年後,在與心有靈犀的閱讀者的驚喜相遇裏,再度從紀錄下來的文本中,翩然複活。
馬小鹽,小說家,文化批評家,現在《延河》雜志任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