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去韓國,走了幾個地方,結識了很多人。最大的收獲是知道了韓國還有那么多的魯迅愛好者。此前曾與韓國的學者召開過一次會議,題為東亞視角下的魯迅,以為魯迅的影響只是在學者的范圍內。但在韓國的許多地方走走,才知道魯迅的名字在那里的影響力,絕非國內所可想象的。
最初知道韓國的魯迅研究,是因為六年前接觸了兩位來自韓國的留學生,一位叫金永文,一位名申正浩。申正浩的博士論文是《論魯迅與存在主義》,他還和我討論過一些問題。而那時金永文正在搜集中國學者有關魯迅的論著,其態度之認真,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不久友人把樸宰雨先生介紹給魯迅博物館的同人,樸先生時任韓國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會的會長,于是兩國魯迅研究界的一段有趣的交往真正開始了。
我的系統認識韓國學界的魯迅研究,還是從我們共同編輯的那本《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開始的。讀到內中的文章,才了解了其中的概況。坦率地講,他們的起點很高,問題意識交織著東亞文化里核心的困境。先前只讀過日本、歐美學人的文章,大意了解一二。但韓國人的讀解魯迅和別的國家不同,那就是有著尋路的饑渴和反抗奴役的激情。富有叛逆精神的鄰國友人,格外感興趣于魯迅的遺產。他們在這位中國文人的身上找到了一種自己需要的東西。那就是對舊傳統的超越和對人的解放的探索。魯迅的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氣,在他們那里不只是象征性的燈火,而且應當說是成為新人的一種可能。不僅僅是人生的啟迪者,重要的在于也存在著思維的快樂。一旦與這個遠去的小個子作家相逢,東亞人神奇的精神攀援就開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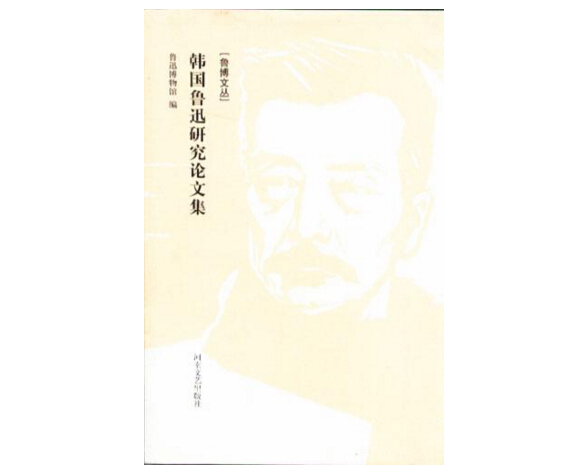
魯迅的引起他們的注意,主要是基于兩國相近的社會狀況,或者說是同樣的主題發生在我們兩國間。李泳禧先生多次強調,魯迅當年描述過的社會黑暗,和過去的韓國沒有什么區別,一些文字仿佛也是對韓國人說的。軍人的專制,文化的奴役,非人的生活,必然導致民眾的反抗,而那反抗中所遇到的問題,魯迅的提示是燃燒的火炬,照亮了困苦中的人們,那些思想同樣也適用于自己這類的思考者。評論家、社會運動家任軒永在《我與魯迅文學革命和人類的命運》一文里談到了魯迅在他生命里的意義。在中學時代第一次讀到魯迅后,他覺得自己的背井離鄉的心緒里就有魯迅式的感觸。兩個人的故鄉遇到了相同的命運,人也如此。后來他走向了反專制的運動,內心一直依傍著魯迅。1974年入獄的時候,他想到:“唉,既然坐牢,也在獄里讀讀魯迅吧。”后來,他第二次入獄后,內心里依然裝著魯迅。他寫道: 我的第二次入獄原因也和魯迅差不多,我加入世稱“難民戰”是在緊急措施統治下的民族主義運動進一步惡化的1976年。在那時,我的行動指針依然是魯迅。因為很多革命文學者或變節或以不幸的結局而結束的。但是魯迅幾乎是完美地將自己作為革命的火花燃燒到最后,因此我很羨慕他的這種智慧。
我沒有想到鄰國知識界對我國現代文化具有如此大的熱情。他們在20世紀70、80年代所表現的內在意識,與我國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青年是如此接近。東亞人在近百年的選擇里,遇到了相同的難題,專制主義和傳統意識使人們久困在奴隸的境地,個性被閹割了。而這正是魯迅當年一直所思考的,要突破的文化羈絆。韓國友人在自己的尋找里,感到了魯迅與自己的接近,也如同當年中國知識界苦苦介紹俄國文學一樣,魯迅在鄰國也成了精神的滋養。 閱讀這些異邦知識分子的文字一直讓我感到激動。我覺得他們讀解魯迅時并不比我們差。除了論著外,我所感動的還有他們的小品文,這些濺血的文字流動著高遠的情思。人們接近魯迅絲毫沒有唯理論的陳腐氣,那是心的撞擊,其間不乏靈魂的悸動。東西大學金彥河通過《狂人日記》暗暗感到自己也是一個吃人的人,擺在面前的只有兩種選擇,一條是“這樣的戰士”走的人的路,一條是阿Q走的鬼的路。金彥河說自己至今仍在人與鬼之間的掙扎。也由于此,魯迅對他具有了一種恒定的價值。我在這些文字里發現了作者心緒的精細和認知的深切,帶著一種自我的經驗,發覺魯迅世界閃光之點,學理的情思和生命的內覺就這樣合為一體。 李泳禧可能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魯迅的知音。他在近三十年文壇上有著不小的影響力。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他因涉足政治而遭到逮捕凡九次。那時他認為自己的國家出了問題,樸正熙、全斗煥、盧泰愚政權是不給民眾自由的。李泳禧在苦悶和反抗里找到了魯迅,他似乎覺得,自己要表達的許多意念,魯迅似乎都闡述過了。《吶喊》里的文字,既寫著中國人的苦難,也有自己同胞的影子,我們兩國在精神深處是如此地接近。魯迅的直面苦難又不安于苦難、不斷與苦難挑戰的大氣概,不僅中國少有,在那時的韓國作家里也是沒有出現的。所以,他借助字典,翻譯和介紹了大量的魯迅的文字,寫下了許多與魯迅相關的著作。據樸宰雨介紹,李泳禧的書曾風靡知識界,被成千上萬的人閱讀著。李泳禧認為,魯迅的偉大不僅在思想的層面上,也在社會革命的行動上。李氏就是在思想和行動上跟蹤著魯迅,對民族的解放做了巨大的貢獻。他在《我的老師魯迅》中寫道:
我從魯迅對民眾的關愛中學到了很多,受到很多影響。這絕不亞于從文章中學到的、受到的影響的。尤其在他的評論文章中,收益匪淺。過去的近四十年歲月,我曾以和韓國社會現實相較量的姿態,在社會上發表了不少的文章。那些文章,是在思想層面既像魯迅的,又在文學層面像魯迅的。因此,如果我在過去的一個時代,我給這個社會、知識分子和學生造成了一定的影響的話,那不過是間接地轉達魯迅的精神和文章罷了。我心甘情愿地擔當了那份腳色,并為之滿足。
我在沈陽和首爾兩次見到李泳禧先生,給我留下不滅的印象。他剛烈的性格和大愛的情懷,像一首壯麗的詩。和他對視的那一刻,好像走進了韓國的現代史。這是一個豐富的老人,他自身的故事纏繞著一個民族的苦難史,以及在那苦難中生發出的最為明亮的東西。他絕不自戀,常常有自省的精神。他在魯迅遺產面前表現出的謙恭和豪氣,我在近年中國的讀書人那里已很少見到了。人們只有在危難的時期才易和魯迅的精神發生共鳴。在今天這個消費的時代,魯迅已被許多中國人忘記了。當與李泳禧這樣的前輩交流的時候,我產生過一種慚愧感。比如我自己是在吃著魯迅飯,做專業的普及魯迅的工作,卻缺乏李泳禧那樣的激情,思想的體積漸漸生銹了。在魯迅遺產面前,沒有國界的區別,而一個異邦人的思考,反而會激活我們幾近冷卻的意識。韓國知識界散發出的信息,不只是學術層面的東西,在更深的領域,我們與人類的一種境遇相逢了。
自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韓國不斷有介紹和研究魯迅的文章問世。按樸宰雨先生統計,經歷了黎明期(1920—1937)、黑暗期(1939—1945)、一時露面期(1945—1950)、潛跡期(1950—1954)、新的開拓期(1955—1979)、急速成長期(1980—1989)、成熟發展期(1990—今),每個時期人們關注的重點略有不同,對當時社會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20世紀80年代后,魯迅作品的翻譯與研究著作在該國不斷涌現,現在每年關于魯迅的文章時常出現在學術雜志上,一些報刊介紹魯迅的文字亦常常可看到。近年間的學術論文達兩百篇左右,專著也一個個出現。直到現在,魯迅在韓國現代文學研究里占著很大的比重。一些研究古典文學的人也加入了這個行列里。劉世鐘教授曾沉浸在唐代詩歌的世界里。但基于社會的現實與心理的感受,她把研究對象轉向了魯迅。因為那里有著現代性的問題。所以,在各個大學的研究中,我們看到一個顯著的現象,學院派的研究在不斷深化著。每年的論文數量很多。柳中夏、李珠魯、洪昔杓、嚴英旭、任明信等人都有很有分量的文字問世。其數量遠遠超過日本。他們的話題也十分有趣,比如金時俊《流亡中國的韓國知識分子和魯迅》,金良守《殖民地知識分子與魯迅》,金河林《魯迅與他的文學在韓國的影響》,申正浩《魯迅敘事的現代主義性質》,劉世鐘《近代精神與反抗的方法:魯迅、加繆、韓云龍的道路》,柳中夏《金洙與魯迅:作為方法的東亞細亞》,在視角和方法上都有可取之處,有的地方,思考得很深。20世紀70、80年代的魯迅熱,是一種社會思潮中的狂飚,人們通過魯迅感應到人的解放的意義。那是心靈間的互動,思想者們在這里找到了變革的動力。20世紀90年代后,學術的分量在漸漸增加,我讀一些論著,覺得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了。這里呈現出東亞知識分子的一種情懷,這些理性之光,散出迷人的氣息。關于現代性,關于反霸權主義,關于主奴意識,關于民族主義等等,有著沉甸甸的分量。他們的特點是,緊緊地糾纏著自己民族的命運,同時亦多普世的東西。在一些想法上鉆研得很細,有時時空開闊得很,對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均有獨到的見解。一些學者在這里表現出的智慧和膽量,超出了許多日本當下學者。成為世界各國研究魯迅數量最多的國度,而且這個趨勢還沒有減弱的跡象。
離開韓國前的那個夜晚,我們在一個酒店聚會。那一天首爾及外地的一些魯迅愛好者、詩人、教授來了許多。酒過三巡,一個詩人用不太標準的中文喊著“魯迅!魯迅!魯迅!”。于是全場的人同聲高喊著,擁抱著,進入了一個狂歡的境地。聲音在寒冷的街市里傳動著,仿佛掠過一個世紀的哀涼,無數顆心因一個意念而共同跳動著。這是我一生經歷的第一次與魯迅有關的狂歡,國內任何一次魯迅研討會,都未能有過這樣的激動場景。我的眼角流著淚水,是因為結識新朋友的緣故還是別的什么誘因,一時也說不清楚。那一刻只是感到,魯迅已成了我們不同國度間的共同的語言。

本文節選自孫郁,《魯迅遺風錄》,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2016年9月。原標題為《韓國的魯迅風》,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